让生命灿烂绽放
作者: 杨菊芳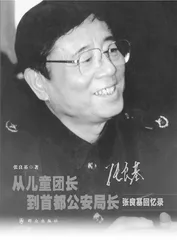
2021年的夏末秋初,从网上知道了良基局长的回忆录《从儿童团长到首都公安局长——张良基回忆录》出版的消息,我向良基局长要了一本。
拿到书我立刻就看。在第104页,我看到了如下一段文字:“1997年,《北京青年报》记者杨菊芳受市委领导委托到市局采访我。她采访很用心,也很热情。在采访时,很多同志对她说:‘我们的局长是性情中人,又不平凡又平凡,又刚又柔,又粗犷又细腻,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她非常认可这番话,抓住我的性格特点,写下了‘铁骨柔情’、‘性情中人’,并拟用《性情公安局长张良基》为题将采访文章发表,我没有让她发表。我认为民警是最辛苦、最感人的,应该报道他们的事迹。”
眼睛顿时湿润了,与良基局长交往的往事一一浮现在眼前。
我不禁想写一写当年的良基局长——这本回忆录里没写到的事情,写一写当年的峥嵘岁月。
一篇稿件,半世情缘
有人说:这世上,所有的“突然想起”,都是“一直放在心底”。
当一本回忆录唤起了我对于良基局长二十多年前的那么多记忆,我才明白,对良基局长的采访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多么深的印痕,和他联系密切的那两年多时光,是我记者生涯中多么浓墨重彩的一笔。
1997年,也是夏末秋初,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编辑胡素娟,约我采访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张良基,写一篇纪实报道。
在他的办公室,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首都公安局长。
他和我谈了一次。更多的,我是和市局法宣处,还有市局其他处室,各分局,乃至派出所的同志了解情况。
我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感人故事,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的性格。他的性格是独特的、相互矛盾的,有坚硬如钢,也有柔情似水,有时诙谐幽默,有时却令人望而生畏。
采访完成,我铺开稿纸(那时我还不会用电脑写作),用圆珠笔写下四个字——铁骨柔情。这是我对这位首都公安局长最深的感受,后来这四个字成了这篇通讯的标题。
稿件发表在当年《前线》杂志第11期上,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我觉得意犹未尽,打算再写一篇关于良基局长的报告文学,把我在受篇幅限制的通讯中没有写进去的故事和感触写进去。
于是,我在北京市公安局开始了时间更长、范围更广的采访。这是我和良基局长、北京公安队伍接触最多的一个时期。
1995年到1997年,是北京市公安局受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公安部表彰最多的一个时期。在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自杀和随后陈希同被撤职查办的重大事件中,良基局长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带领广大首都民警确保了非常时期北京社会大局的稳定,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信任。由于成功破获了鹿宪洲、白宝山这两起惊天系列大案,“张良基”这个名字在社会上几乎无人不晓。
许多次,我看到良基局长端坐在会议或活动的主席台上,身板直直、胸脯挺挺,像一座沉稳的山。帽徽上的金盾和肩膀上的金星闪着耀眼的光。
轮到他讲话了,他站起来向全体与会者敬礼。在立正敬礼的一刹那,他全身上下都绷足了一股劲儿。身躯在这时格外挺拔,脸上洋溢着光芒,举在耳边的手也绷得直直的……人民警察的神圣和自豪,威严和坚毅,全部凝聚在这个动作里。
那时他总是说:“我热爱我的事业。”这让人感觉他不像一个饱经沧桑的六十多岁的老者,而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二十岁的热血青年。一位记者曾说过:“我们当记者的,时间长了,对许多事都麻木了,可良基局长和罪恶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却仍旧保持那么一股激情。”那激情奔腾在他不衰减的工作劲头中,奔腾在他与罪恶不妥协的斗争中,奔腾在他对人对事的严肃认真中,奔腾在他对一个又一个目标锲而不舍的追求中,奔腾在他的大爱大恨、大喜大悲、大怒大笑中……他说过:“从参加刑侦工作以来,从实践当中,我原来的幻想逐渐变得成熟……”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仍有许多幻想,或者应该说,浪漫的理想,譬如:对工作的追求,对队伍的希望……
他讲起话来特别铿锵有力,两道眉不由自主地往一块儿凑,把印堂挤出了“壕沟”。他的讲话向来是声情并茂,还辅以各种手势来加重语气。有时会脱开讲稿,把眼镜摘下来拿在手里临场发挥一段,这时,他的表情也活泼了,眉头也舒展开来了。
他这一生穿得最多的是警服。参加非警务的外事活动他穿西服,在办公室或一些非正式场合他穿T恤或夹克。但任他穿别的什么服装,也没有他穿警服英武,那是男子汉的阳刚之美。
他上任于多事之秋,受命于危难之时。此前从来没有一位首都公安局长在任期之内赶上过那么动荡的国际国内风云和那么多的大案要案,也从来没有一位首都公安局长面对过那么严峻复杂的治安形势。
有一次我去市局采访,中午和法宣处的同志路过局长办公室,看见他正在打电话布置工作。
他招手让我们进屋。
他开了一上午会刚刚回来,脱掉了警服,摘下了眼镜,换了一双拖鞋。这是一个很长的电话,他左手拿着话筒讲话,右手不断地按着眉毛和额头,蹙起的双眉间显现出三道深深的竖纹,眼袋也变得格外显眼。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在公众场合不曾看到过的他的疲惫,也看到了他内心的沉重。
和我们一道吃完午饭,他又必须马上出发去首都机场参加一项外事活动。当他洗完脸换好衣服走出来的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又是一个容光焕发的公安局长。
对他来说,北京市公安局长这个位置是一个沉重的责任,他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重担的呢?
他说:“一个人需要压力,没压力就没动力。一个人要没压力就说明没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只要你觉得你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很远,就会有压力,对自己有要求。”
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第一站就在北京。北京市公安局全体民警总动员,力保万无一失完成安保任务。良基局长偏在此时患了重感冒,他靠打点滴控制病情,点滴打完针头一拔他就去上岗了。
似乎疾病想额外给他增加一些沉重,总在关键时刻找上他。那年春天,中央领导到永定河参加治河工程,良基局长也是患重感冒。他带警卫处的同志进行事前现场勘查。那天正赶上刮大风,永定河畔黄尘蔽天,良基局长一步一步察看、一步一步丈量,确定了中央领导参加劳动的区域地段,制订出保卫方案。待全部工作结束,他从头到脚整个儿变成了一个土人儿,只有鼻头,由于不停地擦鼻涕,是红的。
当年他对我说:“首都,什么都是重中之重。过去周恩来总理说外事无小事,如今是北京无小事。小事发生在北京,处理不当就可能变成大事,变成不安定因素。我们不能让中央、市委市政府分心,要为他们分忧。”
二十多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我当局长后,不曾敢有过一时一刻的懈怠,就连睡觉的时候,我的神经也是紧绷着的。我这个局长不好当,像走钢丝似的,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如何确保首都平安,确保党中央安全。”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当北京市公安局长的那些年,良基局长很少在凌晨两点以前睡觉。每天工作安排得满满的,基本上无缝衔接,直到夜里十二点以后,没人找了,他才开始批阅文件,当天的文件当天批完,还要撰写各种文稿。幽默就在紧张的工作中产生了:大家把他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赶往另一个地方出席会议、参加活动或执行勤务叫“走穴”,把秘书办公室叫“候诊室”,把他批阅文件叫“写作业”,而“留作业”的,自然是秘书了。
良基局长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他根据到他办公室的人多还是少来判断是工作日还是公休日。1997年的春节,全市第一次放七天假,秘书把局机关的放假通知报他批,他问:“怎么休这么多天?”秘书解释:“春节法定节假日三天,再前后借两个大礼拜。”“什么大礼拜?”他莫名其妙。“就是一周两天公休。”“谁规定的?”秘书笑着告诉他:“国务院。”
在工作出现困难或失误时,他自责或责备别人分量最重的一句话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他的下属没有谁会对他的这句话掉以轻心或以为是空话,因为每当他说出这句话之时,往往是他最愤怒或最沉重的时候。
他最喜欢的歌是《少年壮志不言愁》。
他不擅长唱歌,刚开始唱这首歌时,有些地方总是跑调,后来才算唱得比较流畅了。他的下属和朋友听他唱这首歌时,都知道他唱的不是那音调,也不是那歌词,他唱的是一个人民警察的事业、职责、胸怀,甚至生命。
一位相熟的小辈和他开玩笑:“您都啥岁数啦,还‘少年壮志不言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他认真回击:“我就是痴心不改!”
良基有良机,质朴纯粹真性情
1997年10月初,北京市公安局法宣处举行新闻发布会,侦办一年多的石景山系列袭击哨兵案终于告破。
前不久,良基局长带队慰问民警。他在东城、西城等处都没有多停留,唯独在石景山区防暴队——犯罪嫌疑人其母所在的石景山区,坐下来谈了四十分钟。第二天,犯罪嫌疑人白宝山就根据张良基的预测出现了,并走进了公安布下的天罗地网。
人们都说,这是北京市公安局献给十五大的一份厚礼。案破的时机,这个“寸”!
这又成为良基局长的一段佳话。
他的下属也对他进行过研究,提炼出了一句学术用语:良基现象。这个现象的基本特征就是:不断地遇到坎儿,又不断地越过坎儿。
他的一生,浓缩了北京公安尤其是刑侦的历史。他随着新中国公安事业的成长而成长,参与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几乎北京所有重大案件的侦破。也许是上天对他的磨砺,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重要关口,都有大案要案发生,可每一次,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在有关部门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各个专案组和广大公安民警的努力下,经他指挥,案件最后都得以侦破。他曾经满怀豪情地说:“我是替天行道!”这个“天”,便是党、国家和人民,这个“道”,便是保卫正义、惩治罪恶。
勇者无畏,仁者无敌。对公安事业的热爱,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是他总拥有良机的根本吧。
在良基局长的回忆录里,他对自己有个总结:“我带兵有优点也有缺点,很多同志说是被我骂着成长起来的,我承认,这是我的缺点也是我的优点。”
当年,市局许多人都领教过良基局长的震怒。急了,他真骂人,有时能把你骂个狗血淋头,但是他从来没有因为一己的事情骂过人。
当年的法宣处新闻科长刘蔚,就挨过良基局长的骂。那是一个初春的早晨,良基局长带领一批民警到机场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法宣处的同志随队采访。天在下雨,两天两夜没怎么睡觉的刘蔚又累又困、又冷又饿,抱着采访包打哆嗦。
良基局长走过来,指着刘蔚说:“别这么窝窝囊囊的。”
刘蔚小声说:“四点多就到这儿了,没吃饭。”
良基局长好像没听见一样,眼睛一瞪:“你给我精神点儿!”
任务顺利完成了,机场工作人员请良基局长用早餐。他的眼睛扫过一圈的人,落到刘蔚身上:“法宣处,跟我吃饭去!”
当年,良基局长有时称自己为“军人”。他少年时代参过军,一直对军队怀有深厚感情。而且,公安队伍不也是一支部队吗?
良基局长的下属常常亲昵地管他叫“大爷”或“大叔”,他很喜欢“大爷”这个称呼,他说老北京人管看门护院的叫“大爷”,而他这个公安局长就是给首都“看门护院巡大街”的。
不穿警服的良基局长就像个普普通通的老大爷,每天早晨起床后,洗完脸刷完牙,吃俩煮鸡蛋。良基局长是典型的山东人,平时还喜欢吃生蒜,大葱蘸酱,酱豆腐、臭豆腐抹窝头片。
他招待因公来访的人都是吃食堂。他自己吃饭有一个本儿,每顿记账,月底结算。一些特别熟的人来访,赶上饭口留饭,他不走客饭而是记自己的本儿上。有一次他对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徐滔“抱怨”:“滔子,你老在这儿跟我一块儿吃饭,这个月扣了我两百多块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