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热肠与趣笔
作者: 王应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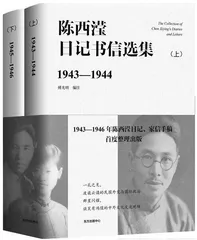
2022 年12 月,傅光明编注的《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上、下两卷本由东方出版中心付梓发行,该书集录陈西滢写于1943 年的日记98 则、1944 的日记225 则、1945 年的日记256 则、1946 的日记85 则。同书还收录陈西滢1944—1946 年致女儿陈小滢的书信61 通、陈小滢1943—1946 年致父亲陈西滢的书信21 通、陈小滢1946 年日记残片一则及沈从文1944年致陈小滢书信一通。
陈西滢15 岁负笈英伦,年轻时是现代评论派的中坚成员,也是鲁迅笔伐最多的现代作家。陈西滢何时养成记日记之习惯?现存史料似无从可考。但至迟于1943 年6 月,陈西滢已将记日记视为每天生活中的重要仪式,选集中有“晨,记日记”“晚,记日记”“补记日记三则”“补记五则”之语,即为明证。陈西滢日记的可贵之处在于不囿于记人记事,而在于评事议事。与《鲁迅日记》《周作人日记》以简略文笔记事记账不同,陈西滢日记更翔实,个人主观感更鲜明,早已超越单纯备忘录的范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傅光明在《代序》中说“西滢曾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中英文化协会’主任”,有意味的是,陈西滢从未在日记书信中提及这个官职,他当时对外开展文化交流的身份是“协会代表”,因有职无权影响力不大,叶公超曾出主意要陈西滢在教育部谋一位置,该事不了了之,国内来信竟称陈西滢为“旅英某君”,他在海外的处境由此可见一斑,所幸陈西滢淡泊名利,冷眼看世,不计较个人得失。《选集》说他有一次为Times 写稿,友人读后指出他不是一名国民党党员。1945 年8 月1 日,陈西滢到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c 出席会议,Homell称陈西滢为head of a Propaganda Organizationd,后者当面反驳说他“与P 毫无关系”,学者的铮铮风骨跃然纸上。陈西滢在日记中以春秋笔法切入历史的罅隙和暗面,从微观史学角度还原接近了事件真相,丰富了学界对民国史的感性认知。《选集》记录了民国四大家族不见经传的稗史:蒋介石竟因哈佛大学教授反对中国统制学生思想的言论而一怒停止中国留学生的出国计划,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程沧波因给《大公报》写社论而被蒋训斥被迫辞职,读者可一窥蒋之气量。孔祥熙的骄横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他往返华纽f 之间时,中国大使、公使、领事馆人员均要鹄立迎候,他竟头也不回,一眼不见。有一次他心血来潮竟训斥使馆工作人员一个小时,全体站立,气氛凝重,顾维钧大使身体吃不消,只得倚墙斜立。宋子文每天靡费十多万元,在中国银行报账,只有他可当面顶撞蒋介石,在中国学油了的史迪威竟然为他训练军队,宋子文的权势刷新了学界的认识。教育部长陈立夫强调“中国学生必须服从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如美国的民主政治一样”!陈西滢在日记中用了一个大大的“!”表达自己的质疑。思想不能统制,民众有自由表达的诉求,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识,早在20 世纪20 年代陈西滢就在《西滢闲话》中借萧伯纳之口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世界上只有一条金科玉律,这条律说,世界上没有金科玉律。”正是基于对民主政治的憧憬,陈西滢日记记录了对国民政府专制独裁行径的担忧,诸如抗战中封建主义Feudalism 的抬头;蒋政府的任人唯亲;国民党封锁边区,不让药品进入边区;基层政权中的保甲长贩卖兵役名额月收入数十万等,陈西滢冷眼观之,以皮里阳秋之笔委婉地表达了对上述行径的反感。
据友人回忆,陈西滢虽在文中喜欢“爱伦尼”(Irony),但其实是一个外冷内热的笃厚之人,此言不虚也。综观陈西滢的日记书信,他对朋友极为厚道,周绠生在纽约割盲肠,陈西滢亲去陪护;萧乾、叶君健在伦敦时,可借宿陈西滢住处,并与之彻夜长谈;陈西滢甚至借钱给一位英国传教士朋友Walbridge 买房,以致后来上当受骗;陈西滢与王世杰、朱家骅、杭立武等人书信不断;他与胡适、杨振声、叶公超、蒋廷黻等人可谓相知,说话多无保留。除了对友人的热心侠肠,陈西滢更是一个书生报国式的文化交流者,他站在民族国家立场,维护国家权威,介绍中国文化,促进西方世界包容接纳中国。1913 年9 月,陈西滢开始了在英国长达八九年的留洋生活,英国人称他的口语perfect,有人问他是否在BBC 广播,英国人说陈西滢的英语比他们本地人还说得好!陈西滢的英语阅读写作能力更是一流,他起床第一件事就是阅读英文报刊,晚上睡觉前常看英文小说、戏剧和时政评论。陈西滢在《选集》中写得最多的是他看戏看电影的观感,傅光明指出这是研究20 世纪20 年代到1946 年好莱坞电影和演员知识的重要史料,此言不虚也,那么陈西滢为何如此热衷于观演看戏呢?仅仅出于孤漂海外排遣寂寞的需要吗?我们从他给女儿陈小滢的信中,似乎可以一窥端倪,在1945 年7 月26 日的信中,他教育女儿说:“数学这门功课,与英文相同,一定得常常练习,不练习便会忘去。”显然,陈西滢认为学习英文需要练习。他在日记中说他1943 年7 月买一台radio,其目的就是练习听力。那么,为了维持专业水准的英文水平,看戏看电影就成为陈西滢一个重要的学习方式。世纪20 年代中期,陈西滢以“闲话体”时政文享誉文坛,1937 年8 月1 日,他在《武汉日报》发表《华北时局的解剖》一文,全面回顾了“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双方的政治、外交、军事博弈,告诫国人放弃幻想,做好中日全面开战的准备。该文2000 余字,见解犀利,有史有论,惜未被陈子善编的《西滢文录》收录。《选集》中记载胡适、周绠生在纽约夸赞陈西滢写的战争评论国内无出其右者。陈西滢在1943 年7 月7 日即预测中国的抗战将于两年内取得胜利,他对时局大势的把握很敏锐。为了维护国家权威,消除英美媒体对国内的误解,陈西滢查阅资料,请胡适斧正,写出答Baldwin 的辩驳文章Chinain Pacific Strategy,发表在1943 年9 月5 日美国的主流媒体New York Times 上。1944 年8 月23 日,陈西滢被教育部正式任命为中英文化协会驻英代表,当时他胃病复发,夜不能寐,1944 年9、10 月德国的V2 火箭弹肆虐伦敦,有几次就在他住处不远爆炸,他在床上不停地“打战”,生命在旦夕之间。为了鼓舞盟军士气,他到York给一个轰战机军营做演讲;为了促进中英文化交流,陈西滢到伦敦、剑桥、斯特拉特福德、利物浦、曼彻斯特、纽卡斯尔等地参观学校、图书馆、名胜古迹、工厂、美术馆等,拜访罗素、福斯特等名家;陈西滢的专业是英国文学,他对莎士比亚、燕卜逊、奥登、艾略特、伍尔夫、萧伯纳等人的文学点评极为精当;他奔波于伦敦的大街小巷,只为早日给中英文化协会找到合适的办公地点;他协助British Council做好陈寅恪访英翻译唐书的工作,他出席UNESCO的会议,维护了中国的地位和形象。
日记本是一种非常私密的文体,作者写作时并未想到出版,故没有必要做假,陈西滢的日记书信采用一事一记的分行体,内容非常零碎,他把一天中印象最深的事情记载下来,只言片语,弥足珍贵。陈西滢月旦人物,点评时事,总是非常简洁,从来不会超过一句话,大有郑逸梅“补白体”的风味。陈西滢过目不忘,他的日记对时间、地点、人名、物事的记载相当准确,有时开国际会议,西方学者几十人的名单,他能一一记录在册。陈西滢看事犀利,见解独到,语句诙谐,读他的日记,有妙趣横生之感。诸如他写叶公超,说他“豪气纵横,什么人都加批评”,叶公超在饭桌上是一个话霸,1945 年2 月24 日,陈西滢请Roxby 夫妇吃饭,请蒋仲雅、萧乾、叶公超作陪,结果“公超一人讲话。到后来Roxby 与仲雅及炳乾背过去说话”。这种无声的抗议不知叶公超能觉察否?熊式一是一个在英国大获成功的戏剧家,国内盛赞他的《王宝钏》《天桥》,可陈西滢却说他的Bridge of Heaven“抄袭中国旧小说中的故事、笑话等”,“写得毫无生气。书中人物也没有一个活的”。这个熊式一也是一个有点奇葩的人,他向英国文士学者介绍驻英大使顾维钧,竟然带有卖弄自己人脉资源的意思,领了顾维钧一路走过去介绍,让顾维钧颇为难堪。这个过于“恳勤”的自大作家很会逃税,“二战”时英国实行严格的税收政策,但熊式一“会填种种的claim!9,不必出所得税”。
陈西滢是一个有广博学识的智者,面对西方学者的有意刁难,他能做出有力的反驳。英国的经济学者Mrs.Joan Robinson 攻击中国留学生出国前必须受训的纪律制度,陈西滢反驳说“中国人也应有些discipline ”,比如英国“King’s 的草地只准dons走,学生不能走。在中国做不通”。该例子太生动了,国情和传统有别,纪律的领域和尺度就不同。在中国行不通的荒唐事情,在英国却根深蒂固,可见纪律和自由也不能照本宣科、生搬硬套。印度人帕里卡尔讲“中印间的文化关系”,他说中国翻译了许多印度书,印度没有译什么中国书,一个英人说“印度人长于语言,所以不必等翻译,中国人不长于语言,所以要有翻译”。陈西滢在演讲结束后问此人:“是否英人比俄人、德人长于语言,如何俄、德人译英书比英人译的俄、德书为多?”以其矛攻其盾,这个英人理屈词穷。翻译与一个国家开放的学习理念有关,与是否“长于语言”关联不大,陈西滢以英、俄、德为例,委婉地批评了所谓某个国家“长于语言”的观念。
陈西滢的戏谑之笔有时也用在对国内文坛和人事的评价上。他认为曹禺改编的《家》并不成功,“角色太多了,线索也太多了”,“并不成为好剧本。不过曹禺写的人物,有些很不差,对话也常很好”。他说袁浚的《万世师表》“写得坏极了。这样幼稚的作品在国内居然可以出版、行销,而且上演”。上述语句尖锐刻薄,这应该是陈西滢站在西方戏剧的高峰来俯视20 世纪40 年代国内话剧的过激之词。他在1945 年7 月20 日的日记中写驻英大使顾维钧宴请于斌主教和威斯敏斯特大主教格里芬,“于斌穿长袍马褂,挂金十字,头戴红帽,很是神气。只是穿了中国衣,更觉得肚子凸出”。这位主教在国际场合很压得住台面,陈西滢说他“很是神气”,惜中年发福,肚子凸出,陈西滢在此不知是在调侃他穿的“长袍马褂”呢,还是在调侃他发福的身材?语气中有戏谑的味道。
行文至此,有两点必须提出来:其一,陈西滢的《选集》包罗万象,特别是为20 世纪40 年代海外汉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书目,诸如赛珍珠的评论The Chinese Novel、抗战小说Gragon Seeds、Waley 翻译的《西游记》《金瓶梅》在西方很有影响力,元曲《灰阑记》被译为英文、德文,在伦敦的剧院上演。韩素音的Destination Chong King,Standish写中国的小说The Small General,哈罗德·阿克顿的Modern Chinese Potery#4 等,均有待学界的进一步研究。
其二,《选集》校勘工作还要进一步精进,诸如1944 年4 月4 日日记中写到“回时不认识路,做错了车”,此处的“做”应为“坐”之笔误。1944 年4 月29日日记中写到“三世余熊、谭乘车去St.MaryleboneChurch”,此处的“世”为“时”,即下午三时多之意。1944 年5 月28 日日记中写到“ 到SheldonTheatre”,可下行中却写成“Shelton Theatre 是牛津授学位等等的礼堂”。1945 年2 月27 日日记写到“尧圣大谈祖文霞”,后来王东原请Irene Ward吃饭时“招祝等二人来陪”,此处的“祝”实为上文说的“祖”(祖文霞)。1946 年3 月1 日日记写到“住在车站附近的Hotel Cortinential”,注释说是“大陆饭店”,此处Cortinential 英文拼写错误。有时陈西滢在日记中也有误笔,比如1945 年4 月5 日他写到“苏联莫洛托夫已宣布日苏中立条约。参战的前奏来了”,不是“宣布”,而是“宣布废除”。以上错讹均没有校勘出来。
作者: 王应平,文学博士,湖北工程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