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深处那抹红
作者: 夏桐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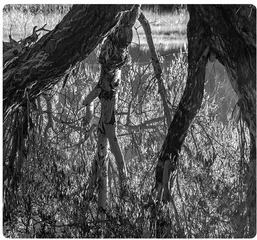
纵然历史的黄沙覆没了戈壁中千年的大梦,纵然岁月的流岚黯淡了荒漠里曾经的明珠,但当你只要身临沙原,抚触那如云如霞的沙漠红柳,倏然间会让你铭感到朔漠深处里的那一簇簇红,恰似一堆堆熊熊燃烧起的生命之火。它不嫌贫寒,虽默默无闻扎根于大漠,但终以柔弱的身躯顽强挺立着抗风固沙,其遭千磨万击却仍坚韧不拔的意志、坚守不迁的品格,堪让你于景仰中铭骨感怀。
就在这旷茫的荒漠里,一句“我在敦煌等你”,她便选择了终生坚守。或许她只是一句此生命定心归处的禅念,感应于莫高窟古老斑驳的壁画上那穿透千年的莲坛慈光,就志以一个拳拳凡心女儿身,凸显着择一不移地守护祖国瑰宝的执着夙愿;或许也是一个女孩儿源自心海的深情承诺,是“敦煌的女儿”两情相思恋燕侣,一腔赤心图报国的真情相约,是“敦煌的女儿”志许“他乡生白发”,力改“旧国见青山”的一意誓念。
“敦煌的女儿”,是《光明日报》于1984年1月3日专题报道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樊锦诗女士坚守大漠二十年,而展开一场文化苦旅先进事迹通讯中的称呼。这位一夜成名的江南女子迈着曾经患过小儿麻痹症的双腿,从长大成人的上海,走到了向往求学的北大未名湖畔,又从北京大都市走向了迢迢千里之外的大西北,走向了荒漠寂寥千年的敦煌莫高窟,这一走就是人世大半生近六十年。她从一身青春走到了一头白发,从满腔活力走到如今影印在金灿敦煌的,一个颤颤巍巍微驼的背影。这位貌似柔弱,却一生坚毅的老人,在走过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坎坷和艰辛后,化一己半世心血,带领一群莫高窟人在漫漫苍凉的黄沙里,走出了令国内外无不蔚然崇仰的敦煌宝窟于沧桑后惊艳的灿烂光辉,成为一位荣膺“改革先锋”国家称号的“文物有效保护探索者”—这一和平年代里的伟哉英雄。
一
1963年7月,北京大学58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樊锦诗,与另外一位马世长同学,两人一起被分配到敦煌莫高窟。对于当时才刚走向社会,尚且年轻的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个女孩子会到地处大漠戈壁深处的莫高窟工作,更不会想到这一去就是五十多年。
对于分配去向,樊锦诗既感到意外,却也平静地接受了。她感到意外的是,虽然去年由导师带领自己等四名同学在莫高窟参加过实习,但由于体质差致水土不服原因,仅实习了三个月时间就无奈地先期离开了敦煌,怎么还会分配自己去那儿工作呢?其实她是不想去的。她之所以又平静地接受了安排,那是因为自己也曾发自内心地向学校表示过坚决服从国家需要,分配就是自己志愿的态度。何况学校还主动承诺会在三四年后分配人替换自己,并会调自己到武汉工作,能和男朋友一起,所以她单纯地就连父亲写给学校的求情信都给压着,根本就没有交上去。
这年夏天,一个才刚二十五岁的瘦弱年轻姑娘,背着大大的背包,肩挎一个黄布挎包,头戴一顶草帽,出现在北京火车站,与同行的马世长同学一起,在哭得像个泪人儿的马同学母亲千叮咛、万不舍的送别下,登上了开往西部那漫长路程的列车,踏上了此行漫漫人生路的艰辛旅程。从踏出这一步开始,樊锦诗就再也没有中途下过这列笃行无悔的人生列车,她梵行苦旅大漠洞窟半个世纪之多,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探索和开拓精神,架起了一场历史的罡风,让千年莫高窟以崭新的高科技形态,在新时代得以涅槃重生。
敦煌的美震撼人心,那时候敦煌的苦也着实令人惊心动魄。初见敦煌,樊锦诗尤感惊艳无比,她惊艳的是千年来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大漠深处,竟会产生如此金碧辉煌的石窟壁画艺术,她完全沉浸在了那衣袂飘拂、翩跹起舞的若英若仙的境界中。可是,也只有留在这里后才真正知道,洞内是神仙世界,艺术宝库,洞外却是飞沙尘扬,黄土漫天。
在她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宿舍里,听得清窗外大风呼啸,屋内黄沙弥漫。住黄土房、睡黄土炕、用黄土桌、置黄土书架、坐黄土沙发,冬冷夏热的房子里充满着一屋子的土味;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一个女孩子半夜还要摸黑外出如厕。有天夜半起床正欲出门,她突然看到黑暗里两只绿油油的眼睛正在对面瞪着她,吓得她以为是狼来了,赶紧关上房门,提心吊胆地过了半夜,等到第二天早上一看,才发现那儿原来是一头拴着的驴。
她习惯了老鼠掉到枕头上,爬起来赶跑老鼠,掸掸沙土再若无其事接着睡的日子;她习惯了除了白菜、土豆就是萝卜,想吃水果是奢望的清淡生活;她习惯了洗完头发竟留下一头黏糊糊的白碱,却还要省着用水的尴尬;她习惯了包裹着窗外黑黢黢的夜暗,就着昏黄的油灯看书、写信、著文案的辛苦时光。过惯了都市生活的樊锦诗,她尽量不去想上海那个遥远世界的日子,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江南的小女子。她藏起了年轻女孩子都喜欢照照脸庞的那面小镜子,更剪掉了那个年代的女孩子都喜欢留着的一头乌黑的长发,一直到现在都再没有蓄过长发。她就这样咬着牙清苦地度过了这段十分难捱,也仍然坚持着要捱过去的漫长岁月。
时光在流逝,鸣沙山上沙粒窸窣滚动的嗡嗡嘤嘤声,似是莫高窟内千年佛国老人传出的阵阵呻吟;莫高窟九层楼檐角铁马于风中荡响的叮当声,宛若洞窟壁画上的飞天仕女在呜咽……这如泣如诉的声音,百年来一直寒鸣在旷渺的大漠上空,也战栗似的叩打在了才刚踏上莫高窟土地的樊锦诗的心头。一路的艰辛已将她的生命旅程连接上了那时尚不清楚何日再尽辉煌的敦煌石窟。
二
黄色是我们华夏民族的传统底色。我惊奇那连绵起伏的漠丘上铺天盖地的澄澄黄沙,我惊叹那莫高窟一溜儿外墙满壁的灿黄,我惊艳那洞窟壁画多配以明亮华丽的橘黄。就因为炎黄子孙是中国人的标志,就因为黄土高原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
茫茫黄沙深处的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二十五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的峭壁上。洞窟始建于公元366年,经历了从北凉到元的十个朝代,其间连续建造时间长达千年,是古丝绸之路上一处集建筑、彩塑和壁画三者结合创造的立体文化艺术宝库。崖面南北两区一千七百多米长的峭壁上,分布着远看错落有致如蜂房般现存的七百三十五个洞窟,洞内绘有壁画四万五千平方米,雕立塑像两千四百余尊,其画塑真迹真实形象地再现了浩瀚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这段千年间的奇珍艺术所展现的杰出成就,极具无与伦比的珍贵艺术价值,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时代影响和历史地位。
莫高窟就像一个孤悬大漠深处的千年老人,积一体旷古痼疾,染一身黄垩沴疫。面对密密麻麻破败不堪的石窟群,看着像是披着一件件破破烂烂旧袈裟的壁画和塑像,樊锦诗深有感触地叹愕研究所的前辈们,竟然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缺资金、无保障地无怨无悔工作和生活了二十余年。她想起了导师和系领导行前对自己语重心长的嘱托,暗暗立下了一生守护莫高窟绝不放弃的坚定志向。于是,她自此接棒了常书鸿、段文杰这两位敦煌莫高窟第一、二代开拓者和奠基人,一路筚路蓝缕,自20世纪40年代初开启守护敦煌这样一场史诗般的接力赛。舍一生于茫茫大漠,樊锦诗以对中华文化的一腔血脉挚爱深情,接续启动了又一场持久的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的跋涉历程,将戚戚忧心之家国情怀,毅然安归在了那“西出阳关无故人”之孤寂冰冷的敦煌石窟里。
樊锦诗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敦煌的时候,莫高窟呈现的几乎就是一片废墟,很多洞窟里都堆满黄沙,有些洞子就根本进不去。她一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就风风火火地参加了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参与对南区窟前遗址的发掘清理工作。每天一早,她跟着同事们一起,攀一架用两根搭靠在崖壁上的木杆,再横向绑扎一束束树枝,制作成一坎坎踏蹬的“蜈蚣梯”,爬到崖壁上下错落分布着四五层的洞窟里作研究。每当攀爬的时候,这个形似蜈蚣的梯子就会左右摇晃,吱吱嘎嘎作响,虽令樊锦诗难免一阵心惊胆战,头皮发麻,却也仍是咬牙坚持着每天照常爬壁钻洞,不知疲倦地清理流沙,翻寻文物,考研古迹。
为什么在被世人遗忘的大漠里,会创建出如此辉耀世界的石窟艺术?这些光辉熠熠的壁画和彩塑,究竟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这些壁画和彩塑形象再现的佛国世界又是怎样产生、发展和被最后湮没在历史的记忆中……带着这些问题,樊锦诗走遍了大大小小七百三十五个洞窟,就着手电筒的光亮,凭着一柄放大镜,精细入微地研看每一幅壁画,研索每一尊塑像;和专家们慎重研定一个个抢救性保护壁画的修复措施,以竭力延缓这处数千平方米壁画的衰败,延长这片古迹瑰宝的寿命。
敦煌定若远,一研动经年。2011年,她历时四十年主持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正式出版,被权威专家誉为国内第一本极具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日前,另一本历时十余年编写、共三十多万字的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9窟考古报告》,已正在进行出版前的最后修订。
五十多年来,樊锦诗女士在担负繁重的各项业务与管理工作,以及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之外,精心缜密地单独撰写、著书,或与他人合作撰写,计发表考古报告、学术论文、各种提案、纪念文章,以及国际合作协议等共八十多篇;在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和活动中发表学术演讲、专题讲座、会议发言共计三十多场。樊锦诗女士就这样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生命完全交付给了古老敦煌的流沙和莫高窟这片圣洁而又神秘的伟大文明,用她的学识,用她的执着,用她的汗水,用她对中华民族文化炽烈的爱,竭力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催生出了一幅幅揭示并体现着科学结晶之五彩斑斓的新时代“神光”!
三
“敦煌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樊锦诗后来曾这样说起。还早在上海生活时,她就被父亲带去博物馆欣赏艺术大师的作品,也曾有幸看到敦煌壁画美术展览。因此,敦煌石窟那些幻化在灵动作品中的美,早就让她少年时代极富幻想的心灵感受到了艺术美带来的冲击的震撼,因而从那时起,她就萌生了要一睹敦煌真面目的念想。
当大学毕业后,樊锦诗迢迢数千里来到敦煌,在那个沙石纷飞的戈壁大漠中,她还是被莫高窟内的壁画上从北凉、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的一壁壁琳琅满目、丰富多彩、满壁风动、天衣飞扬的佛国锦绣所倾倒和陶醉。每当一缕缕灿烂的阳光泻入洞窟,照在本就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时,那栩栩如生飞动的身形,那婀娜柔媚的舞姿,就真若仙女般活灵活现;那灵动缥缈的仙乐,那芬芳飞洒的鲜花,竟真就犹似置身在如来世界,幻响起了宛若清梦般的阆苑仙曲。这些显以轻盈飘逸艺术形象的飞天神女,还有那一个个出胯旋身、丰腴奔放的反弹琵琶伎乐舞女,施以一幅幅色彩和线条凝固的时空,被天才的画师永远定格在洞窟的石壁上,千年生动地诉说着一个个浪漫与想象幻化出的神仙故事,充分地展现了天人合一的魅力艺术境界,浓郁地演绎出华夏民族五千年历史文明的精髓传承。
然而,樊锦诗在组织抓紧编制洞窟科学记录档案时,她通过找出一幅幅前后数十年间不同时期的照片,进行了一番比对,竟然惊讶地发现,现在见到的彩塑和壁画已经或模糊,或残缺,或丢失。壁画在退化的警钟,开始在她心里惊扰;壁画在退化形成的魔咒,开始如影随形地缠绕着她本就不尽平静的生活。如何将莫高窟的石窟艺术历史信息真实完好地抢救性保存下来,成了樊锦诗日思夜想放不下的一件大事。
20世纪80年代末,一次偶然的机会—樊锦诗出差北京,看到有人在电脑上展示和储存图片,她通过认真地学习了解后深受启发,顿时萌生依据计算机技术,建立数字储存保真洞窟壁画的历史信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敦煌石窟壁画和彩塑艺术档案的构想。在当时计算机技术尚未广泛应用的情况下,这个大胆的创意,立即得到了国家科委和甘肃省科委的大力支持并很快下拨专项经费,开展敦煌石窟数字档案建设的立项研发。无独有偶,没想到这一研制数字化档案的实验,居然也正好同符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的“世界记忆工程”项目的发展理念,因而也得到了国际专业组织提供先进数字技术,展开壁画数字化项目的合作支持。
“数字敦煌”计算机技术石窟壁画历史档案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数字化工程建设,历时二十多年,持续攻克了涉及灯光及色彩管理、影像自动采集、图像拼接形变等一个个技术难题,形成了一整套集数字影像采集、数字色彩处理、数字定位存储、数字展示传播等壁画数字化技术规范。截至目前,此项目已完成了两百多个洞窟的图像采集,两百余个洞窟的VR节目的制作,四万五千张底片的数字化图像处理,还完成了莫高窟和榆林石窟两处大遗址外景的三维立体重建。敦煌石窟数字化档案建设,让千年文物焕发出了万年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