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象绘画在红色主题美术创作中的主导地位
作者: 李海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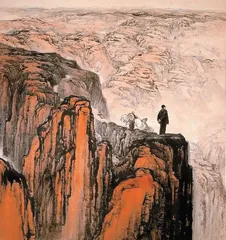
关键词:具象绘画;抽象绘画;红色美术;人民群众
绘画在艺术形态上可分为具象绘画和抽象绘画,属于两类不同的表现语言和手法。具象绘画就是艺术家通过对外部物象的观察、感受,而进行的客观描绘,从而达到视觉感官体验上的科学性、物理上的真实性及审美体验过程的愉悦性。具象绘画在欧洲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从中世纪到20世纪之前,西方艺术就是具象绘画的历史。不论是服务宗教的中世纪壁画和人文思想复苏的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华丽浓艳的巴洛克、洛可可和重振古希腊古罗马的英雄主义精神的新古典时期,以及描绘人民群众生活的批判现实主义时期,都是以具象绘画的表现手法为宗教、家族、王朝贵族及大革命服务,也包括沙皇时期的宫廷美术、俄罗斯“巡回画派”、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现实题材作品,这些不朽名作无不体现出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力量。1839年摄影出现之后,“绘画死亡”的言论开始不断争鸣,一度让人们对具象绘画的功用产生了怀疑。来自摄影的外部挑战并没能取代写实性绘画,反而使写实性绘画借助其发展壮大,出现了新现实主义、照相写实主义(超写实主义)、里希特的“摄影绘画”等。
抽象绘画是20世纪之后发展起来的,不描绘自然表象和物理空间,而是通过最基本的点、线、面、色彩来表达最丰富的人类情感、精神。具象绘画和抽象绘画都来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只是抽象绘画更强调绘画的本体语言和平面化,将形式提到与表现内容同等的位置,更强调个人情感表达。抽象绘画就如西方古典音乐,在旋律的基础上通过改变节奏和音色、加装饰音来表达,不像带歌词的通俗音乐那么容易理解,相对于人民性的、大众化的具象绘画,抽象绘画更偏向于精英阶层,这也是抽象绘画一直被人们看不懂或难以理解的原因之一,也是抽象绘画在红色美术创作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和长期扮演着“他者”的角色的问题所在。
中国百年美术发展史,红色美术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红色主题美术创作,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不同时期的光辉历程,其中具象绘画艺术创作在百年红色主题美术创作创新发展史中居于主流和主导地位,而其发展原因和选择逻辑也是有其必然性的。
一、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党的指导思想,文艺是党宣传思想战线的重要领域,红色美术作品对于塑造这一百年来不同时期、各个阶段的民族精神,特别是在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以人民为中心的红色美术是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做出的积极响应,是一百年来中国美术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内在诉求,是在党的领导下美术创作的实践成果,代表着新中国美术创作的发展趋势。
20世纪初,鲁迅、蔡元培、胡适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民主与科学启蒙思想的序幕,经过苏联革命实践检验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1931年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领导下的进步美术团体“一八艺社”在上海成立,他们一边学习革命的文艺理论,一边进行革命美术的创作,在鲁迅的倡导下社员们进行木刻创作,以艺术作为战斗武器,新生的版画特性符合时代的要求,很快形成了全国性的新兴木刻运动。左翼美术运动的倡导与发起者鲁迅将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和墨西哥壁画运动中最杰出的共产主义画家迭戈·里维拉介绍到中国,广大的美术工作者受到影响并自觉地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具象绘画表达方式,形成了“为改造国民性而美术”的美术创作实践。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主持召开了文艺座谈会,系统地阐述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态度和主张,从思想上回答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号召文艺要很好地“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逐渐形成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民族化”的具象绘画创作方向,并且针对形势形成了“为抗战而美术”的创作实践。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形成了“社会现实主义”和“为人民而艺术”的创作指导思想。
从党的不同时期文艺方针大的方向来看,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以贯之。从绘画艺术的功能出发,具象绘画与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理论相呼应,符合革命美术的需求,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路线的方向。尤其是红色美术创作要做到通俗易懂、易于传播、易于接近人民生活、易于拉近和老百姓的距离,让人民群众享有平等的审美权益。现实主义的具象绘画相对于抽象绘画而言,更适合红色美术的创作需要,特别是红色主题美术的审美诉求,同时也符合中国美术发展大的趋势和规律。
二、近现代以来中国美术教育的培育
美育,又称美感教育,是将美学原则贯穿于教学实践后形成的教育。2018年8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8位老教授的回信中强调:“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落实党的文艺、教育方针,发扬爱国精神,引导莘莘学子在红色美术创作上讴歌党和人民,表现时代发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华美育精神,始终贯穿在我国美术教育的不同阶段。
20世纪初,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一代人提出了“科学救国,美育救国”的救国策略和文化理想,中国美术教育引进并开启了西方式学院美术教育的道路。徐悲鸿、林风眠作为中国早期两所重要美术类专业院校的掌门人,一生均致力于中国美术教育事业。他们在法国完成高等美术教育的学习,并将欧洲的美术教育理念引入到中国美术教育中来,创建了中国式学院派高等美术教育的体系。虽然他们留学法国时,正是法国印象派如日中天的时候,但徐悲鸿接受的教育和他回国后的美术教学实践,沿袭的还是印象派之前欧洲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具象绘画路线。《美的呼唤:纪念徐悲鸿诞辰100周年》一书曾写道:“他(徐悲鸿)是第一个把写实主义的素描移植到中国的传史者。”[1]虽说学院派美术教育属于精英、象牙塔式教育,但其培养理念最终都是以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为己任的,体现了艺术救国思想和“为社会而艺术”的艺术追求,也成为中国学院派美术教育中一个最严谨的基础教学派。
林风眠承继的更多的是印象派以后的艺术理念,在具象绘画教学的实践上,更注重个人情感、情绪的宣泄和个性的表达,强调画面形式的重要性,体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蜜月期”的50年代,苏联派专家在1955至1957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办“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训练班采用的是苏联油画教学体系。在马克西莫夫的协助下,中央美术学院在油画教学大纲、油画教研制度等方面采用了苏联体系。现在很多让人耳熟能详的经典红色美术作品均出自参加过这个训练班的各大美术学院教师,他们中许多人后来相继成为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骨干。徐悲鸿也是最早热烈赞扬苏联现实主义美术并把它介绍给中国人民的美术教育家,他对素描非常重视,力求打好造型基础,这些主张都与苏联绘画教学体系如出一辙。在一切向苏联社会主义学习的时期,1952至1962年间,鲜有到欧美留学的艺术家,中国大量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归国后他们任教于国内的美术类专业院校,使得苏联写实的现实主义绘画更为广泛而深入地传播,也影响了新中国美术基本结构的构成,几乎所有高等美术学院的美术教育都曾长时间沿袭苏式具象写实美术教育体系。
当代,在我国高等美术教育中大多沿袭的还是这种苏式美术教育体系,苏式美术仍然是我国各大美术院校绘画基础教学和考试的准则。20世纪之后,现代艺术观念大大拓宽了艺术的疆域和国人的视野,西方艺术流派纷呈、轮番上阵、此起彼伏、多姿多彩,演变到甚至认为架上艺术已“死亡”,加上后现代艺术概念的扩大,一个时期架上艺术似乎沦落到了边缘地步。现代主义艺术更多是从艺术本体思考,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而后现代艺术强调了艺术的社会性、人民群众的参与性和互动性,艺术的表达方式、表现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写实性具象绘画能在我国美术教育体系中落地、生根到壮大,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各种思想内容庞杂,涉及面广,尤其是主张观念先行,主导了抽象绘画,弱化了传统绘画技术,艺术与非艺术界限渐渐模糊,各种翻新的观念与中国社会普遍的现实问题有一定距离,抽象绘画在功能与传播上带有局限性;二是抽象绘画在创作功能指向上,难以适应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和政策需要;三是红色美术作品具有史诗性、叙事性,是人文观念、思想深度和历史主题三者的有效统一,具象绘画更容易表现,且直观而具有力度。当然,当下的中国学院派美术教育正在逐步突破苏式具象绘画教育的单一模式,在红色美术创作的表达方式、表现形式上逐步注重传统与现当代艺术表现的有机融合,将个体的生存体验、主体审美融入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英雄人物、新时代劳动模范等主旋律叙述之中。同时,近些年党和国家也加强了美术人才的发展规划和储备培养工作,组织实施国家艺术基金创作项目、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人才培训、美术家海外研修工程等,这些都是在学院美术教育培养基础之上的再次提升。
三、画家对绘画形式语言选择的自觉
美术,作为造型艺术或视觉艺术,运用物质材料,通过造型手段,创造出具有一定空间表现和视觉审美的可视化艺术形象,而绘画艺术则是用材料在平面上表达出某种立体效果或色彩的效果,引发人们的共鸣、联想和思考。红色美术主要是要在思想和主题上表现红色革命的历史印记、现实与理想,以现实主义的再现和讴歌为主,中国的经典红色美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色美术的思想的主体性和内容的主题性是其基本特征。主题承载着绘画作品所要表现的中心思想或主要内容,特别是在描绘性艺术中,主题关涉到个人或事物的再现,也涉及艺术家的具体经验,这经验也是艺术创作灵感的来源。画家对题材的选择,尤其是在红色美术的表现上,对思想立意和内容主题的确定则往往是其先导,是画家在开始酝酿和构思时首先要考虑和确定的。
红色美术作为党和国家文化价值建构和艺术创新的重要符号,之所以具有重要的价值,是因为其创作的审美形式和特定历史内容体现了现实主义精神,实现了“人民性”与“艺术性”的融通。绘画是静态凝固的艺术,文艺工作者在创作红色美术时,以亲历者或间接体验的方式,通过各自对党的历史与现实的理解,在红色美术作品的创作思想、内容的选择上往往要力求题材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在创作风格上则要力求现实的相对直观的具象叙述,通过对历史发展、人民革命和现实生活的表现,叙述、阐释和建构一个艺术的世界,达到视觉和情感上的共鸣,以之来鼓舞人、感召人,进而化育人。红色绘画的主题和思想必须要符合普罗大众的视觉经验,往往才能引起广泛共鸣、传播久远、构成经典,同时还必须有正确的政治思想观,把握艺术创作的功能方向,不断实现艺术为人民服务的诉求。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写实的具象绘画,都便于画家实现红色美术的思想和主题诉求。当代中国的红色美术创作,在具有扎实的写实能力、深思熟虑的构思构图、重视社会功能性和严肃性上借鉴与汲取现代西方艺术观念与语言的同时,也突破了以往的“纪实性”描绘,呈现出新时代红色美术的审美追求,但其具象形态的创作表现仍是主流选择。
四、新时代历史使命的感召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上,红色美术创作能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提和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首先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依靠的就是为人类提供精神指引和动力的文化输出。主导权、话语权是文化输出的重要一环,依靠的就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美术作品。若要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只有将党的文艺思想建立在中华美学精神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发展进步和人民生活面貌表现好、展示好,不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文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