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好作家的成长史,都是一部优秀的写作教科书
作者: 徐则臣 傅小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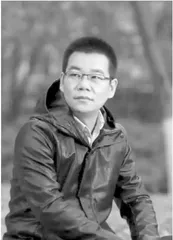
“你的世界观与别人真正区别开了,你的写作也必然成为独特的存在,但做到这样很难”
傅小平:你被视为中国“‘70后’作家的光荣”,你的作品亦被认为“标示出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可能达到的灵魂眼界”。但以我的观察,你写的评论、随笔、创作谈,包括你做的演讲等在内的一系列文章,也标示出了同时代评论家在青年时代可能达到的思想眼界。套用流行的说法,你是作家里面自我阐释能力特别强,也是擅于阐释的评论家里面写作能力特别强的。你对写作不仅有自己独到的心得体会,也有一套相对自足的理论构架。你何以对理论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徐则臣:我当然谈不上什么理论构架,我写的就是自己的一些杂七杂八的想法。它们看起来有点一脉相承,是因为我有一个比较坚定的对理想中的好小说的想象。所有的想法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对那个好小说的描述和逼近。可能会有一些矛盾处,但整体上这些想法是渐进的、相互修正和完善的。一个作家不可能完成了所有的写作才开始整理自己的写作理论,他会边写边想边实践,要实践出真知,要理论联系实践,互动着往前跑。
傅小平:当然,我有时也想,作家在写作上是不是不妨糊涂一点,开个玩笑,作家自己都充分阐释了,就没评论家什么事了。其实,作家有很强的理论构建能力挺好,前提是能促进写作,而不是用理论把自己给框死了。更何况,写作和理论在一个作家身上并不总是并行不悖的,有时候反而会是相互背离的。
徐则臣:我觉得你的担忧,不是因为我在边写边总结自己的想法,而是担心我会画地为牢,把自己活生生地憋死在自己预设的写作理念里。这的确是我需要警惕的。在我的想象里,好小说是开放的,关于好小说的理论也是开放的,我希望我的思考也是开放的,这就意味着,当我的努力事与愿违时,我能够及时地反省和调整。不是最终非此即彼地服从哪一个,而是尽力找到最合理的那一条路。所以并行而悖并不可怕,恰恰是一帆风顺可能更糟糕,它会让你忘记反思这回事。
傅小平:没错,不管怎么说,作家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总是好的。也因为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年一直有人提作家学者化的问题,我觉得这应该不是说要作家同时做一个评论家,或是要作家有大学问。如果作家学者化有必要的话,你觉得必要性在哪里?也不妨说说,有阐释能力,有理论基础对你自己的写作有何帮助?
徐则臣:在我看来,作家学者化的最重要一条是:你要有问题意识。你知道你写这个故事的意义和必要性在哪里。由此,你才会以文学的方式去研究问题、表达问题、解决问题。由此才会产生及物的文学,文学也正是这样一步步发展至今的。作家的任务不仅仅是讲个好看的故事,故事漫山遍野,不需要一群人当个事儿专门去干。自我阐释说到底不重要,真要写得好,会有无数人帮你阐释,甚至你永远也想不出的东西都能掘地三尺给你找出来。学者化肯定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让你有问题意识,能够就某些重要的问题深入有效地思考下去,让你成为一个有脑子的作家。
傅小平:既然说到理论,就得说说你关于“世界”的理论。因为你在不少随笔文字里谈到对“世界”的理解么。你还写了一篇《零距离想象世界》,挺有意思。感觉应该能代表你现在理解和把握世界的一个角度,或某种方式。
徐则臣:这是写作面临的现实。现在的科学技术、网络这些东西,让世界上任意两点间的距离越来越短。我们处在一个地方,却要去想象它。叙述本身就是想象的一部分。你无论怎么描述,其实都包含了你对一个事物的想象。比如,我在北京写北京,就是一种零距离的写作,所以零距离是我们根本的处境。那么,我在零距离的情况下怎么写北京,就是我在小说里要解决的问题。
傅小平:由“世界”延伸开去,不妨谈谈世界观的问题。想到这个是因为想到,一个作家的写作该怎样在本质上与别人区别开来?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个作家和那个作家写得差不多啊,要是深受某个外国作家的影响,还往往会被冠以“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福克纳”之类的称谓。尤其是对于初学写作者来说,模仿是不可避免的。反过来说,不同的作家写作很不相同,那又不同在哪呢?说白了,这关系到作家该有怎样的世界观,该怎样确立自己的风格的问题。
徐则臣:没错,模仿和超越,在我看来,关键在于是否形成了自己面对世界的独特方式。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必然要求与之契合的表达方式,别人谁也帮不了,模仿在这里是失效的。李敬泽先生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怎么写其实是个世界观的问题。你的世界观与别人真正区别开了,你的写作必然也会成为独特的存在,但做到这样很难,所以才会有“影响的焦虑”。总的来说,模仿在写作中是必要的,因为你得知道游戏的基本玩法,你得学习和借鉴,需要别人的光照亮你幽暗的角落,激发你的创造;其后,超越是自己的事。
“当‘大作家’的影响溢出文学,于世道人心等有所增益时,他就既‘大’且‘伟’了”
傅小平:想起你不时提到萨拉马戈和他的《修道院纪事》,是不是也因为在这方面给了你很多启发?这部小说,我读了印象特别深的,并不是介绍语里写的所谓一位士兵和一位具有特异视力的姑娘之间奇特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些奇崛的想象,比如人造的大鸟,得靠人的意志驱动之类。你一看就觉得这是虚的,它偏偏又嫁接在一段实的历史上。要让两者很好地融合起来,且有说服力,真是很难。
徐则臣:我的确非常推崇萨拉马戈。还为他的一个中译本《所有的名字》写过序。如果别人问我说,你最喜欢的作家,只挑一个,我会觉得有点难;但要我说最喜欢的三个或五个作家,那里面肯定会有萨拉马戈。这部小说让我对小说艺术,也不只是小说艺术有了不同的理解。这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在于,萨拉马戈把虚和实处理得特别好,他是以实写虚的典范。中国作家写实就像你说的,写得很好,但写虚就是不行。萨拉马戈写虚就特别好,他作品里的缝隙,或者说那种轻盈的东西,比卡尔维诺要重。但要变得拙重,又飞不起来。萨拉马戈处理得刚刚好,拿捏的那个分寸我特别喜欢。就《修道院纪事》这部小说,我一读再读,还因为我读的绝对是一个好译本。
傅小平:你说的是范维信的译本?
徐则臣:对,范维信先生的翻译是真好,你都不觉得是在读翻译小说,而是原本就用汉字写就的,他把一些只有汉字才能实现的美妙都传达出来了。所以,只要见到范先生的译本,我都买来读。平常重读 《修道院纪事》,随便翻,翻到哪页算哪页。
傅小平: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或许是因为这是一部可以从很多角度进入,“翻到哪页算哪页”的作品吧。
徐则臣:鲁尔福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我推崇他并不是因为《佩德罗·巴拉莫》,尽管我很喜欢这个小说,明白它的价值。我更看重他的短篇和他的短篇的精神。他的所有短篇里,没有任何两篇是相似的,一篇一个样,从结构到内容。这极其不容易,他给自己的写作制造了极大的难度。此外,他的小说艺术和脚下的大地结合得如此之完美,堪称典范。前年去了一趟墨西哥,此地此情此景,更觉得鲁尔福的伟大。
傅小平:这句话有启发,虽然说“脚下的大地”,会让人感觉比较抒情。
徐则臣:你起码可以向鲁尔福学学真正的“底层叙事”“三农文学”是什么样的。我们一度在炒作这些概念,但不见得明白多少。你看,在鲁尔福的小说里,你能看到作家本人独特的气质,看到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必然关系,也能看到作家和时代、作品和时代之间存在的那种几近完美的张力。很多人对鲁尔福包括对拉美其他文学的认识,更多的是停留在作品表面,对他们的借鉴和学习,也是从作品到作品,忽略了作品背后的作家和大地。鲁尔福对我的意义在于,他在气质、小说艺术、与时代关系、精神支撑等诸方面,是浑然一体的。
傅小平:要说小说与时代的关系,村上春树是一个典型。他该是捕捉到了时代的情绪,才会如此触动读者的心弦。但你分明为他的小说在中国如此受欢迎感到忧心。
徐则臣:看村上春树没有问题,但把村上春树看成文学的典范就需要存疑。就像拒绝写作的难度是作家的耻辱一样,拒绝阅读的难度同样也是可怕的。一个热衷于村上春树的民族和一个热衷于曹雪芹的民族,你觉得哪一个更有希望?任何东西都会有人在其中找到精神归宿,三级片和大字报也不例外。但我们不能听之任之纵容之,读者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被建构出来的。不能因为存在的就认为它是合理的、不可变更的,否则只能陷入相对主义。小说应该满足读者的需求,但不是一味地迎合,它不应该以平行甚至低于读者的水平来取悦大众,恰恰相反,应该高于或者稍高于水平线,让读者从中得到一些陌生的东西,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依次往上,大约才是当下文学的正途,而不是以不断降低读者智商为代价的泛滥的精神抚摸。
傅小平:说得也是。相比而言,萨拉马戈这样的作家,是适宜“取法乎上”的,他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构成了智力上的挑战。
徐则臣:当然,我喜欢萨拉马戈,还因为他和君特·格拉斯、库切、奈保尔、鲁迅一样,是我一直想成为的那种作家。
傅小平:要不是你亲口说,我都不敢相信,你居然把他们的作品都通读一遍。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阅读量,你想啊,就奈保尔一个人的著述中文版就达二三十种了。更何况即使是一个大师,也不见得每部都是精品。那为何要通读呢?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或许会说,通读一遍,你会明了一个作家的来路、过程和去处,也会明了他的优长和缺失之处。我想,以此对照自己的写作,会有一些启发的。
徐则臣:个人的阅读习惯,遇到一个喜欢的作家就要把他吃透,典型的强迫症。看他好在哪,为什么好;不好在哪,为什么有问题;看他如何一点点克服掉缺陷形成自身的优势。好和不好有时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你必须看进去,才能理解这一点。所以,我越来越不喜欢拿着一两部作品就信口给一个作家做结论,优劣都是局部,一个作家创作的所有作品勠力同心才能真正建构出他的完整形象和意义。每个好作家的成长史,都是一部优秀的写作教科书。现在网络和出版都发达,搜全一个作家的作品相对容易;很多年前不会上网,也没有这么多信息和资源,见到一本书上有一篇喜欢的某作家的作品,我会把整本书都买下来。或者托朋友在大图书馆复印,现在手头还存有很多作品的复印件。
傅小平:我想把这样的作家称为大作家,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不妨谈谈对“大作家”或“伟大作家”的理解。
徐则臣:我没法严格区分两者的界限。非要说,那就是莫名其妙地觉得加了个“伟”字就跟道德、匡扶救世、万世师表、时代楷模等正能量的东西联系起来了。凡文学有大成者,都是“大作家”,而当这“大作家”的影响溢出了文学,于世道人心、人类发展等有所增益时,他就既“大”且“伟”了。望文生义,瞎说哈。
傅小平:这么说来,你说想成为像那样的作家,是想习得他们写作里的某种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