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叙事文本的内在张力:以《促织》教学为例
作者: 代泽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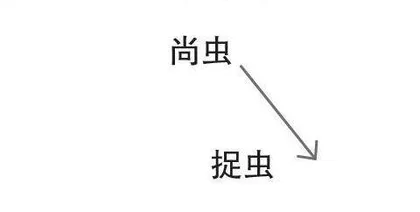
当代小说家毕飞宇评价蒲松龄短篇小说《促织》时说:“作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蒲松龄在极其有限的1700个字里铸就了《红楼梦》一般的史诗品格。读《促织》,犹如看苍山绵延,犹如听波涛汹涌。这是一句套话,说的人多了。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苍山是如何绵延的,波涛是如何汹涌的。”“苍山绵延”“波涛汹涌”是指《促织》在叙事上的起伏跌宕及读者在阅读中被调动的情感体验。这种情节的曲折是多数高中生能发现并理解的小说特色,可如何体会其中所具有的如苍山绵延、波涛汹涌般的美学趣味呢?
我让学生用最精炼的话概括《促织》每部分讲了什么,学生很快找到文本规律概括出了以“虫”为线索形成的“尚虫——捉虫——卜虫——得虫——死虫——丧子——复得虫——斗虫——斗鸡——献虫”的故事链,接下来我们一边细读各部分,一边根据情节发展与人物心理绘就一条折线图,这条折线也是读者情感体验的变化图。以“尚虫”为起点,“宫中尚促织之戏”,从宫人到县令、里长、市井人家,层层加码,直到成名一家成为目标对象,被逼交虫,读书人成名日日于草间寻虫却无所收获,最终被打得鲜血淋漓意欲寻死,倘以“尚虫”为成名一家心理波动的起点,那么从“尚虫”到“捉虫”成名的情感趋向就是一条下行线,即:
叙事文本中人物的死亡情节往往是低谷元素,通常是某一阶段的终结,蒲松龄将成名的欲死置于小说开始,那么而后就一定要有转机,所以这时村里来了一位神机妙算的驼背女巫,成名妻子前去求卜,得到一张绘有图画的谶纸,这是“卜虫”的过程。我问学生“卜虫”的折线图应该怎么画,落点应在什么位置,有的学生说应该与“捉虫”的落点在同一水平线,因为此时终究还是没有虫,所以成名的心情应该还是绝望的;有的学生说落点应比“捉虫”稍高一些,因为这时有了悬念,好像有可以得到虫的机会,心情应是因有期待而好一些,但又不能太高,毕竟还不知道能否如愿得虫,经过讨论我们决定采取后一种观点,于是折线图变为:
通过将人物情感具象化为可度量的图线,学生能清楚理会并表达出每种情感的走向变化程度与原因,所以接下来当成名拿着谶纸果真在村东大佛阁后的草石间找到一只“巨身修尾,青项金翅”的完美促织时,学生不约而同地要求一定要把“得虫”的落点定得高一点,我问为什么一定要高一点,不那么高不行吗?学生纷纷不同意:不高不足以显示此时的激动与兴奋,因为实在太难得了!本来要绝望自尽的人却突逢转机,还是在整个陕西境内不盛产促织的情况下,通过巫术这种传奇方式得到了一只极俊健的促织——是的,如果说找到促织这件事本身就是朝上的走向,那么由于这只促织又是凭借特殊方式意外得来、且各项条件异常优越,成名一家及读者的情绪便会加倍欣喜,所以“得虫”这条折线不但要向上,而且落点要较高:
至此小说叙事已完成了一轮抛物线——从正常到低谷再到高峰。我让学生仅借助目前的折线图来预测接下来的情节走向,几乎所有学生都说要下降,因为只有从高处落下才能曲折,找到完美的促织之后一定会发生变故使故事转向悲惨才能精彩。果然接下来成名的儿子因好奇想要看一看这只完美的促织却不慎将其拍死,这一情节在小说第五自然段,相较“捉虫”“卜虫”“得虫”,段落篇幅短小,也即在经历了漫长又痛苦的寻虫过程并最终得虫后,蒲松龄干脆利落、很“无情”地立马把这只“救命稻草”写死了,这时折线必然下行,可落在哪里?学生立马指出要在“捉虫”的落点之下,因为这种得而又失的心情必然比一直无所得要更加低沉绝望,所以小说在极短篇幅内迅速大起大落:
学生心情也随着这清晰的折线图起落,这时他们也如成名一家般不知如何是好,同时又极欲知道成名得知促织已死时会发生什么,他会怎么跟儿子算账?——怒火必然会造成极大的戏剧冲突,掀起情节上的小高潮,学生充满了期待。可再读下去却并非如此,学生的期待扑了个空:成名的儿子极度惊惧投井自杀!成名“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小说并没有如常规般掀起小高潮,而是继续下沉——可正是这意想不到的悖常在读者反应中构成了波折,这也正是蒲松龄卓绝叙事艺术的表现:以低谷做高潮。即使学生对怒火的期待成空,但并未造成阅读与审美缺憾,蒲松龄用巨大震惊和无言悲哀轻松填补了读者期待。我继续在折线图上添加“丧子”部分:
这时有学生提出质疑:“老师你画得太短了!‘死虫’情节的折线那么长,‘丧子’情节怎么才这么一点(长度)?”我还没说话已有学生抢先作答:“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不如虫。”这个回答精彩极了,在一个自上而下都被小小促织左右的社会,很难说成名夫妇此刻的悲哀中是对死虫的悲哀更多还是对丧子的悲哀更多,“丧子”情节的折线长度越短,其中的反讽与批判意味越强。
从叙事来看,小说走向已连续两次下行,如果说第一次下行是叙述规律的必然,第二次下行是小说家蒲松龄的艺术造诣,接下来必然要上扬。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有净化作用,悲剧的悲伤体验本质上是一种审美快感,可一旦没有限制便会失去美感与快感,只能带来恐怖与惊惧,这时丧失审美距离的艺术已不是艺术。所以成名的儿子到了半夜复活了,翌日成名又得到了一只促织,可作者并不着急,此时叙事节奏很轻很慢:儿子只是有了气息慢慢复苏,得到的促织也是“小”“劣”“形若土狗”,这既是作者对叙事规律的忠实,也是在为后文张本。我问第二次得虫落点应在哪里,讨论后学生认为应在第一次“捉虫”之上,因为毕竟是得虫,所以是喜悦的,但要在第一次“得虫”之下,因为这次得到的促织并不很完美,所以没那么喜悦,我又追问,与“尚虫”相比,落点孰高孰低?学生又陷入思考,一位学生的答案折服了大家,他认为应比“尚虫”低一些,因为起初什么都没发生时应是最普通的心理状态,现在尽管复得促织,但经历了前期“捉虫”“卜虫”“得虫”“死虫”“丧子”这些起伏巨大的折磨之后,成名一家的心情应是战战兢兢,他们已不可能是平稳正常的初始状态——又是一次精彩的回答,于是我们画下了“复得虫”的折线:
成名得到这只品相不佳的促织后害怕贸然进献不得圣意,于是想试斗一番,恰同村有一战无不胜的名虫“蟹壳青”,于是拉开了二虫相斗的序幕。从叙事来说,小说情节至此已有两个“U”形结构,但第二个“U”型的高潮还未来到,一战无不胜的名虫与一品相欠佳的小虫相斗,在亟需情节高潮的文本中必然是上行情节——看似不可能获胜者获胜,这是大多数文本引发高潮的技巧,学生也很熟悉,所以能轻松猜到,可如毕飞宇所说:“这一段写得极其精彩,可谓漫天彩霞,惊天动地。如果没有这一段,《促织》就不是《促织》,蒲松龄就不是蒲松龄了。”因为在这一段中“蒲松龄发明了文学的公鸡”。与前文蒲松龄使成名一家“死虫”又“丧子”出人意料地连续下行一样,蒲松龄在这里又使小说连续上行——这只小促织不但战胜了“蟹壳青”,更力叮逼退了一只意外闯入想要啄食它的大公鸡!至此小说又显传奇色彩,也进入令人拍案的高潮,我问这一段折线怎么画?学生说“斗鸡”的落点一定要高,要比“得虫”还高,情感不会说谎,他们清楚地体会到此次斗鸡的高潮要比第一次得虫的高潮高得多,因为这是经过了又一次生死与失去、经历了两次看似不可能而得来的高潮,为了这个高潮作者酝酿了很多。我追问除了落点要极高外其他部分怎么画,这时有学生说要有曲折,因为这个高潮前还有一个小高潮“斗虫”,同时“斗虫”与“斗鸡”都是先经历了不可能再到可能,所以是经过两次曲折再到顶点,而且坡度一定要陡,以显示高潮的急遽性与冲击性:
《促织》该部分的精彩程度在折线图中一目了然:于大波折中加小波折。成名将这只传奇促织进献上官,层层向上直抵皇宫,它不但一路斩将杀敌击败各类名虫,还能在宫中随乐起舞,皇帝龙颜大悦,向下层层嘉奖,从省台巡抚到县宰再到成名皆飞黄腾达,那“献虫”这一折线如何画呢?有学生说站在成名一家的角度此时心情是愉悦的,所以这条折线也应上行,可它的落点似乎又不应高于“斗鸡”,因为这明显不是情节高潮点,学生陷入困惑。
我很高兴学生发现了这一点,此前学生内心随小说人物同步起伏,主人公得虫时他们开心,死虫又丧子时他们悲伤,小促织战胜公鸡时他们激动,这里学生内心开始与成名一家分离,这是因为小说在传递情感的同时也呈现道德与价值。发迹以前成名一家是黑暗社会被压迫者的代表,作者站在悲惨人物一边书写,所写皆为被压迫者发言,出于披露与鞭挞,作者、读者与被压迫者有共同的对立面——人为虫死、人不如虫的社会及压迫者。在仅因为进献促织而“裘马过世家”时,读者虽会为成名一家摆脱厄运而宽心,但这来路蹊跷、过度夸张以致荒谬的奢靡富贵不但难以使读者苟同,反而使读者意识到其中的不合理性,此时的读者不能再与成名一家同心同行、心安理得地接受这样的富贵与社会,作者的批判意图自然使读者在这里与小说人物分道扬镳,所以“献虫”一节要读者与文本拉开距离、理性思考,展开道德与价值评判,它得是平缓的,给出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让读者评判,学生理解了自己困惑的原因,我把这条折线画成了水平方向:
“献虫”位于结尾,蒲松龄不动声色地在其中又引入了一个情节——“化虫”,原来这只其貌不扬却传奇无限的小促织是成名之子所化,他不慎拍死了父亲辛苦得来的完美促织,投井自杀,但死后不能安心,于是魂化促织,为父亲“大杀四方”并最终得来煊赫荣耀,读者猛然领悟传奇促织的真相——一份荒政下的真情。蒲松龄的处理极其简单,仿佛不经意带过,在皇帝自上而下、花团锦簇的层层褒奖中只有很淡然的一句“后岁余,成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这是一段插叙,我最后问学生“化虫”情节是否需要添加到折线图里?画到哪里?怎么画?我让学生静下来琢磨读完该情节的感受,并与之前做对比,于是发现,在原本最高潮的“斗鸡”情节后还有一个更高出些的部分“化虫”——真相的大白使小说带有解谜般的快感,文本的铺排越少,解谜的快感越大,因为留给读者的思考空间越大,读者的思考越多,感性体会与理性发现的体量也越大,蒲松龄简单克制的处理带来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阅读体验,不论从情节发展的推动力还是从带给读者的内心震荡来说,“化虫”都是最高潮的所在:
至此,《促织》的情节部分已阅读完毕,折线图也已绘成,凭这幅图就能明白何为“苍山绵延,波涛汹涌”,它本身就是苍山、就是波涛。通过在学生与文本间搭建支架,二者建立起了真实联系,削弱了隔膜,学生直观意识到了文本的叙事艺术,发现叙事的生成不是天经地义或随心所欲的,而是专业如科学般有自身规律的,何时升、何时降,为何升、为何降,如何使上升、沉降与转折更加精彩都有理可循。在这过程中学生的思维与情感始终紧随小说文本内在的叙事张力与节奏而变动,这反过来也可启迪学生设计自己的创作,变自发为自觉。文学是沉思的艺术,沉思是真实阅读、深度阅读,如何带学生进入真正的沉思,成为专业读者,积累经验,看到新世界,而非只用套话在文本浅表不痛不痒地“划水”,是每一次文学性教学都要用心思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