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声音
作者: 杨海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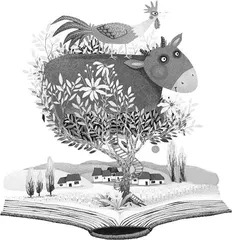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我很喜欢李商隐的这首《夜雨寄北》。因为诗人把一片深情和无限思念藏在巴山里,藏在秋夜里,藏在那哗啦哗啦或滴答滴答的雨声里。
说到雨声,我不由想起余光中先生在《听听那冷雨》中写的:“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普通人总是不喜欢雨季,不喜欢冷雨,可余光中先生不一样。他说:“雨不但可嗅,可观,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显然,作为游子的余光中先生把他的乡情融入雨声,哪怕是冷雨的声音。
其实,很多人都有自己怀念的声音,除了雨声,还有别的。“春君整天忙着家务,忙里偷闲,养了一群鸡鸭,又种了许多瓜豆蔬菜,有时还帮着我母亲纺纱织布。她夏天纺纱,总是在葡萄架下阴凉的地方,我有时回家,也喜欢在那里写字画画,听了她纺纱的声音,觉得聒耳可厌。后来我常常远游他乡,老来回忆,想听这种声音,已是不可再得。”这里的春君,是齐白石的结发妻子。两人伉俪情深,相伴六十余年。年轻时的齐白石听到纺纱声就心烦,老了却不能忘怀。为此,他还作诗一首:“山妻笑我负平生,世乱身衰重远行。年少厌闻难再得,葡萄阴下纺纱声。”纺纱声已是不可再得,可两人相濡以沫,也当心满意足了。
当代作家里,我比较亲近赵丽宏。在他的笔下,每一种“物”似乎都寄托着一段感情,留给人一份思索。譬如,他的《独轮车》中写道:“四五岁时跟大人到乡下去,农民用独轮车把我从码头送到村子里,一路上独轮车吱吱呀呀响个不停。这声音实在不怎么悦耳,像是一些老太婆尖着嗓门在那里不停地瞎叫嚷,听得人心烦。从码头到村子的路很长,耳边便不断地响着独轮车那尖厉而单调的声音。”一个人四五岁时的记忆也许不那么确切,但有的记忆确实刻骨铭心。那种木制的独轮车是乡间常有的运货工具,或在马路上,或在田埂上,慢慢腾腾,吱吱呀呀地响着。时过境迁,天地间许多“物”都在消逝。回首往事,赵丽宏由衷地感慨:“而独轮车,大概是很难复活了。只是那悠长而又凄厉的声音,却再也不会从我的心中消失,它们化成了属于我的音乐,时时在我的记忆中鸣响。这音乐能把我带到童年,带回到故乡。”
纺纱声也好,独轮车声也罢,是画家齐白石也好,是作家赵丽宏也罢,结果都相同——从此,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个声音了。人与人之间,有萍水相逢,有擦肩而过。想来,人与声音之间也是如此。
不过,既然人与人之间还有再次相逢,那么有的声音也可以失而复得。史铁生便有这样的经历。史铁生小时候随奶奶外出时,听到教堂的钟声,那“钟声沉稳、悠扬、飘飘荡荡,连接起晚霞与初月,扩展到天的深处,或地的尽头……”,可“不知何时,天空中的钟声已经停止,并且在这块土地上长久地消逝了”。四十年后,在另一座城市,在另一个地方,史铁生再次听见那样的钟声。对故乡,史铁生忽然有了新的理解:“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
似乎,声音往往跟故乡连在一起。我怀念的声音多数在老家,在一个叫杨家村的乡下。那个时候,一群野孩子在田里跑,山上闹,白天玩,晚上狂,没完没了,无拘无束,自然也听惯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日后读到“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还有“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压根儿不会听老师解释,自己早已心有领会,又心旌摇曳了。
如今,我久居城市,已经很少听到蝉噪、鸟鸣、蛙叫、鸦啼……夜深人静时,我想起以往,想起年少,虽然有忧郁,有伤感,但是并不悲观,不悔恨。要知道,那过去了的,不正是亲切的怀念吗?而这怀念里,还有关于声音的,也算是一种特别的福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