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调查研究工作
作者: 李慧 周心怡

邓小平早在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就指出:“要了解某个重大问题,必须调查各方面的情况。”(李慧:《邓小平左右江地区社会调查方法启示谈》,载《党的文献》2009年第3期)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延续和发展,是以黄松坚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云南、贵州和广西三省交界以及中越边境地区创建的坚持斗争时间最长、参与少数民族最多的苏区。根据地军民之所以能在远离党中央,甚至在较长时间内与上级党组织失联的情况下,能保留革命火种并坚持斗争达8年之久,其重要秘诀是重视调查研究、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但由于诸多原因,至今公开出版的权威读物中鲜有提及。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探讨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调查研究工作,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的讲话精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调研辟新道:跳出敌包围圈寻革命新基点
1930年冬,红七军主力北上后,韦拔群带领红二十一师继续坚持右江苏区的革命斗争。由于新桂系的多次“围剿”,如何保存革命力量成为党继续推进右江革命的首要问题。1931年8月,右江特委制定了“跳出敌人包围,向外发展”的计划,决定派一批党员骨干深入滇黔桂三省交界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寻找革命新的落脚点。1932年4月,韦拔群在东兰西山上弄所会议上提出:“到右江下游以后,应当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掌握我党、我军、群众、敌人的情况,然后从实际出发,制定工作方针,开展恢复根据地的农运、工运、学运等各项工作。”(中共广西百色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云南文山州委党史征集研究室,等:《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韦拔群提出的这一工作要求,奠定了发展右江革命新渠道工作的总基调,调查研究成为黄松坚等人开展工作的首要方法。
入滇桂边区发展革命力量富州位于滇桂交界区,因其位置偏僻,两省军阀鞭长莫及,是红军向外发展的理想路径之选。右江党组织曾先后派出3批骨干力量去富州开展调研。1931年11月,谭统南、黄庆金等人在刘家华的带领下进入富州七村九弄地区,他们深入谷留、弄洒、弄所等地的壮瑶寨子,通过拉家常、喝鸡血酒结拜等入乡随俗的方式开展群众工作,初步掌握了该地的群众基础等概况。1932年8月,右江下游党组织又派韦纪、韦天恒、朱鹤云等人进入富州的剥隘、洞波、那能等地调研富州革命形势。1932年年末,右江下游党组织派出李家祺、赵敏等第三批红军干部进入富州县城、皈朝镇和百油村等地,通过多种渠道传播革命思想和发动群众。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红军在云南花甲、那耶等地成立了兄弟会等群众组织,还以保护乡寨的名义建立了赤卫队等半公开的革命武装,团结争取了部分开明地主和乡绅,说服教育争取到以梁振标为首的绿林武装,组建了600多人的游击队,逐步打开了滇桂边区的工作局面。
深入黔桂边区传播革命火种1932年4月,黄举平、韦星高等15人装扮成商贩,从西山出发,沿途考察黔桂边区的地形特点和交通路线。他们依托商贩的身份走街串巷,深入地方探查敌情,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动员群众起来闹革命,为新区的开辟奠定群众基础。黄举平等中共党人认为,黔桂边境的林友屯山高谷深,交通闭塞,是两省军阀势力不及之处,在黔桂边境开辟根据地是可行的。随即黄举平、黄鸿腾一行又乔装成游商来到黔桂边境,在罗甸、贞丰和望谟等地调研,了解到地方实力派陈秀卿虽然在罗甸等地称霸,但他深受国民党军阀欺压,加之又逢军阀进军罗甸,侵犯了陈秀卿的利益,双方矛盾更加尖锐。据此,黄举平指示黄伯尧和黄衡球乔装成游客,秘密接触陈秀卿,向陈秀卿建议收留从东兰上贵州避难的广西地方实力派韦万灵,并帮助陈秀卿渡过难关,赢得陈秀卿的信任和支持,为党组织在贵州的活动开辟了落脚点。
重回右江流域点燃革命火焰1931年4月,黄松坚带领30余名党员骨干在思林县古芬村调研达20天之久,了解到“右江下游各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和革命干部已分散隐秘到农村工作,群众组织已经没有什么活动”(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青松高洁——黄松坚史料专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为此,黄松坚、滕国栋等人提出“以巩固求发展,相机消灭敌人”的工作方针。在仔细摸排果德、那马、向都等地党员的思想情况和党组织建设情况后,他们对各地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进行分类指导。6月,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委员会和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成立,负责领导右江下游、红河下游和滇桂边、中越边的革命活动,重燃右江下游革命火焰。为恢复和建立右江上游党组织,黄举平乔装成瑶胞,深入西山对社会各阶级的思想状况进行考察,培养出一批先进分子;通过打老庚(又称“打老同”)、喝交杯酒等形式获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在各乡和村寨成立青年同盟会、劳农会和杀奸团等组织,严惩西山的恶霸和反动势力,建立“西山—海亭—洪力—中亭—天峨更新—乐业—逻沙—雅长—贵州板陈”联络站,右江上游的革命火焰重新燃起。
调研开新局:紧抓统战工作扩大革命武装
1933年,黄松坚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指出:“那里的反动统治阶级经常在少数民族之间挑拨离间制造隔阂、扩大矛盾,挑动民族间互相仇杀、械斗而从中得利。”(《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返回右江后,黄松坚根据党中央指示并结合右江革命实际,把统一战线工作作为边区工作的重点。后来,黄松坚回忆说:“那时的搞法是,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只要你是爱国的,拥护革命、反对国民党的,拥护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的,我们都组织起来。”(《青松高洁——黄松坚史料专辑》)滇黔桂边区党组织创造性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争取和改造收编了一批绿林武装、少数民族武装、地方实力派,还灵活开展兵运,争取了一批国民党军队,革命形势不断好转。
争取绿林武装,发展革命盟军韦拔群认为开辟新区要“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团结进步人员,争取中立者,和他们打老庚、交朋友、孤立顽固的反动派,开展工运、农运、商运、学运、兵运等工作”(《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自1931年秋起,中共右江特委多次派谭统南、黄松坚、黄举平等人去滇黔桂三省交界地区调研。他们了解到两个信息:第一,此处山高林密,土官多、士兵多,土匪也多,有几十股土匪在此占山为王,其中以韦高振、梁振标两股绿林武装势力最大,其他土匪既依附于势力最大的头领,又各自为政。且这些绿林武装打远不打近,打大不打小,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第二,从绿林武装的政治态度来看,一部分土匪只劫富不伤贫;一部分土匪是被迫落草,如活动在靖西中越边境一带的韦高振绿林武装,一度被桂系收编,但因同桂系矛盾重重,韦高振多次直接率部脱离桂军返回靖西。右江独立师党委高度重视对韦高振部的争取改造工作,鉴于韦高振有担心投靠桂系被吃掉的矛盾心理,谭统南逐步深入引导,一边揭露桂系军阀的罪行,一边指出任何武装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去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才有前途。此外,他们还对黔桂边王海平、滇桂边梁振标等绿林武装开展统战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统战工作,不断改造两股绿林武装,收编他们参加红军游击队,红军在滇黔桂边站稳了脚跟。
争取少数民族武装,壮大革命队伍广南县牛滚塘的苗族头领王开洪和王咪章在当地群众中有较大影响力,争取这一支武装力量对于党和红军巩固壮大边区力量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大量走访调查,边区党组织了解到,王开洪深受地方当局勒索和欺压,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迫不得已策划组织农民共同进行武装反抗。在得知王开洪的起义计划后,黄松坚派黄树功和陈勋等干部多次前往牛滚塘与王开洪、王咪章接触,了解情况,立足民族平等原则,向牛滚塘二王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在党组织的帮助下,王开洪顺利起义,在和游击队合作抵抗八宝区守备军进攻的过程中,王开洪被红军严明的组织纪律和对群众的关怀行为所感动,主动请求红军收编。随后,党组织派遣陈尧宝多次深入牛滚塘开展调查,陈尧宝在扎实掌握王开洪武装详情后向党组织反映,党组织将其收编为“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牛滚塘独立大队”,王开洪武装成为红军的队伍。

争取地方实力派,夯实革命基础边区党组织非常重视兵运工作,派出党员骨干深入白区开展调查,策动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何之奇等部和桂系罗伯连的部分士兵倒戈;1933年初步争取到贵州板陈地方实力派王海平的合作意愿,但其归顺红军的决心不够坚定。1935年,黄唤民和黄世新一行人来到黔桂边,经过长达4天的谈话后,了解到王海平认可红军是一支好队伍,但因其曾派部攻打红军而心存余虑。黄唤民等人以此为突破口,向王海平宣传党的革命理念,打消了其“害怕红军报复”的顾虑,促使王海平真心实意和红军合作,成为红军事业的忠实支持者,协力为边区革命作出重要贡献。
广泛结交群众,增强革命力量对于边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党组织运用“造福群众,广泛交友”的方法,学习本地民族语言,与当地群众交流,拉近关系,增进感情。壮族干部黄举平在西山工作时,常用一口流利的瑶语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纲领,快速争取到当地群众对革命的支持。边区党员干部还以各种职业为掩护,与群众打老同、认亲家、喝鸡血酒,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国民党强征苛捐杂税的恶劣行径和民族间的歧视与压迫,并逐步建立起兄弟会、同盟小组、革命农民等党群组织。在统战工作的持续推进下,各地革命武装迅速成长起来。继1934年11月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成立后,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各级机关也相继建立起来,革命火焰在滇黔桂边区形成了燎原之势。“据统计,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先后培养了1200多名少数民族干部,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毛宽海:《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研究》,2018年云南大学硕士论文)
调研施新策:因地制宜巩固新根据地
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创建后,国民党当局多次“围剿”破坏。为巩固和发展边区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实际,大力发展边区政权组织、建设边区经济、开展宣传教育。
强化党组织建设以巩固政权毛泽东指出:“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还需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研究》)1933年10月,党委扩大会议在弄法召开,黄松坚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整顿恢复党组织,发展壮大党的队伍,把党支部建设成坚强的战斗堡垒”(《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目标要求。针对富州本地干部缺乏党员的实际情况,黄松坚经过充分考察后,将当地干部刘家华、傅少华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并介绍入党。滇黔桂边区党组织相继建立和恢复,至1937年,成立支部以上的党组织44个,党员人数扩增至600人。边区各级党组织通过不断开办党员干部培训班,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并通过开展支部生活会等方式,保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因地制宜开展边区经济建设朱鹤云在滇黔桂边区调查报告中对边区的经济状况做了介绍,“农民收到军阀地主豪绅高利贷之残酷压迫:县政府征收盐税每人每月二角(合铜版60—70),至于人民有无盐吃则在所不顾;高利贷之利率为20%,故□米之利息为高!……农民生活之苦,老是只单衣一身冬夏皆然,吃包谷粉,菜只有辣椒,油很少有人吃起,甚或盐都吃不到!生活之苦可以想见!”(《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可以看出,民生凋敝、满目疮痍是滇黔桂边区经济的突出实情。边区党组织在沿用原右江苏区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动员群众反对国民政府强征苛捐杂税的恶劣行径,因地制宜开展边区经济建设:一是进行土地革命试点工作。富州地区虽有2000多亩良田,但大多数被地主豪绅强占,农民只能在贫瘠的土地上耕作。由于村寨分布较为分散,边区党组织力量薄弱,进行大规模土地革命容易引起反动势力的注意,边区党组织便在条件较为成熟的富州一带进行土地革命试点工作。二是探索“以农养兵”的经济发展模式。为解决军队给养问题,红军采取“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和“以农养兵”的措施,在边区通过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开设集市交换农副产品等方式获得物资补给,如“牙永平把连队带进高山密林,建造了一栋5间的两层楼房,并开垦了约300亩地”(《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据统计,1932年至1937年,群众除了向游击队捐款3万余元,还捐献了粮食70万余斤、猪2000多头、枪1000多支,充分体现了边区军民的鱼水之情。
着眼实际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滇黔桂边区很多村寨位置偏僻,农民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党的宣传工作滞后。朱鹤云在调查报告中指出,边区农民“有病则信鬼而不信药,每有巫女唱土歌驱鬼则有数十青年男女和之”,“宣传工作是做得非常不够,过去的说教,群众还知道一点,现在宣传抗日了,大家却没有办法把它同群众切身痛苦联系起来!”(《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这决定了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边区党组织着眼实际施策,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一是实行平民教育,提高群众认识。据调查,边区“只有少数较大的村寨中有私塾,很多求学者不辞劳苦,步行数十里方能到私塾中求学。三十年代初,偌大的‘下江片区’没有一所公立学校”(《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在边区创办学校,实行平民教育,并把红军游击队的标语、口号、宣传文件和红色山歌作为教材内容,如富州等地开办的农民夜校,以原右江苏区的《工农兵识字课本》为主要教材,创强小学将报刊的抗日宣传文章改编成教材。二是结合民族特色开展宣传工作。边区党员骨干以标语口号、山歌对唱、写词作赋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传工作。1935年,黄松坚、梁振标在富宁皈朝游击队整编当日发表动员讲话说,共产党是领导人民大众翻身求解放的,是领导穷人打土豪、打国民党反动派、打军阀、打贪官污吏的,是人民的救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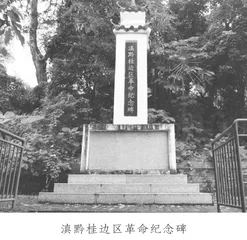
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党员干部用调研行动诠释了以求真务实为核心的苏区精神。当前我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时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发扬调查研究这一党的传家宝,推动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任务不同,但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调研范式和思路,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如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接续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实践经验借鉴。文
【李慧系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周心怡系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本文所属研究项目: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红军在广西开展社会调查活动的历史考察研究”(19YJA710020)、2020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滇黔桂边区苏区精神研究”(20FDJ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