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座中央图书馆
作者: 周文洋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在瑞金建立第一个全国性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下简称“中央政府”)。当时,红色根据地(以下简称“苏区”)已拓展到赣南、闽西20多个县,辖域5万余平方公里,有人口250多万,工农红军5万余人。
由于苏区地处偏远,百姓生活困苦、文化落后,90%以上的民众都是文盲。大多红军战士家境贫寒,读不起书,目不识丁,他们虽立场坚定、斗志高昂,但许多人对党的方针政策缺乏了解,对国家前途命运所知甚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成立之前,苏区各级党组织已认识到提升民众文化素质、建立文化机构的重要性。1927年9月,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在发布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行动政纲》中提出:“极力增进工人、农民及一般平民的知识和娱乐,开办校外的教育机关(如图书馆……)。”1930年9月,上杭苏维埃政府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也表示:“实行免费教育,编制教材,开办报馆及教育人才训练班,设立图书馆,阅报社……”但这些都因缺少稳定的社会环境、充裕的物质条件等均未得实施。
筹建:缴书、征书、购书
1932年4月20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率红军攻克闽南重镇漳州,收缴战利物资时,在漳州高中发现3000多册图书。毛泽东命令将书全部运回瑞金,请来时任教育部代理部长的徐特立,商讨创办一座属于中央政府的图书馆。
徐特立见到缴获的图书非常高兴,兴奋过后认真地对毛泽东说:“如是阅读和收藏,这些书已很可观,但要建一座图书馆还远远不够,要继续收缴,多多益善。”
依照徐特立建议,毛泽东在签发《关于扩大红军的通告》中加入“在攻打城市时,发现所有书籍一律上交,不可以就地销毁,因为大部分书籍可以拿来为我党所用”的内容。红军各部队遵照通告要求,每占领一座县城都特别注意搜查学校、书店等,见到书刊立即封存,派专人整理、保护。红军攻克兴国、于都、广昌等县城,共收缴书刊近万册,足足装满20多个麻袋。这些书刊集中送到瑞金,徐特立觉得书的数量虽已满足成立图书馆的需求,但还必须分类整理,统计图书书目,补充所缺书籍。毛泽东听了徐特立的意见,说:“干部群众学文化是当务之急,图书馆应该先办起来,分类可以边干边分,没有的再想办法收集嘛。”
按毛泽东的指示,1932年6月,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以下简称“中央图书馆”)在瑞金叶坪村挂牌,从部队、机关选拔出20多名政治素质、文化水平俱佳的战士、干部组成图书馆工作团队,徐特立任馆长。
中央图书馆坐落在一个叫“熬厅子”的大院,有20多个房间,当大家在宽敞明亮的阅览室里整理书籍时,发现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书刊,极少有马列著作、革命理论、阶级斗争等方面的红色图书,难以满足苏区读者的需要。
徐特立又向毛泽东建议:“可以动员苏区机关、学校、部队和个人捐赠红色图书。”毛泽东觉得这建议可行,就亲自审定中央图书馆的《征书启事》。《征书启事》刊登在1932年9月6日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为着充分给革命工作的参考需要,给予提高革命同志的文化水平起见,极力扩充内容材料,增加革命图书,向诸位同志及革命团体征求赠书,倘有特别优良图书将出售者,可函知本馆,在可能条件下采购,亦所欢迎的。”
《征书启事》得到广泛响应,当时,少共(共青团)中央局正准备建立少共图书馆,看到《征书启事》,少共中央书记顾作霖以大局为重,决定缓办少共图书馆,将现存的3000多册图书全部捐献;红军子弟小学号召全体师生踊跃捐书,不到10天就收集到红色图书900多册……
1932年9月至11月,中央图书馆先后收到各界和个人捐书约1.2万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在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拨给中央图书馆3000块银元购书专款,徐特立利用中华苏维埃钨矿总公司与广东军阀陈济棠有钨矿石交易的机会,派人搭乘矿石运输船前往广州、珠海等地采购人文历史、医疗保健、农业技艺等方面的图书5000多册,极大地丰富了馆存和借阅图书的种类范围。
经营:管书、借书、护书
中央图书馆的主要创办者、领导人徐特立思维观念新、创造意识强,他不照搬曾组建图书馆的老经验、旧模式,而是根据苏区的社会现状、发展趋势,制定切合实际的管理办法,设计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徐特立带领工作团队夜以继日地对全部图书进行整理,分成革命理论、社会经济、农业科普、文化知识等20多个类别,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共产党宣言》《劳动经济论》《新经济学方法论》《种子学新编》《农艺学》《成人读本》《识字课本》等数万本图书一册册填写类别索引、书目卡片,供阅读者、借阅者查询,同时制定出管理条例、阅览须知、借阅规则等一系列便于执行、易于操作的规章条例。如借阅规则详细规定“馆存书籍一律外借,有教学、办班、会议等特殊需要可以批量借阅;借阅的个人或团体,须持隶属单位或苏维埃政府介绍信;借阅期限为2周,有特殊原因逾期最多不得超4周;超越规定2周不还者,通知其单位协助追收”等内容。这些硬性条规既照顾到红军频繁转移还书不便的困难,也考虑到机关干部经常集体学习的情况,还有的需要人手一册等特点,深得读者赞誉。
富有苏区特色的图书管理条例、阅览须知、借阅规则等图书馆运营管理制度的创建与实践,为红色政权图书馆建设积累宝贵经验。5年后的1937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中山图书馆,沿用的就是这套规章制度和管理模式。
他们在建章立制的同时,对图书的存藏和保护也提出严格要求,例如,“破损的封面、书脊要加包封皮或粘好;不许在书页上圈点批注、折叠;不许散乱存放,要防雨、防潮、防霉、防蛀;每册封面须加盖‘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藏书章’等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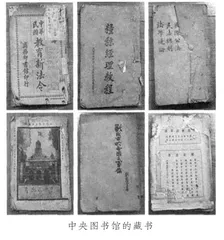
有一次,徐特立去一个村办事,走到一座青砖门楼前,忽然看到院子里农民正围着一堆书报着手焚烧,他即刻进院子喝止。原来,村里正在打土豪,在这家劣绅的库房中搜出许多书报,农会干部认为没用,便下令烧毁。
徐特立急忙找来村农会干部,表明自己的身份,耐心地对他宣讲书报在提高苏区群众文化素质、政治觉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要求把书刊暂存在农会,过几天派人来运走。
中央图书馆得到这批书报后,立即进行清理,对有用书籍分类归档,对破损的旧报纸也不丢弃,把有价值的、完整的文章裁剪下来,分门别类粘贴成册,存放到资料室。
一次,图书馆从民间征集来一套4册线装古籍《四书句解》,由于岁久年深,古书的订线朽断,许多页码散乱、破损,徐特立带领工作团队用了2天时间,将书页一张张整理、粘贴完好,重新装订,上架借阅。
成效:读书、讲书、用书
瑞金没有电影院、俱乐部等文化设施,中央图书馆就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读书识字成为一种时尚。熬厅子门前经常有人持书高声诵读,周边围着一群听众。许多党政军干部、战士是为书光顾,也有不少群众到此是要见一见来看书、借书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苏区领导人。
为便利读者,中央图书馆将闭馆时间延至晚上11点,夜里没有电灯,就用汽灯、马灯、油灯照明。当年居住在中央图书馆隔壁的谢成福老人回忆说:“‘熬厅子’的凳子经常不够坐,读书的人屋里挤不下了,许多人就在厅子外看书。”
1957年,毛泽东回忆自己当年在瑞金的读书生活时说:“1932年,将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列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就向图书馆和一些同志借。我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矛盾论》《实践论》的思想和观点,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1932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目前我们的宣传鼓动形式,只是限制于传单与标语这些死的文字,而没有考虑到苏区大部分群众都是文盲的现实。应该充分发展俱乐部和列宁室的读书、讲演工作,吸收群众积极参与进来,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为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指示精神,中央图书馆组成5个助读小分队,深入苏区各乡、村,协助成立俱乐部、列宁室,组织读报团,培养团员既做图书管理员、讲解员,又当识字教员、政策咨询员。毛泽东在一篇调查报告中记述:“读报团设于俱乐部内,有一主任,逢圩日(五日一圩)读《斗争》《红色中华》《阶级分析》等,每次最少五六十人听,多的八九十人。”
中央图书馆还在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开办成人文化补习室、读书识字班,号召乡、村建立颇似如今乡村阅览室、农家书屋的俱乐部、列宁室,在广大农民中普及文化知识,提高他们对读书的关注和兴趣。
1933年2月19日出刊的《青年实话》第2卷登载的《在列宁室》一文,真实地描述了列宁室读书活动的场景:“你看‘红色中华’,我读‘青年实话’,他跑来笑哈哈!‘列宁室’真好呀!来,我问你,不管是军事还是政治,你答得有道理,我奖你一朵大红花!”
据不完全统计,1934年,在苏区的乡村共建起俱乐部、列宁室1656个,有读报团1000多个。崇学尚读蔚然成风,劳苦大众学文化、长知识,投身革命、建设家乡的热情空前高涨。
中央图书馆除致力于阅读、讲解服务,还将学以致用作为工作重点。每当中央机关、红军部队、各学校举办重大政治理论学习,开展革命教育、知识竞赛等活动,中央图书馆都要备齐相应的书籍,供活动主办单位、参与的个人借阅、查询,甚至有些军事行动也含有书的功劳。
红军总司令朱德曾要求指挥员:“战斗前要多看看书里的战法、战例,虽不能照着书本打仗,但一定能得到启发。”粟裕也说:“管什么‘纸上谈兵’‘书上谈兵’打法,只要打得胜,就是好打法!”
1932年5月,红四军团得到情报:国民党一个团兵力准备向苏区发动进攻,必须途经一条长约1公里的峡谷。军团参谋长粟裕仔细视察地形后,命令红一师第二团伏击敌人,并在战前召开二团排、连以上干部会议。他手持《战术讲授录》,根据书中对伏击战的要求,边在黑板上画地形示意图,边布置迫击炮摆在哪里、地雷埋在何处、架设机枪的位置……有人说这是纸上谈兵的打法,但在战斗中,每个指战员都清楚自己的位置,知道仗该怎么打,结果大获全胜,歼敌1000余人,缴获了大量枪械、物资。
充实:写书、编书、出书
1933年,经常来中央图书馆借书的毛泽东听到反映:目前国民党对苏区严密封锁,许多农村干部不知道如何在艰苦环境中建设、巩固红色政权,一些地方的农会出现人心涣散、工作停滞状态。
为此,毛泽东深入上杭县才溪乡走访调查,总结出这个乡土地革命、民主建政、执政为民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写出《才溪乡调查》交给中央出版局印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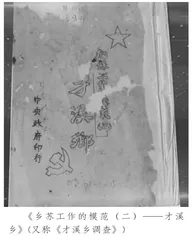
极具启发性、指导性、实用性的《才溪乡调查》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中央图书馆摆上书架的100册不到3天就被借阅一空,苏区的每个俱乐部、列宁室都借走10~20册,召集农村干部、群众阅读、宣讲。
1933年至1934年,毛泽东撰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都是中央图书馆阅览次数最多、借阅量最高的书籍。
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也经常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来中央图书馆调研,部署安排房舍维修、书架增设、书籍保护等工作,鼓励大家要“充分利用图书宣传党的革命思想和斗争策略,增强党在斗争中的领导力和凝聚力,为提高干部群众的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提供有力帮助”。
中央出版局局长张人亚经常邀徐特立到苏区机关、学校、工厂和红军部队了解干部、群众与战士想读什么书,最欢迎哪些书。通过深入走访调查,了解了大众需要,张人亚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编辑、出版了《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左派”幼稚病》《战术讲授录》等政治、军事著作20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