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艺术“卫士”常书鸿
作者: 叶介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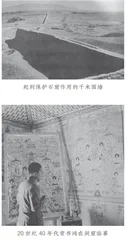
常书鸿(1904-1994),满族,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中国著名画家、敦煌学学者。他在生活环境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历尽千辛万苦,为保护、研究敦煌艺术默默地工作和奋斗50年,被誉为敦煌艺术的“卫士”、人类艺术宝库的“守护神”。
奔赴敦煌
1936年9月,留学法国的常书鸿回到祖国,受聘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40年冬,该校迁往重庆,后解聘了一批教授,常书鸿也在其中。年底教育部成立美术教育委员会,常书鸿被聘为委员兼秘书。在此期间,他创作大量油画,先后在成都、重庆举办个人画展。
1942年,围绕洛阳龙门石窟浮雕被奸商盗卖事件,重庆文化界热议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问题,对包括敦煌石窟历次所遭受的劫掠破坏及现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批评和建议。迫于形势,国民党政府指令教育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在文化界物色人选。
陈凌云与常书鸿在法留学时就认识,当时在监察院任参事,他与常书鸿谈起去敦煌筹办研究所一事,并透露准备让常书鸿担任筹委会副主任的消息。常书鸿接受了这一邀请,随即与梁思成、徐悲鸿等商讨此事。梁思成和徐悲鸿都十分支持常书鸿。徐悲鸿鼓励他说,从事艺术工作的人,要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要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做到底。
在去敦煌前,常书鸿拜访了当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于右任曾于1940年在西北考察时专程前往敦煌莫高窟参观,认为莫高窟作为民族艺术宝库,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考察结束后,即打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募大学艺术学生,寓保管于研究之中。他对常书鸿立志去敦煌莫高窟从事文物的研究与保护工作十分赞赏,建议常书鸿去敦煌后,可以就建立“边疆民族文化学院”提出建设性意见。
承担筹委会的筹备任务后,常书鸿立即着手工作班子的组建和经费的落实工作。教育部只拨给5万元(旧币,下同)开办费,离实际需要相差甚远,大量的还要靠自筹,为此,常书鸿决定开画展卖画、卖家具,典当行李,发誓做破釜沉舟的打算。他在离开重庆前的画展上,共展出40余幅油画,徐悲鸿为画展作序。徐悲鸿还抱病前来,赠《五鸡图》以做纪念。画展作品售出不少,筹得西行必需的几万元经费。
1942年8月,重庆报纸公开报道“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即将筹备成立的消息,公布了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由7人组成: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委员,常书鸿任副主任委员,王子云任秘书,张庚田、郑通知、张大干、窦景椿等任委员。
是年冬,一个浓雾弥漫的早晨,常书鸿告别妻子、儿女,离开重庆,来到西北高原的兰州。高一涵主持,在兰州召开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会议,初步决定筹备计划。当时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所址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人主张把所址设在兰州,常书鸿坚决不同意,认为兰州距敦煌1200公里,这么远怎么搞保护和研究呢?他提出把所址设在敦煌千佛洞。有的官员一提起塞外戈壁滩就谈虎色变,有人还引用古诗“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向南飞”,伤感地表示敦煌不能去。常书鸿向于右任反映这一意见,于右任支持常书鸿,提出建立研究所是寓保护于研究,所以不能离开千佛洞的建议。这样一来就得罪了兰州一些官员,他们对常书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人员配备、图书器材、绘画材料等得不到解决,工作难以展开。
常书鸿毫不气馁,继续寻找愿去敦煌的专业人才。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在西北公路局工作的原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生龚祥礼,龚祥礼当即表示愿意去敦煌工作。龚祥礼帮助凑起6人的班底,又设法买来笔、墨、纸、颜料等工作必需品。常书鸿喜出望外,对大家说,不要小看这点可怜的家底,只要齐心协力、艰苦奋斗,照样能做成一番大事业。
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和龚祥礼、李赞廷、陈延儒、辛普德、刘荣曾一行6人乘一辆破旧卡车,开始西行敦煌的征程。他们从兰州出发,沿古代丝绸之路西行,进入祁连山脉之后,地势渐高,气候更加寒冷,沿途人烟稀少,原野荒凉。由于汽车破旧,路上时常抛锚,步行仅需半个月的行程,汽车却走了一个来月,才好不容易到了安西。
从安西到敦煌,连破旧的公路也没有,一眼望去,只见一堆堆沙丘和零零落落的骆驼刺、芨芨草,活像一片巨大的荒坟葬场。汽车不能走了,只好靠骆驼帮忙,他们以每天15公里的速度艰难缓慢地前进。沿途缺食少水、风餐露宿,人人口干舌燥,满脸尘垢。终于在一天,太阳从三危山高峰升起的时候,“骆驼客”告诉他们,千佛洞就要到了。他们沿“骆驼客”手指的方向望去,透过白杨树梢,看到悬崖峭壁上像峰房一样的石窟。灿烂的阳光,照耀在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此情此景令常书鸿陶醉,一股发自肺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他们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疲劳,一齐跳下骆驼,向着向往已久的民族艺术宝库跑去。
抢救石窟文物
敦煌是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最西面的一个,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石窟群包括存在于敦煌方圆几百公里范围内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水峡口小千佛洞、敦煌西千佛洞等,其中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保留的洞窟、壁画、彩塑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跨越时代最长,保存情况也比较好。
莫高窟始建于366年,从十六国到魏、隋、唐、宋、元,历代都在这里凿窟、塑像,以唐代最为繁荣。根据唐代碑文记载,当时有窟、龛1000余个,现在保留700余个,其中有壁画、塑像洞窟492个,共有彩塑2000余身,壁画44830平方米。
1900年5月,居住下寺的道士王园禄发现第17窟的藏经洞,这是在1035年时,为逃避西夏入侵抢掠,莫高窟和尚和当地豪绅把历代宝藏、经卷、画幅、古文艺抄本、契约等3万余件文物封藏起来的。王园禄上报清廷后却无人过问。
1907年和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两次窜到千佛洞,贿通王园禄,盗走丝绢、织造、绣像等150余幅,绘画500余幅,图书、经卷等6500余件。此后,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柯斯洛夫、日本的橘瑞超等接踵而来,先后盗走手抄经卷、绣像、幡画、卷轴等文物万余件。美国的华尔纳用化学药品粘去壁画20余幅,并搬走最精美的彩塑,敦煌文物遭到严重损失。
国内的军阀官僚也对敦煌文物垂涎三尺。1940年,军阀马步芳派一个步兵连,把敦煌石窟封锁三天三夜,盗走五代银质宝塔、宋代白瓷瓶、经卷等不少珍贵文物,而且破坏了唐元时期的许多佛塔基座。
面对祖国宝库被帝国主义、军阀官僚掠夺破坏的累累伤痕,常书鸿悲愤交集,痛下决心,要守护敦煌一辈子,绝不让以前的悲剧重演。
1943年3月24日,常书鸿等6人在千佛洞中寺破庙的土炕吃了一顿晚餐,这也是他们到敦煌后的第一顿晚餐。他们用来照明的是从老喇嘛那里借来的木制油灯,筷子是用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成的,吃的是河水煮的半生不熟的面片。这是他们新生活的开始。
戈壁滩的气候十分恶劣,变化无常。夏天沙漠气温高达60摄氏度,冬季最冷可达零下20摄氏度,滴水成冰。常书鸿他们的办公室设在中寺皇庆寺破庙内,宿舍是马厩改造的。桌、凳、床全是用土堆成的,没有取暖设备。这里人烟稀少,邻居只有上寺的两个喇嘛和下寺的一个老道。最近的村舍也在15公里的戈壁滩外。一切生活用品都需要到县城去买,往返七八十公里,至少得走一天一夜,而他们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一辆借来的木轮老牛车。
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沙。由于年久失修,无人管理,许多洞窟内及其通道上积满流沙,不少洞窟已被流沙淹没,要到洞内工作首先要清除这些流沙。堆积的流沙大约有10万立方米,如果雇用民工清理,至少得花300万元。这对只有5万元开办费的常书鸿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好在大家情绪很高,雇不起民工就自己干,他们用自制的刮沙板,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推,一点点地把沙推到水渠边,然后再用水把沙冲走。他们前后用了两年时间,加上少量民工,终于把流沙清除。
他们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筑墙。为了防止人畜破坏和风沙袭击,需要建造一道两公里长的围墙,把石窟群围起来。当常书鸿把这一设想向敦煌县的县长提出时,县长哈哈大笑,挖苦他,说他大概是书念得太多了,真是一个书呆子;说这是戈壁滩,除了沙子没别的,没有土怎么筑墙,要修这么高这么长的围墙,简直比修万里长城还难!
常书鸿受了奚落,但并不灰心。他想,古人可以在这里建窟,修庙,创造如此辉煌的艺术宝库,他们的子孙为什么不能修一道保护宝库的围墙呢?
不久,千佛洞一年一度纪念佛祖生日(农历四月初八)的庙会开始了,人们从很远的四面八方赶来,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庙会上,常书鸿看到有人用沙土加水夯实筑起墙,用作临时小卖店,经询问得知,千佛洞附近的水碱性大,加沙夯实作墙很结实。常书鸿以此为由再次去县里交涉,坚持要他们去千佛洞看看,并说,如果不筑围墙,以后石窟再受损失由县里负责。县长怕负责任,勉强同意派人去研究修墙计划,经常书鸿多次交涉,后又派来民工。常书鸿等人和民工一起,起早贪黑干了50余天,总算筑起一道2米高、1000米长的围墙。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县里和研究所联合发出布告,宣布莫高窟正式收归国有,禁止在附近放牧和私自进洞。至此,石窟清理及外部环境保护工作告一段落。
常书鸿根据筹委会通过的敦煌艺术保护研究计划大纲和实际情况,决定首先进行测绘石窟图、洞窟内容调查、石窟编号、壁画临摹等几项工作。
为了进洞工作,首先要清理、修补通往各洞及各洞连接的栈道。原来的栈道由于年久失修,有的腐朽、有的倒椽、有的堵塞,在没钱雇人的情况下,他们决定自己干。他们用水夯沙做土坯,打桩、钉架、筑垒,两个多月时间,修补好简易栈道,为进洞开展工作做好准备。
调查工作本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由于没有必要的工具也变得复杂起来,有时还出现险情。当时没有长梯,他们只好把几个小梯子接起来用,人爬上去歪歪扭扭、摇摇晃晃,提心吊胆。后来大家想办法,用一根长的杨树椽子,每隔30厘米钉1根横木,做成简易“蜈蚣梯”,攀登时手脚并用。有一次常书鸿等攀上半悬在30多米高岩壁上的9层楼高的196号窟,工作完毕准备下来时,不知谁把梯子碰倒,大家被困在洞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多亏工人窦占彪有经验,弯腰弓背十分敏捷地爬上山顶拿来绳子。为了给大家增加信心,常书鸿大着胆子想试试,没跨出几步,由于岩壁硬,脚的蹬力过大,一个站不稳,差点摔下来。惊慌之中,他的一本调查记录本飘飘荡荡地落到崖下。后来还是窦占彪把他们一个个慢慢拉上山顶。
对于这些专业绘画人员来说,壁画临摹并不是难事,困难的是缺材料。首先是纸、笔、颜料,附近无处买,他们只好就地取材,把当地糊窗户用的纸裱褙起来代替绘画用纸;画笔秃了、坏了,自己修理;没有颜料,就按照民间艺人的经验,从黄泥、红泥中提取自然颜料。其次是照明和绘画设备问题,洞里没有照明设备,更没有必要的桌、凳,他们只好一手拿油灯,一手拿画笔,在简易的画板上艰难地临摹,看一眼画一笔,油灯熏得头昏眼花,特别是临摹洞顶壁画时需要不停地仰头,不一会儿就头晕目眩。
在这个周围20公里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洲上,交通不便、信息不通,职工为盼望一封远方的来信,常常是彻夜难眠;生病时,只能用所里唯一的一辆牛车送到县城看病,病痛加孤独令人难忍。
1944年8月30日,老工人窦占彪在中寺后院的土地庙3座塑像中发现经文残片,常书鸿立即去现场调查,发现了六朝手写经文68件。这是继1900年藏经洞发现以来的又一重大发现,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不久,他们又从宋代重绘的泥壁下剥露出唐贞观十六年(642年)的壁画,金碧辉煌,灿烂如新。其中东壁中的维摩居士画像,有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的“清赢”画风和神态,是莫高窟所有50余幅维摩画中最好的一幅,是前人从未见过的。这些重大发现,让常书鸿高兴得夜不能寐。
遭遇意外打击
正当清理修复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常书鸿遇到意外打击。
首先是他的妻子陈芝秀不辞而别。
1943年秋,常书鸿回重庆办事,顺便把全家接到敦煌。陈芝秀刚来时,被绚丽多彩的古艺术所吸引,参加了临摹复制工作。可是时间一长,她忍受不了艰苦、寂寞的环境,过不惯清苦、单调的生活,1945年4月19日,以去兰州就医为名,丢下13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弃家而去。常书鸿得知后又气又急,赶紧骑马去追,马不停蹄地追一夜,到安西也没见到人影。他不死心,朝玉门方向继续追赶。不知又追了多少时间,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常书鸿精疲力竭,一下从马上摔了下来,幸被玉门油矿地质学家孙建初和一位老工人相救,把他送回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