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圣手”聂绀弩之重庆编报生涯
作者: 颜坤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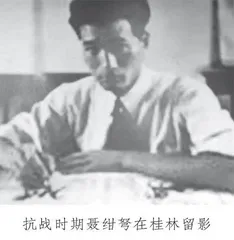
聂绀弩(1903-1986),中国作家、古典文学学者,湖北京山人。他一生编过的报刊很多,但每种刊物参编的时间都较短,最长的不过一年,且都是副刊,所以,学者夏和顺戏称他为“短命副刊编辑”,更多的人赞誉他是“副刊圣手”。
1943年秋冬的一天,聂绀弩离开广西桂林到了陪都重庆,在重庆短短4年间,他相继担任《真报》《客观》《商务日报》和《新民报》副刊编辑,他所编辑的这些副刊,充分体现出他办刊的个性和特色,给读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编辑《真报》副刊
1945年五六月间,聂绀弩辞掉位于重庆江北董家溪的私立建川中学的教职,受《真报》邀请,为《真报》编辑副刊。
赵则诚在《颂绀弩》中回忆:
《真报》是几个朋友集资办起来的报纸型的周刊,因为我年龄比较大些,拉到的股本比较多些,就由我担任报社社长。《真报》,名为报,实际是周刊,向国民党政府登记时就叫《真报周刊》,不过,采取的却是大报的形式,印的报头也是学了《新华日报》的版式,“真报”二字尽量大,“周刊”二字则可劲地小。这样做,有我们的私心,想发展成日报。当然这只是幻想,因为国民党限制出版报刊,限制言论自由的法令和用心,路人皆知,但是,“幻想”有时也产生某种力量。
该副刊最初聘了一位熟悉英美文学的知名人士担任主编。后来有人推荐聂绀弩,赵则诚怕请不来,因为聂绀弩在文坛上名气大,资格老。同时有人说聂绀弩倔,好骂人,难相处。赵则诚说,好骂人,无所谓,你不惹他,他总不能骂人。难相处,也没什么,迁就迁就就是了。其实,赵则诚心里的想法是根本请不来。谁知过了几天,去请的人回来说,聂老都不计较,答应来!这消息令人喜出望外。第一次见面叙谈就在报社。《真报》初创时条件很差。报社以5年为期,租了七星岗兴隆街一幢临街小楼,聂绀弩后来在文章里把它戏称为“通远楼”,因为这里邻近重庆名声响亮的通远门。楼身两层,二楼天棚上有所谓的阁楼,但站不起身来,只能爬上去睡觉,这就是职工宿舍,其简陋之状可想而知。
虽然许多人那时都已称聂绀弩为“聂老”,但他实际只40岁出头。因为个子高,跟人讲话时身板就多少有点俯就,侧看则是躬着身子。他两眼炯炯有光,面色微黄而黑;一口湖北腔,他这异乡人的口音给多为外省流亡到重庆来的报社同人异样的亲切感。没几天,聂绀弩就搬到报社住,不过报社没让他住阁楼,而是住的一间正屋。朝夕相处,大家都把他当作兄长。聂绀弩外面事多,每天回来得晚,大家都叨念他,连当初说他难于相处的那位同人也宾服了。
《真报》每期稿子大都由内部几个人分工编写。外稿欢迎,但没有稿费。工作人员也是没有工资的,但管吃管住。
聂绀弩的任务就是主编副刊。因为太忙,报社又请来“七月派”青年诗人庄涌做他的助编。聂绀弩给副刊取名为《桥》,他在中苏文化协会的一本外文杂志上找来一幅漫画作刊头,画面上有一座桥,桥上桥下都有行人,画幅下面一行小字:“马可波罗就从这座桥上走过,至今还是老样子。”当日寸距马可波罗来华已有600多年了。画面讽刺历代封建统治者,尤其直指国民党政府治绩差,社会没活力。内行人常讲:“办报纸要编辑有术。”聂绀弩这第一招就使《真报》的同人折服了。
由于聂绀弩名声在外,文艺界的友人众多,因此,招来不少重要稿件,如冯雪峰以“画室”为笔名的谈时局的长篇论文、臧克家的新诗、骆宾基的小说和杂文……当时重庆文化机构文化名人云集,单是日报就有十几家,国民党的官报且不论,除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副刊,大概很难在其他报纸的副刊上见到这么一连串的鼎鼎大名了。所以《真报》一出版,就令读者刮目相看。《真报》在陪都重庆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影响,可以从其他杂志对《真报》的介绍中看出来:“第一期印了五千份,一出门就争购一空,外埠的四千份订户就不得不再版了。”(沙浪:《(真报>——全国唯一大型周刊》,载《读者》1945年4期)
副刊《桥》占了《真报》一个整版的版面,每期万余字。征稿、修改、编写、定版式等,即便是有庄涌当助手,聂绀弩的工作量也是很大的。虽然说好请他来只编副刊,但聂绀弩到报社后什么都干,他自愿当外勤记者,做了大量采访工作,采访了不少知名人士,写出一篇篇内容丰富、扎实有力的长篇人物专访,如《陶行知访问记》《黄炎培访问记》等。
赵则诚在《颂绀弩》中回忆:
其时,绀弩文章的锋芒已登峰造极,他那些对敌人嬉笑怒骂的文字,岂止匕首而已。办报者既要敢言,尤其要能言,要看出问题来,讲出道理来,还要有文采,方才叫人读来喝采不止,印象深刻。我记得很清楚,报社内部的同志嗜读绀弩的文章,所谓“先睹为快”,就不说了。来自报纸排字房的赞扬声就太不寻常了。《真报》小本经营,谈不到自己印刷,是由《国民公报》社承印的,每周交稿时确定捡字拼版的日子,我们就有几个人去随时校对、画版样。我们曾几次看到、听到排字工人擎着绀弩的稿子边念、边捡字、边叫好的情景,每到此时,我们都忘了那是重庆的仲夏夜,内心像穿上合身的新装那样熨帖。我干报馆那时已经十年了,还不曾见过这样的事。大家回报社跟绀弩讲时,他只莞尔一笑。
《真报》是小报,但办出了特色,办出了影响,不但赢得读者的喜爱,也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注意,得到周恩来的赞赏。
赵则诚在一份材料里这样写道:
《真报》谈不到是革命的,最多也只能是揭露了蒋管区的一点黑暗,反对了蒋帮打内战的罪恶行为。但就是这样,却喜出望外地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鼓励。
聂绀弩传达周恩来指示说:“周副主席讲:《真报》的方向是对的,应该继续努力;这样的文章有作用,路子对,要力求进步。”
在另一份材料里,他写到当时的聂绀弩:
我清楚记得,他传达周恩来指示时是很郑重其事的,对周恩来的亲切尊重的情感,也能看出是很真挚的。再三叮嘱不要因为周恩来对《真报》有所肯定而骄傲起来,要加倍努力,不辜负周恩来的期望。
《桥》办了4期,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双十协定》的签定似乎开启两党合作建国的新纪元,在这样的新情势下,《真报》继续讽刺蒋介石政权已经不适合,再加上经费局促,报社运转维艰,1946年3月,《真报》悄悄地谢幕。
编辑《客观》副刊
1945年秋,国共《双十协定》签定后,著名评论家、报人储安平与在桂林主办过《力报》的老板张稚琴合作,创办一份时事政论性期刊《客观》,张稚琴出资任经理、发行人,储安平任主编。储安平想把刊物办成一份进步的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的刊物,因此,利用留英时期的关系,联合深受英国自由主义熏陶的知识分子朋友来办刊。储安平邀请留英学人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等担任编辑;张稚琴找到《力报》旧部、左翼作家聂绀弩担任副刊编辑。
《客观》于1945年11月11日创刊,这是一份八开的大型周刊,创刊号上,储安平以“本社同人”之名发表《我们立场》一文,指出:
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致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
可以看出,主编与编辑是平等的关系,他们各守一个摊,各负各的责。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华中华北传来内战爆发的消息,企盼和平建国的各阶层民众忧心如焚。聂绀弩也不希望国共内战,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让国家走上中兴之路。他将自己的新诗《命令你们停战》发表在《客观》创刊号上。聂绀弩在诗中将国共两党各打五十大板,重庆的左翼文人严厉批评聂绀弩,甚至还惊动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批评聂绀弩,认为我们是革命的,即使蒋介石不打我们,而我们先打,我们也是正确的”(刘军:《聂绀弩的“反战诗”》,载《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3期)。聂绀弩很快写了《感谢与寄慰》(载《客观》1945年第4期),诚恳地承认自己思想上“跌了一跤”,而且跌得非常惨重。
储安平对聂绀弩《命令你们停战》这首诗并不感兴趣,也无意批评,只是在《客观》第2期的文章《内战解决得了一切吗》中感叹道:“悲哀得很……人民虽然反对内战,而舍呼吁之一途外竟无他路可循,呼吁始终是呼吁不是命令,今日中国人民还没有力量可以命令要打内战的人停止内战!”
1945年11月26日,国民党政府在重庆成立最高经济委员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以民生主义为中心,改善民众生活,推动经济建设,重视人才的演说。储安平随后写了题为《蒋主席的新演词》的文章,发表在《客观》第5期上。文章评论蒋介石的演讲:“这是一篇完全谈具体问题的演说。这是一篇完全谈物质建设的演说。也可以说,这是一篇象征我们的国家在结束战争以后必须步人另一个新时代的演说。”对蒋介石提出的充分训练技术人员、惩办贪污腐化之徒、承认私人的才干等,储安平在文章中都给予无条件的肯定。
储安平的文章见刊后,聂绀弩立即在第7期《客观》上,以“绀弩”之名发表《伤风楼自语》一文,称“言论自由决不包含替宣讲圣谕”;随后又于12月25日写了一篇《韩青天》,该文于1946年发表在《客观》第9期,重提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亲自审案、被阿谀奉承者称为“韩青天”的事,批评这是“阔人崇拜”心理。他说:“中国人的头脑系统,当以为无论什么知识,都是可以由一个人具备的。同时,封建的、君主专制的、官僚主义思想深中人心,形成一种阔人崇拜的心理,以为阔人就是具备一切知识的大知识者,以为阔人真是替人民伸冤的。”聂绀弩所说的“圣谕”,指的是蒋介石在最高经济委员会上的演讲;“阔人崇拜”指的是储安平称赞蒋介石。聂绀弩这两篇杂文明显是针对储安平的。作家周健强说:“储安平发表了一篇吹捧蒋介石的文章,绀弩看不惯,就撰文骂储。”(周健强:《聂绀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945年11月14日,《新民报晚刊》副刊主编吴祖光在副刊《西方夜谈》显著位置隆重推出《毛词·沁园春》,并配发热情洋溢的“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11月28日,重庆《大公报》以《转载两首新词》为题,在显著版面转载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及柳亚子的和词,随即山城各大报纸竞相转载,并发表大量步韵、唱和之作和泾渭分明的评论文章。
《沁园春·雪》被蒋介石污蔑为“帝王思想”。他对陈布雷说:“我看他的词有帝王思想,他想复古,想效法唐宗宋祖,称王称霸。”并要求陈布雷“赶紧组织一批人,写文章以评论毛泽东诗词的名义,批判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毛泽东来重庆不是来和谈的,而是为称帝而来的”(《知情者说》第二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一时间,陪都文坛掀起针锋相对的论辩。
12月4日,《和平日报》刊出两封读者来信,分别是董令狐的《封建余孽的抬头》和杨依琴的《毛词(沁园春)笺注》,将毛柳的诗词唱和说成“奉和圣制”,将毛柳友谊说成是君臣关系。这两篇读者来信发表后,12月29日,聂绀弩发表一篇驳“帝王思想”的辩论文章《毛词解》(《客观》第8期),说“毛词《沁园春》发表后,有人以为是封建残余,是帝王思想的表现。本月4日《和平日报》副刊上董令狐先生的《封建余孽的抬头》,及杨依琴先生的《毛词<沁园春)笺注》,可为代表”。聂文对董、杨两人对毛词的诋毁与曲解进行反驳,并按照自己的理解阐述毛词的思想内涵和主题。他认为,毛词上半阕的头几句是“用雪、用白色、用寒冷来象征残暴的统治”,“而评论家反说作者欲与天公试比高,完全胡扯”;下半阕“翻成白话,不过说:强盗们,汉奸们,封建残余们!你们想用武力统一中国吗?你们自己认为可以成为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吗?你们错了!那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些无知识、无思想的野蛮家伙……要在今天成为一个人物,必须理解的多一些,必须自己成为一个知识者乃至思想家,必须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试问这与封建余孽或帝王思想有一丝一毫的相同吗?不!刚刚相反,它是反封建的,反帝王的!”聂绀弩在《毛词解》中贬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自己在若干年后对此问题作了澄清,他说:“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毕桂发:《毛泽东如何评说历代帝王》,载《人民政协报》2015年5月23日)“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毕桂发:《毛泽东评说历代帝王》,解放军出版社,2002)可见,聂绀弩并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