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人类“西来说”和“东来说”
作者: 聂云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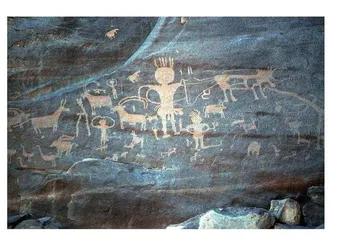
人类“西来说”和“东来说”的主要争论焦点集中于4大方面,这4大方面都是有关人类起源演变及其在人类自身的进化演变过程中,不断地与外在的客观环境进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过程中所产生的。人类作为地球生物圈内的特定种群,在面对生存和进化跃升自身的双重任务和使命的历史发展全过程中,成为国际学术界产生“西来说”和“东来说”大争论的客观历史基础。通过梳理“西来说”和“东来说”的主要观点,必须认识到人类是地球自然生态圈乃至太阳系星际大生态圈周期性整体变迁综合作用塑造的产物,单纯探讨局部区域地理意义上的“西方”或“东方”,都是线性研究思维,是不全面的。
人类“西来说”与“东来说”的四大焦点争论主题
文章所论述的“西来说”和“东来说”,并不仅仅是指国际学术界在人类起源、现代智人类起源、人类文明起源、人类文明文化传播路线等问题通常意义上的“西来说”和“东来说”,而是指人类作为自然界特有的物种,在整体作为一种物种在自身种系的自然发生演变全部过程中,在地球时空范围内所表现出来的现代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东来西往、西来东往这样一种循环式的人类种系族群跃升进化运动全过程。
自西方近现代学术思潮兴盛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土的大量地下地上遗迹文物等古人类活动基础上,通过对各区域性人类活动及其表象特征大量的实地调查,“西来说”和“东来说”两种学说,从提出到发展到今天,一直以来都是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随着现代分子学建立和广泛发展应用,这一学科所取得的成就,并没有按照原先学说创建者的本意能够进一步消弭“西来说”和“东来说”之间争论的多种多重焦点性问题,反而随着国际的风云变幻而进一步产生新的大争论、大分化、大对立。
从国际学术界对人类“西来说”和“东来说”的争论焦点问题分析,大致主要分为四个焦点问题:有关人类直立人起源地及其迁徙路线的争论;有关现代智人类起源地及其迁徙路线的争论;有关全新世时代“农业革命”起源地及其传播路线的争论;有关人类早期大河流域文明起源地及其文明文化传播路线的争论。限于篇幅,文章不展开论述有关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演变的“西来说”和“东来说”。
人类直立人和现代智人起源的“西来说”与“东来说”
从历史的时空分野来看,“西来说”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其主导的学术观点是人类起源从非洲地区,特别是东非大裂谷地区进化成功并逐渐迁徙迁移出非洲大陆,进而走向亚欧澳美等其他大洲。以西方学者发现的南方古猿“露西”为代表的非洲直立人约生存于320万年前,其后续直立人迁徙出非洲大陆的时间大约是200万年—175万年前。
对于人类直立人的起源,“东来说”认为要从古猿说起,其学说认为直立人的起源在中国西南特别是云南地区。在中国云南地区的发现中,滇中古猿系列是最具代表性的,如开远腊玛古猿、禄丰腊玛古猿、保山古猿、昭通古猿、元谋蝴蝶古猿以及晚期智人如昭通人、西畴人、丽江人、昆明龙潭山人等。中国云南古猿人的这一特点,使得“东来说”的学者们认为古猿人在中国云南是连续性进化的,其间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中断期,而这成为“东来说”连续进化理论的主要基础。
在现代人类即现代智人的起源问题上,“西来说”的主导学术观点同样是现代智人诞生于东非大裂谷地区,时间为25万年—20万年前,并在随后的“出非洲”迁徙中,分时间分批次分不同路线从非洲大陆迁徙走向亚欧澳美等其他大洲。
根据分子生物学理论,人类有23对46条染色体,这些染色体代表的基因群决定了人类每一个人的外表、性格、体能及智力,每个人的基因都来自其直系父母并且可以持续遗传给其直系后面的每一代。人类种系群和族系群的变化是靠着一代代具有共同祖先血缘关系的基因突变长期积累的产物。分子生物学家经过长期研究发现,人类的基因突变导致的遗传差异总量和累积程度,非洲地区是最高的,也就是说,非洲人类身上基因多样性数量巨大的原因,使得“非洲的人类历史最古老”这一结论得到确定。同时,由于基因变异进化的速率相同,分子生物学家就可以根据对比每一个进化分支的差异数量,从而得到人类进化各个分支的大概时间。
由于人类迁徙的批次和时间并不一样,这就导致了不同的迁徙批次人群身上其携带的基因标记是不同的,通过对比不同的基因突变标志,就可以大致绘画出一条人类迁徙迁移世界各地的路线图。按照现代分子生物学家的研究,现代智人类从非洲大陆迁徙世界其他地区的路线和时间有多次,并不是一次性迁徙完毕的。
现代智人的第一次大迁徙被“西来说”称为海岸线迁徙之路。第一波现代智人是携带M130突变基因,在大约5万年前,沿着非洲海岸线即东非大裂谷一线,从非洲大陆经过欧亚非大走廊,经过印度洋一直走到澳大利亚及其周边岛屿地区。在5万年前的地球冰河时代,都是冰原,这就使得第一批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的现代智人能够很轻松地沿着波斯湾、印度洋斯里兰卡、东南亚马来西亚最终抵达大洋洲。在本轮冰河时期结束以后,全球海平面持续上升,淹没了绝大部分史前人类的旅程足迹。
现代智人的第二次大迁徙被“西来说”称为欧亚大草原迁徙之路。第二波现代智人是携带着M89突变基因,在3.5万年—3万年前从非洲大陆扩散到欧亚大草原地带。第二波智人迁徙的动力主导因素来自追随猎物,由此进入广袤的欧亚大草原,即分布在亚洲东部-亚洲中部-亚洲西部-西伯利亚-欧洲东部-欧洲西部的巨大草原带,由此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更加波澜壮阔的迁徙旅程。
伴随着第二波现代智人的扩散,这群智人越来越远地迁徙,在迁徙的路途中遇见了巨大的屏障,即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为主体的东西方两大分区,包含兴都库什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为南北走向主线的屏障区。这3条山脉共同汇合于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由此第二波现代智人的扩散路线在这里出现了分叉,又由此汇合点和屏障区分化出南、中、北3线。
南线:3万年前进入南亚次大陆,成为南亚古印度人的祖先
中线:3.5万年前,经帕米尔高原越过天山山脉,经过准噶尔缺口来到亚洲东部,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中国、韩国、日本等区域的现代人类都是第二波智人类的后代。
北线:3.5万年前,从亚洲中部出发,在欧亚大草原带分为东西两个方向,其中西路进入欧洲,东路进入西伯利亚,并经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地区,成为大部分欧洲人和几乎全部美洲原住居民的共同祖先。
借助现代智人出非洲的第二波大迁徙运动,由此导致了人类文化文明发展演变史的大爆发时期,在大约1.2万年—1万年前,人类进入全新世时代。
人类农业起源的“西来说”与“东来说”
新石器时代,亦称全新世时期,与旧石器时代的一大分别是技术工具的根本性进步,这种技术工具的根本性进步推动了全新世时期农业革命的发生,进而使延续了400万年—1万年之久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方式,从狩猎采集过渡到半迁移半定居的农业生产方式。在8000年—5000年前,又逐渐过渡到定居型农业文明时代,而原先的狩猎采集生产类型,逐渐过渡到半农半牧的游牧性农耕经济生产类型,从而在5000年前左右正式形成了定居型农业文明类型和半农半牧型游牧文明类型在地球各区域时空范围内呈现交错分布状态。由此在BC3500-BC3000年前后人类文明进入真正成熟期的文明时代,这一成熟期文明的主要标志就是人类初代类型文字的发明和创造。
正因为全新世时期,人类生产工具的技术性革命导致农业文明大爆发,由此国际学术界对人类农业文明的起源地进行了广泛研究与探讨,由此产生了在人类农业生产生活类型起源发展和演变上的农业文明文化“西来说”和“东来说”。
一般而言,距今1.2万年—1万年前后,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一个共同时期。考古学家认为最早的农业应该是在现代智人在洞穴居住晚期出现的,因为人类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从洞穴居住向平地居住转变的过程。
根据学术界的研究,在距今1万年前,世界各地大致诞生了3种体系完全不同的原始生态农业体系,而且都很有地域空间分布特点,这3个原生农业体系分别是位于北非-西亚两河流域的麦本农业体系、位于东亚大陆黄河流域的旱地粟作农业体系-长江流域的稻本水作农业体系和位于中南美洲的玉米-番薯农业体系。正是由于在全新世时代初期地球在不同的3个主要地域爆发了具有不同“内涵”的“农业革命”作物和生产体系,所以学术界对农业的起源出现“西来说”和“东来说”。
关于这一点,除了西方学术界所提出的“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的西方起源论外,过去20年里,随着东亚尤其是中国考古学的迅速发展,发现了一系列揭露全新世时期农业革命的遗址遗物。这些发现促使更多学者提出,在全新世农业初期,中国的旱田和水田两种农业体系已经与西方的麦作农业有了明显不同。世界上的原生文明几乎都是建立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之上,而农业革命正是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石。因此,持有“东来说”的学者们认为,从农业文明的起源角度来看,基本上可以推翻中华文明西方起源的说法。
目前考古发现,至少在1万年前,从已经发现和出土的考古看,中国二元农业体系就已经形成。比如在北方,东胡林遗址、李家沟遗址、柿子滩遗址等地都出土了石磨盘、石磨棒等用于黍粟类粮食脱壳的工具,这些工具显示了当时农业粮食作物的统一性。
水稻种植作为中国南方主要的农业形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万年前。在华南地区,已有至少四个考古遗址发现了1万年前的稻谷遗迹。淮河地区的贾湖遗址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分别距今9000年和7000年,均出土了大量的碳化稻谷。这表明中国北方和南方旱地和水田相结合的农业体系发展经历了独立而完整的历程。即使小麦大约在4000年前传入中国,并丰富了人们的饮食之后,这一体系依然保持着其特色和连续性,这种中国原生的粟、稻二元饮食结构也一直在整个古代史中占主导地位。
对人类“西来说”和“东来说”的思考
对于人类“西来说”和“东来说”,我们从目前国际学术界主要争论的四大论题进行分析和考察,可以看出,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从人类作为个体生物在各地区目前已发现的存留物时间的早晚程度来进行综合分析的。笔者认为,这种单纯的焦点争论有失偏颇,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是地球自然生态圈乃至太阳系星际大生态圈周期性整体变迁综合作用塑造的产物。
目前“西来说”和“东来说”,争论的焦点更多单纯地放在了各地区发现的属人遗迹遗址时间出现的早晚上,却忽视了对地球自然生态圈的周期性系统性变化对人类作为种群、个体同时双重的巨大推动促进作用。已有的考古证据已经表明了不同时期的人类生物特征的差异化是非常明显的,这就表明人类作为地球生态圈系统的一分子,必然要受到地球生态圈环境周期性变化的巨大影响,而这一点就不是单纯地理意义上的“西方”或者“东方”能够解释的,而必须将地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这也同时表明人类是连续进化的自然产物,人类的进化是缓慢渐进与快速突变的双重叠加结合体。
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人类从直立人向智人演变的初期阶段,而且在人类文明达到创造文化和文明的辉煌时期也同样适用。实际上,在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包括狩猎采集时期、农业文明时期、工业文明时期,以及当代的智能信息化文明时期,地球生态系统的周期性全球变化对人类文明的区域性发展和文化变迁都有着深远影响。历史上每一次人类文明文化时代的整体性跃迁,都是由地球上某一地区的特定率先变异的族群引领发展创造出来的,这一点无论是农业文明时代取代狩猎采集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取代农业文明时代,智能信息文明时代取代工业文明时代都是如此。
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类作为社会性种群,族群间和族群内部个体之间的分工协作所产生的巨大社会规模性效应,对人类的不断进化发展乃至创造如今辉煌的现代文明,一直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考古证据已经表明,人类曾经在数百万年内都是穴居性动物,这种生存状态,直到农业文明的中期发展阶段才得到大规模解决,而人类的居住环境状态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单纯的“西来说”和“东来说”不能够完全解释,而需构建新的理论学说进行阐释。
(作者单位:中共陆丰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