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朝贡制度探讨
作者: 张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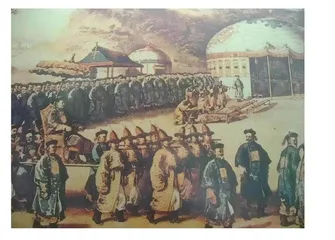
在我国古代的封建统治时期,向藩属国和朝贡国的封赏是其重要的一环。清代前期对于藩属国和朝贡国的封赏并非遵循明朝“怀夷柔远、厚往薄来”的封贡政策,这种外交政策在康熙后期开始逐步显现出来。随着王朝的发展,清王朝的贡赋贸易日渐兴盛。
作为中国传统的外交方式,明清二朝在实行“海禁”期间,朝贡是中国与外国交流的唯一方式。朝贡体制下,中国王朝对于朝贡国的“奉表纳贡”,也体现了对朝贡君主实行封赏的实际情况。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实质上和在名称上,都是经由封贡关系而确定的。前人对于清王朝的贡赋制度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费正清和邓嗣禹的《论清代的朝贡制度》之中,主要集中在对朝廷的基本制度的探讨上,总结出其特点,而对于清王朝的封赏与册封,却是缺乏足够的了解。下文将从清朝早期一些重要的朝贡(藩属)国家入手,对清朝早期的外交赏赐体系及这一时期的朝贡贸易进行简要梳理和研究,以便更加完整地了解清朝的朝贡体系。
朝贡的起源
在历史文献中,“朝贡”是外交的同义词。直到近代,这一方式才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历代《会典》的整理,可以发现康熙和雍正两个朝代的《会典》中所记载的“朝贡”对象,不仅是与清有联系的诸侯,而且还包含了与清有贸易往来的西方各国。乾隆之后,朝鲜、琉球等国成为当时的“四夷朝贡之国”,而西方各国却仍然是朝贡的国家。一直到1899年,清末《会典》中,西方各国才被剔除出朝贡,只有朝鲜、琉球、安南、南掌、暹罗、苏禄、缅甸七个国家,“其馀,多通互市”。
清代法令:“凡封外邦,应先有诏,始有内诏,亦有玺印,均辅以赏。”依此,朝廷的封赏包括授诏、授印和授勋三个部分。但是,对于“使者”的选择,却与其政权的性质有关。关于这一点,在《会典》中有这样的记载:“凡是诏封王,藩属国在有继承人的时候,都要首先派使者上奏。钦命镇守朝鲜、安南、琉球,正、副使奉诏前往。其余几国,也都派了使者前来,以示感谢。”清代所授的封邦分为朝鲜、安南、琉球等国,即“奉敕往封”;其他各国,都是“颁赐使者”,而不是另外派使者来封。
在中国的封建统治时期,一切大事向臣民宣布,以及向藩属国和朝贡国的君主任命,都要用圣旨。清代的诏书,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作为开端,用“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或“布告中外,咸使闻知”结束整段告示。圣旨的落款是“皇帝之宝”,上面写着圣旨的日期。
诏书乃皇帝用于官职任命与训导群臣的文书。清朝的敕令分为敕命与敕谕,但据《清会典》记载,实际常以“敕谕”代之,用于封赏或增补。以琉球为例,顺治虽命其君王朝贡,但因海难延误至康熙元年。康熙帝再次下旨重申:“尔国慕恩,朝化,遣使来朝,世祖章帝嘉乃抒诚,琉球特颁恩赍,令琉球军副总管张学礼等,奉上诏书,册封汝为琉球国的国王。乃海道尚未开通,滞留闽数载,致尔使之故者颇多。张学礼奉命归京,却未向朝廷禀告前事,各省巡抚也不得上奏。但朕再三审问,才知此事。朕念尔国诚待朝贡,当有优待之心,故遣臣子与各地官员,滞留不去,非是朕不仁之意!今日,正副使及督抚等各官,均有区别处置,特颁恩赍,并命张学礼、副使王孛等,使其悔过自新,复职司,并即派人尽快回国。一切册封之事,都是按照世祖章陛下的旨意来办。朕恐尔不能得朕之旨,特发一道旨意,俾尔闻知。”
另外,朝廷还经常对朝贡的诸侯国进行嘉奖、赏赐等,比如康熙十六年(1677年),就下了一道诏书,命安南王黎维禧派兵援助围剿吴三桂。清代将印玺颁发给臣属国有君主,是建立了封建宗藩关系的一个象征,表明了对其在自己国家的支配地位的认可。朝鲜国君李仁宗于崇德二年(1637年)册封为藩属国,并被授以龟钮印章;1654年,琉球太子尚质和安南太子黎维禧在康熙五年被赐予一枚镀金的骆驼钮银玺。
朝贡的发展
在奉贡系统中,藩属国每年都要进贡给清朝,比如高丽每年朝贡一次,琉球国每年朝贡两次,安南每三年朝贡一次,对纳贡的品种和数量都有很严格的规定。这才是一次正规的朝贡,也称常贡。朝鲜每年进贡一次,这就叫“岁贡”。在诸国“奉表纳贡”之后,由清朝政府按照习俗赐予他们的国王和贡使。
与清王朝有着紧密外交往来的朝鲜、琉球、安南,除了正贡以外,“每有庆祝赐爵,谢恩之举”,都要使臣属上贡。而清朝所赠之物和数目,则大体与向之奉正之礼大体相同。三个国家里,朝鲜是进贡最多的一个国家,每逢“圣诞(皇帝的诞辰)”“冬至”“元旦”,都要上贡,年终还要随“正贡”一起上贡,按照惯例,接受清朝的封赏。
根据有关文献,可以看出,顺治和康熙年间,清朝对于朝贡国家的封赏,并非完全沿袭前代“厚往薄来”的惯例,甚至统治者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颁布了改正措施。康熙后期,朝廷对朝贡国家的封赏有所增多。
所谓的“加赐”,是指清朝除了规定的各种封赏项目以外,还向朝廷进贡的国王和贡使进行了特别的封赏。雍正二年(1724年),世宗谕怡亲王允祥:“各诸侯国向朝进贡粮食和回国之时,均有相应的赏赐。然而,主管官吏却不予理会,以至于远人得不到好处。朝鲜人守了数百多年,如今琉球的使者也是恭敬有加。伊等回国之时,所赐之物,必有最好之人,以求公平。此后,除了理藩院的蒙古使臣之外,还有朝鲜、俄罗斯、暹罗、安南等各国的使臣,都要向朝廷进贡,届时所赐的粮食,由户部负责。若有重赏,可酌情上报。”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都是仿照康熙后期的惯例,多次向常贡赏赐的国家增加贡品,通常占到总贡品的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
“特赐”是清朝对藩属国君主特别优待的一种制度。康熙朝时,对于外藩的特别赐礼相对稀少,通常仅限于皇帝亲笔书写的御赐匾额或字幅。以康熙廿一年(1682年)为例,琉球王受诏,康熙帝御笔亲书“中山世土”四个大字,这份殊荣不仅彰显了琉球王室的尊贵地位,也体现了清朝皇帝对琉球王国的重视。
雍正时期,朝廷对国家的特殊赏赐开始逐渐增多,且赏赐的内容和形式也更加多样化。除了皇帝亲笔书写的御赐之外,还包括了金银珠宝、丝织品、瓷器等贵重物品。特别赏赐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皇帝书写的文字,而是扩大到了朝贡国家的王室成员和高级官员等。
清朝时期,对于朝贡国家的封赏制度逐渐完善,通过封赐和特殊封赐等手段,向朝贡国家传递了友好与尊重的信号。这种“厚往薄来”的外交惯例,即清政府在赏赐上给予朝贡国家更多的回赠,而在朝贡国进贡时则不苛求太多,反映了清政府对朝贡体系的重视和对朝贡国家的优待。
朝贡贸易的衰退
朝贡贸易为清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质依据。从经济学上讲,“贡”与“赠”是一种以货易货的交易。另外,互市也是朝贡贸易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朝贡贸易的主要内容。顺治年间,“各国派官入京,授勋之后,须于会同馆开市,为期三至五天,但朝鲜和琉球则无此限”。礼部将文书送往刑部,然后上报,官员监督,保证公正。外国船只,在没有正式进贡的情况下,擅自前来交易的,都要加以阻拦。“在贡舟抵达之前,不得与护贡、探贡等贸易”。这说明清代初期的“有贡才有市、无进贡不得互市”的传统,是一种继承了明代初期的“朝贡”方针。唯一的区别在于,明晚期澳门一次通商的方式得以延续,澳门曾经是中西方唯一的贸易渠道。
然而,“以贡代市”并没有持续多久。清圣祖皇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下了圣旨:“先行颁布的海上禁令,应当全部终止。”在废除海禁的同时,由“以贡代市”到“贡市并举”。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曾颁布:“洋船所携之货,一律不征。其馀之人,则准许买卖,并依所派官员之命,征收赋税。西洋商船一事毕,所有的外族人,都要遣送回国,不可在内陆逗留。”此后,朝贡与互市并行。这就是《粤海关志》中的记载:“凡入广东者,当免税;专以市为进,货物应征,是故外国之故惧也。”如今,每一国都有来市之税,每一国都有贸易之税。而且,无论贸易还是市场,都是清朝用来怀柔、控制远民的一种方式。
朝贡贸易的场所有两处:一是京城同治所,二是贡使进入的边疆,地方官府有权安排商人,通常在有贡使处的驿站里办理买卖,并受地方官吏严密监视。康熙三年(1664年)曾言:“凡是有外贡之人,欲从其夫之力,入京交易,悉从之。”若要在那里交易,须派人监督,不得骚扰。
例如,琉球的纳贡官员可分成入京、留边和召回三个方面。入京之人,除了上奏朝廷贡品之外,还可以在会馆中进行三到五日的贸易,这些人被安排在福州的柔远驿站,用来和本地商人交换他们所带的货物,剩下的人返回自己的国家。
当时的情况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康熙三年(1664年)颁布的谕旨,虽然准许各藩属国将进贡之外的“顺带货物”运至边疆,但数年之后,又收回了谕旨,仅准在京中与馆中交易。然而,除了琉球诸王的上谕之外,清朝的古籍中并没有记载这一条。另外,根据《清朝通典》,康熙十一年(1672年),清廷再次强调:“暹罗各使者所带之货,欲往京城交易,由其自行转运,若有需要,请随其自行处理;或欲于广东通商,由巡抚监察。”由此可以看出,“禁令”仅为一纸文书,而没有实际执行。
与明代将贡物及其他交易之物均由官方转运的惯例相区别,清政府对“顺带货物”须“自出夫力”运送到京城,这一点并无异议。因为路途遥远,需要大量的金钱,所以琉球方面也不想吃亏,所以上书清廷,要求继续与闽省通商。所以,清朝的贡赋,多是在福建的琉球、广东的暹罗等交付。
一部关于中琉两国之间的相关文件,记载了从日本明治政权兼并琉球的一百多年来,琉球以朝贡方式向中国购买的商品,不论税率和种类均有较大的改变。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免税白银597两,可用于购买71种商品;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减免税款共计4984两,其中33种货物可用于消费。产品的品种从针织品、干果水果到以布料、药材等为主。
另外一个经常派使者到中国进行朝贡交易的是暹罗。起初,清朝对朝贡贸易存在较大的制约,后来在《暹罗求及废除海上禁令》的要求下,对朝贡贸易的有关规定得以放松。由于船上装载的物品(也称为压仓货)可以免除关税,到了乾隆时期,暹罗出贡的范围更广。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曾有大臣上书:“暹罗每年正副贡船入关,所载船只多达数十艘。还有一些走私的船只,都是从内陆运来的。由监察人查出应交之银两数,上报各巡抚,予以赦免,绝非为谋反之策。”乾隆帝又命:“暹罗修贡贡船,奉贡贡船一艘,照常免税,其他船一律以货物收税。”其正副贡船,亦得免税。同时不容许大陆的商船逃避关税。这一类的商船,到了关内,监察使可以一艘一艘地检查,除了进贡的货物以外,如果有走私的,一看就知道是走私的,自然要收税。暹罗贡船种类繁多,有正贡船、副贡船、象船等。由于清朝制定了只有正副贡船才能免关税的政策,所以暹罗加大了贡船的出航频率,让更多的货物可以免关税。事实上,康熙时期,广东的番禺人屈大均,在记录明朝由广东向外国朝贡的时候,就已经提及暹罗等旧时向粤进贡三船,使节带着金叶,进京朝进贡,其舶市之货归还。第二年,三艘商船再次前来迎接,并将货物交还给国家。总之,对于暹罗来说,贡赋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与中国的交易,也是一个获取经济利益的正当途径。更为关键的是,由于“修贡输诚”,得到康熙帝恩准,从康熙后期,暹罗人就陆续向广东和福建出口本地稻米,并享有与“贡物”相同的免租优惠。
相对于18世纪初清朝的全盛时代,清朝在19世纪初的衰微中,尤其是琉球和暹罗这两个国家,对华的朝贡贸易却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封建君主,首要考虑的是纳贡的价值观念。其本身的利害关系,常常是决定其盛衰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只讲“义”而不讲“利”的封建君主们,他们颁布了一套严格的朝贡制度,禁止走私,禁止本国商人与各国上贡的私人运输,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朝贡的范畴。19世纪初清朝发布的各国使团贸易物品限制令中写道:“凡外国贸易,不许收买史书,黑黄紫皂,大花西番莲缎,并一应违禁兵器、焰硝、牛角等物。”“外国贡使归国,伴送人员不许将违禁货物,私自进行贸易”。凡商人等,将所购之物,以布匹为业,立即归还。而与馆中的将士们,交易一些禁货,或者是武器,或者是铜铁之类的东西,卖给其他国家的人,都会被处死。又有法令,凡外国使臣返国,其陪同人员,不可擅自从事走私货物的交易。在朝贡体系逐渐淡出后,具有“防”“禁”双重性质的贡赋仍未发生变化。
(作者单位: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