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礼制礼俗发展演变
作者: 陈冠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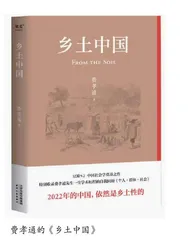
湖南、江西一带的传统村落大部分发源于明清时期。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里说:“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担负,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为了要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而且凡是政治、经济、宗教等事物都需要长期绵续性的……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氏族本是长期的,和我们的家一般。”所以我们研究传统村落的礼制礼俗,离不开具有长期绵续性的家族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因而有必要窥探现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宗族和族规。
华村田段肖氏宗族的复兴
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传统宗族的复兴及此种复兴带给农村社会生活的影响,肖唐镖先生及其学术团队以江西的9个乡村为例,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将成果发表于《村治中的宗族——对9个村的调查与研究》。
我们据此进一步考究可以发现,肖姓宗族在20世纪20年代曾修过谱,1991年新修《族谱》之前,曾经于1948年再修。当时全庄本族男丁有80余人,修订了自29代往下20代的派行辈分:“诗书遵孔孟,文章法唐明,祖德大如天,本源永世昌。”按此派行,至1997年,至善堂已衍至“唐”字辈(37代);缉熙堂的大房和小房衍至“法”字辈(36代),中房繁衍速度最快,已到“明”字辈(38代)。
这里要说明的是,田段原本是单姓村落,原来只有刘姓。后来肖姓迁入,肖家兄弟肖寅开基至善堂,肖玄开基缉熙堂。肖玄之后,孙辈肖子民、子良、子顺分出大房、中房、小房三个房支。据判断,《村治中的宗族》一书主要作者肖唐镖君应该就是江西华村田段肖氏缉熙堂中房第37代的佼佼者。(至善堂1997年才有第37代“唐”字辈,而肖唐镖君出身于1964年,无疑不算至善堂之后了。)又,由肖氏“派行辈分”之排序口诀,至少有如下3层意思值得注意:首先,重视诗书,遵从孔孟的教导;第二,唐之韩柳为古文八大家之首,明也有众多文章高手,“文章法唐明”,后来肖氏子孙在文章学术方面冒出来精英人物不在少数;第三,尊宗祖德,后人之本分。唯其如此,源远流长,一姓一族乃至中华民族才能繁衍发扬光大。
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作为组织的宗族虽然不复存在,但是宗族所形成的一些‘规矩’却没有变,村民维护宗族利益的自觉性与责任感始终存在着”。这最典型地表现在对《族谱》与宗祠的保护上。如田段,至今不仅刘氏宗族保留着笔拟的旧《草谱》,而且肖氏宗族的《族谱》也一直保存着。经历各种运动,几卷厚厚的族谱始终被族内长者保护完好,村内的三座祠堂也未受到冲击,一直完好无损。这揭示了宗族在中国农民心中的根深蒂固,也预示了它可能复兴。
“田段肖氏家族除了设立族长、房长由他们组成的合议机构‘斯文前辈’外,还于1990年建立了管理本族和村庄公共事物的‘村长’班子及一年一会的户主代表会议……族长系按年龄而非辈分而定。在这里,族长的产生并不需要经过什么程序(选举等),完全是自然形成的,即由缉熙堂子民中年龄最大者自然上任或继任。房长的任职条件与方式也同此……传统族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转型,已近于王沪宁先生所称的‘荣誉型族老’”。
这一段前面还只是说宗族“可能复兴”,这一段却在说“复兴后的家族组织”了。显然,这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已经把宗族复兴后的组织结构与活动当作既成事实加以研究。援引权威学者关于“荣誉型族老”的论说,也是承认管理宗族的权力机构缩小权力范围的事实。这意思就是说:尽管乡村中的宗族复兴已是事实,但宗族管理机构毕竟与以前的那一套不一样了。
“在结婚仪式中,宗族因素特别显眼。”“田段肖、刘氏皆有宗祠,族中青年结婚,酒席就在族祠内举办。男青年的迎亲队伍,须从宗祠出发,并以鼓声、鞭炮声相送。新娘进村后的第一站,即到宗祠认祖宗,从此便正式归于一族。女青年结婚,也须到宗祠拜别祖宗,并由宗祠送出。在嫁娶中能进出宗祠是族中每一个青年的荣耀……而一旦丧失进宗祠的权利,则是人生的奇耻。”这样的礼仪,与《仪礼·士昏礼》不只是相关,而且相通。“士昏礼,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诸祢庙。”小戴辑《礼记·昏义》:“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可见宗族因素在婚姻仪式中占据重要位置,不是偶然的,而是传统如此,世上有宗庙有昏礼以来历来如此。
肖唐镖先生写道:“总的看来,在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宗族因素仍然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举凡重要活动和仪式大多洋溢着浓厚的宗族文化……”这样的话是肖君在自己的家乡深入调查研究之后作出的论断,有大量的证据,应该可信。
泰和县苑前乡岱村的礼制礼俗
改革开放以来,宗族活动在一些乡村逐渐公开化、正常化。譬如《村治中的宗族》记载了泰和县苑前乡岱村的一些宗族活动。
“宗族活动已由幕后走到台前,成为村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修祠堂、修祖坟等活动也公开化了……作为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延伸或代理,乡村治理组织对宗族的态度比以前更宽容了。这些都是宗族复兴体现出的新特征。”
这是符合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肖唐镖与戴利朝等人都说到了“宗族复兴”。宗族活动在20世纪改革开放以前被取缔,受到长久的压抑,但表达对宗族祖先的怀念,适当程度的宗族活动其实应该予以理解。
岱村的结婚仪式含有宗族因素。“迎亲队伍主要由族中男青年及亲戚组成,一大早到女方吃早点,行前要到宗祠鸣爆竹揖拜。迎亲队伍将新娘接回到村里,停靠在宗祠门前,再由男方房族中年长者将她抱下车进宗祠,与男方在宗祠祭拜。当然,新娘的双脚仍未着地,而是踩在早准备好的布条上,拜完祖宗后再由人抱回家中。这样,男方才算将新娘娶了回来。此过程称‘等亲’。”由岱村的“等亲”之礼可以判断男女双方所在地的宗祠在婚礼中的地位。显然,与旧时相较,妇女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
“在社区公共道德秩序的维持中,宗族显然比村级政权组织作用来得更大更实在。事实告诉我们,不孝敬父母、兄弟不和的事情时有发生,但终究不会引发争斗甚至惨剧,其因在于同族年长者尤其是妇女的调解……这说明,宗族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有稳定农村社会秩序的机制与功能……在社区公共保障与互助上,历史已经展现了家族的巨大作用……而不像县乡的保障对象仅限于军烈属和五保户之类。”“本村个案研究说明,即便是强大的国家权力进入基层农村社会,也未必能使宗族销声匿迹。改变不了的历史事实是,宗族与村级治理在互动中共存、变动和发展”。
只要深入农村调查实际情况,不难发现戴利朝从岱村个案调查与研究得到的上述结论颇为实在。譬如“不孝敬父母、兄弟不和的事情”,由兄弟和同族的人协商,有可能比从县、乡派干部来解决要有效果。要让宗族在社会上销声匿迹,那就必须铲除宗族产生的根源,也就是说除非人类产生的历史被消灭,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戴利朝说:“即便是强大的国家权力进入基层农村社会,也未必能使宗族销声匿迹。”可谓言之有理,中华礼仪之邦自夏商以来几千年的文明史可以为证。
泰和县螺溪乡藻苑村的礼制礼俗
螺溪乡藻苑全村共有五姓,分别为肖、李、陈、郭、刘。只有照溪刘姓于1996年重修了《族谱》和《村志》,修复了祠堂,举行了谒拜祖坟的活动。
“刘氏修谱时入谱规定有所变更,即过去没有生育男孩的家庭,女孩不能以红丁入谱,而现今独生女可以入谱。变更的原因是为了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号召。”今按:将男子方可入谱的旧规稍作变更,也就是增加一条,“独生女可以入谱”。这也是适应形势的一个办法。女子入谱,与大革命时期妇女进祠堂具有类似意义。
族谱修好后,“全村男丁都必须到祠堂迎谱”。将族谱迎回来后,抬入祠堂,“然后,族长带领全村男丁点香鸣炮,祭告祖先”,“族长、村主任分别讲话,劝诫人要敬祖念宗,孝敬父母,发扬传统美德,遵守国家政策法律,振兴刘氏家族”。由这些情况可见:即使族规发展后,当地宗族活动主要参加者还是男性,男性是宗族的当然成员。
“祠堂是宗族的象征,从精神上维系全族族人……绝大多数人认为修复祠堂是本族头等重要的事,因为祠堂是村的门面,每家每户都用得上它。谱可以不修,但祠堂是一定要修……1996年将祠堂内外两块牌匾‘永庆堂’‘刘氏宗祠’重新整修油漆后,举行了上牌仪式,族长带领全村男子祭拜祖先,挂上匾牌”。
祠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祖宗牌位安放之地,先祖神灵憩息之所,族人祭拜先祖之庙。把祠堂之修复看得比修族谱还重要,原因大概也在这里。小戴辑《礼记·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祠堂是行祭礼的地方,明乎此,自然可以明白修祠堂的重要性了。
“过去村里的居丧期有3年,以门上贴绿色对联为标志,而今把范围缩小在49天内。在此期间,家属们的鞋、帽要蒙白布,妇女扎白条绳(如今也有改为戴黑纱),并在门上、墙上贴小块红纸避邪,孝子不能去别家做客……在49天之内,家里后代不能言婚嫁。”(49天有7“七”之分,逝者之女有为逝者“烧包”之事。)
这是有关藻苑村丧服制度和相关礼俗的说明,与传统礼俗有不少相同的地方,其中也有藻苑村的特色。譬如,居丧期内蒙白布,不能谈婚嫁,古今相同。但古代不仅仅49天之内如此。古礼子女为父亲服丧3年,实为27个月。可见,随着时代变化,一些乡村的礼俗习惯也与时俱进地朝着简化礼仪、减轻负担的大方向有了演变。
要说中国广大农村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已将宗族宗法观念扫荡一空,当然不合实际。现在该如何治理广大农村,如何把社会主义法治落到实处,如何看待城镇与村落长期以来实际存在的宗族观念与宗族活动,如何把中国城乡治理好,确实该深入研究。肖唐镖等人对江西农村的调查与研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可供借鉴。
在我们看来,村落社会礼制礼俗的发展,与乡村的各类宗族活动的演变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传统光宗耀祖的思想观念如果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持一致,如果融入振兴祖国的伟大事业,那就是值得尊重的,有利于乡村社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我们对宗族观念与宗族活动,也应该因势利导。
基金项目:2020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新时代湖南传统村落礼文化研究”(XSP20YBC229);2018年度湖南省教育厅课题“明清以来湖南乡村礼制发展演变研究”(18C0803)。
(作者单位:邵阳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