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凡,一个精英女性决定“放弃”
作者: 马拉拉 陈彤
邵逸凡,一个不怎么被熟知的名字。这个名字在2017年的时候提及才有一些声量,因为它曾被整整齐齐地排列在2017年《非诚勿扰》舞台,那一年节目改版,迎来了收视小高峰。这个名字的主人拥有一米七零的身高,小圆脸,中发和露齿的微笑。不具攻击性的外表加上她一针见血的剖析能力,让“知性”一度成为她的标签。
2017年,节目组做过统计,邵逸凡是男嘉宾选进心动区次数最多的女性嘉宾,有着“心动区女神”的称号。彼时她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毕业的资优生,前国企外派人员,曾在伊拉克坐防弹车出行,又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普华永道里的咨询顾问。她的前同事形容,她所在部门的PPT配色都和其他部门的不一样。那个时代,她是“别人家的孩子”,是不同于普通人的“精英”的存在。
但在这之后,如果去寻找她的名字,人们会发现,邵逸凡这三个字更经常隐匿在电视、电影放映结束之后长长的演职人员名单里。又或者,疲惫的路人在乘坐地铁时抬眼看,能发现一张熟悉但叫不出名字的面孔,她抱着不属于自己的孩子笑脸盈盈地出现在地铁穿越而过的一个个广告灯箱上面。
2018年,邵逸凡几乎放弃了之前的一切,裸辞成为了一名演员。不是那种会光鲜地出现在综艺节目上有自己麦克风的演员,也不总是那种在主角旁边有台词的演员,而是在电影院演职人员开始排列满整个银幕,观众几乎要离场的时候才会出现名字的演员。圈外人不明白具体分工的时候,将其称之为“跑龙套”或“群演”。有的时候几乎是“道具”一样的存在,在《繁花》里,她是配角“小江西”的背景,贡献了几个眼神的表演。
2024年,《小巷人家》热播,她在里面饰演的周老师和蒋欣对戏,因为剧情有趣,曾在社交媒体上有过热度。原以为是《月亮与六便士》一样精英放弃世俗选择艺术的故事,但邵逸凡又再次放下一切,在演艺事业有所起色之后,跟随伴侣去了温哥华,从零开始。
邵逸凡多次拿到过那张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拿到的通往成功的门票,但她又一次次地爬上山腰就下山,总是主动选择“向下”的人生,一选就是7年。在那条常被认为是成功和幸福的大路上,邵逸凡极致热烈地投入过,又转身背离而去。她的经历折叠了属于我们的这个时代。
优等生
2月温哥华时间的22点40分,室外接近0摄氏度,邵逸凡接到一个帮忙遛狗的单子。她住所的附近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女生,住很好的房子,却总是没有时间遛狗,她总是呼叫邵逸凡,邵逸凡也总是随叫随到。
这是2025年的邵逸凡,在温哥华,她一边遛狗我们一边完成了一部分的采访。2024年6月,她放下刚有起色的演员生涯,离开上海跟随伴侣去了加拿大。夏天的时候,她靠兼职遛狗一个月挣了2000加币。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在想,那个女生有没有想过这个给她遛狗的人是个演员,在中国的微博上有二十几万的粉丝。”邵逸凡说。她笑了笑,“我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愧疚,我觉得自己躺得太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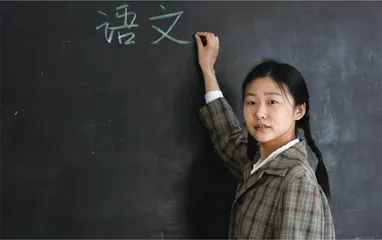
卷又不想卷,不卷又愧疚,这是一种卷过的人常有的情绪。今天的邵逸凡和曾经的自己过着完全相反的生活。
1989年,邵逸凡出生于辽宁沈阳的一个小康家庭,父亲是国企员工,母亲是大学老师。从很小的年龄开始,她就有了变得优秀的条件和推力。
5岁,邵逸凡就在少年宫的学前班学习舞蹈,课外她一周一次地学习电子琴。“对门的小朋友每次过来找我玩,都得等我练完琴。一个曲子每天要练15、20遍,他就在旁边数我弹到第几遍。”小学以后,邵逸凡喜欢唱歌,母亲给她报了声乐课。那个时候,每个周日母亲骑着自行车,上午带她去学声乐,下午去学琴,学完琴再去省文联学乐理。虽然忙碌,但这样的生活并不是她厌烦的部分。
“对门的小朋友每次过来找我玩,都得等我练完琴。一个曲子每天要练15、20遍,他就在旁边数我弹到第几遍。”
小学二年级下学期,生活发生了改变,有一天,她和母亲去书店遇到了一个同班同学,她们发现,同学已经在学初一英语了,但邵逸凡连“apple”都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妈震惊了,觉得我被落下了。”于是很快地,母亲在家里准备了一台电脑,又弄来一个多媒体软件,让她跟着电脑学英语,每天学习英语1-2个小时。以前母亲经常会在家里放音乐,但在那之后,家里的背景声总是英语。“只要我早上一睁眼,耳边就全都是我背过的课文,做梦都是那些玩意儿。”
放假,对邵逸凡来说不是休息,反而是更累的存在。假期的早上7:30,她起床,8:30到11:30学英语,下午练琴,之后接着学英语,一天要学习英语累计四五个小时。
她在16岁就参加了高考,接连跳了两级。高二,父亲的工作调动要去河北,全家户口也转去了那边,相较于沈阳,河北分数线更高。邵逸凡一直是全校文科第二,但她高考那天发挥失常,志愿也没报好,最后以比本地同学高了快100分的成绩去了天津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母亲帮她选了这个学校,因为这个专业有钢琴的双学位。
对于现在的邵逸凡来说,让她形容自己为优等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她已经抛弃了“赛道”的叙事,但她早年的人生轨迹的确印证了这一点。小学五年级就考到了业余电子琴最高级,连跳两级还能考上省重点,大学英语和钢琴双学位毕业,大三以专业课第一的成绩拿到全系唯一一个去德国斯图加特交换的资格,在德国留学期间开始学习德语,足以完成日常对话,也足以用德语做一次完整的presentation的水平……这几乎是一个标准的优等生开场,除了高考没有考上一个令人咋舌的学校。但不复读是她自己的选择,考试完的书,她第二天就全部卖掉了。
2010年,邵逸凡从本科毕业,她去了新东方英语学校当英语老师。这是一份完全专业对口的工作,和母亲的职业一样。工作很顺利,学生很喜欢她,但是她发现教育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她以为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帮助一个人脱离原来的阶层和生活,但其实大部分高中生已经定型了,他有什么样的学习习惯,见过什么样的世面,接触什么样的资源,从小就被决定了,“我很迷惑,老师到底能干什么?教育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学时邵逸凡读过一本小说,叫《杜拉拉升职记》,书里面杜拉拉踩着高跟鞋,穿着西装,在摩天大楼里面走来走去,在天上飞来飞去,每天和她开会的人都是精英,过着看上去是“样板间”一样“好”的生活。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繁荣,不论起点如何,只要足够努力,每个人都似乎被许诺了成功和幸福。邵逸凡很好奇,她想成为那样的人,前往那样的生活。
尽管她后来在每一个采访里都说自己是普通人,但那绝不是全部,她有着能直接将想法落实的惊人执行力。2012年,还在新东方当老师的同时,邵逸凡开始在西门子工作,起初她要得不多,只在咨询部门做辅助工作,类似助理。
没待到一个星期,就有公司里的人跑过来告诉她,她辅助的那些咨询师们觉得她做辅助工作有点大材小用,“她太特别了,看起来就不属于那里,她应该做咨询师。”回头看,邵逸凡不知道这份特别是什么,她归功于自己当时在德国“学着也许未来有用”的德语。
那时候她吃不下饭,一米七的身高,瘦到只剩下九十斤,一直在崩溃,打电话给母亲的时候哭,打电话给朋友的时候哭,在老师面前说着说着也哭。
“那里的老板是德国人,你随便在走廊遇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碰到,跟他讲两句德语,人家马上就认识你了。公司里有中国人会德语,能聊天,还能讲几个笑话,他们就觉得太奇怪了,而这样的人竟然在一个非常小的组里。所以平常有活动,他们会叫我去,就越来越熟。我问他们,我要是想加入咨询师该怎么加入?他们说我们的学历都有门槛。”邵逸凡回忆说。
那就去读书“镀个金”。邵逸凡在新东方当老师的时候也会几个月就要考一次托福、GRE,所以成绩她都有。几乎没有花什么钱,她不费力地就把学校申请了,但只申请了三四所学校,都是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这样的级别。因为天津师范大学不是“985”和“211”,所以母亲一直希望邵逸凡能继续读一个研究生,知道她的申请后,母亲觉得邵逸凡没有认真在做这件事情:“你要是认真的话,你是要有备胎的。”那时候的邵逸凡非常自信,她回答母亲说:“宾大就是我的备胎。”
约一个月之后,正在西门子上班的邵逸凡收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院文化社会学系的录取通知,宾大还给她发了奖学金。2012年下半年,她的坐标从北京变成了费城,一切都仿佛一个美好故事的开端。
触底
过去了13年,邵逸凡依然会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课堂。“梦到选课马上就要截止了,但是我还没把课选好。”
2012年8月底,犹豫不决要继续上班还是去学习的邵逸凡,几乎是踩着点去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别人多是提前一周、半个月过去找房子、倒时差、购买教材。她在当天早上七点半才抵达费城,下午就是报到仪式,除了给自己提前订下一个学生宿舍,其它什么都没有准备。更令她感到崩溃的是,那天时差都还没有倒过来,同学就已经在讨论小布什提出的“No Child Left Behind”计划,十年前的法案,她却连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过。
被推着走,被全方位地推着走。在宾大,邵逸凡的专业一共14个人,4个国际生,一个加拿大人,一个高中就过来读书的中国人,一个韩国公派的大学教授,还有她,剩下的10个人都是从哈佛、耶鲁本科毕业的美国人。
她修的专业是社会学,几乎天天都要写文章。以前她觉得GRE写作3.5/4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突然她发现班上每个同学几乎都能考5.5/6。她骤然从优等生的次列里跌落了,“都不是比他们差的问题,而是根本跟不上。”邵逸凡说。她总是写不完作业,每门课每周都有一本阅读材料,几门课就是几本,专业书籍很晦涩,根本看不完。
本来第一个学期的课程就已经够艰难了,第二个学期她还选了一门MBA的会计课,那堂课上其他人都有商科背景,只有她毫无会计基础。她专业课程里本身还有一些统计的内容,要学编程,她不是一个细心的人,程序总是有bug,但是她总是找不到bug在哪儿。“没有一门课是让我省心的,每一门课都是困难重重,每走一步都感觉自己要挂掉了。”
在宾大的第一年,她每天都在图书馆待到凌晨三点,图书馆关门之后她还回宿舍楼的自习室继续写作业。但那种学习和以前的感觉不一样,邵逸凡回忆说:“我觉得是在拖延,都不见得看进去了,但是作业没做完,我得做。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学习,就觉得效率很低,但是我又没办法睡觉。”那时候她吃不下饭,一米七的身高,瘦到只剩下九十斤,一直在崩溃,打电话给母亲的时候哭,打电话给朋友的时候哭,在老师面前说着说着也哭。
有一次她没忍住,直接当着自己社会学老师的面哭了,那位老师理解不了,他不知道邵逸凡在抱怨什么。她记得他说,觉得这件事难,那就去克服,如果觉得自己克服不了,那就放弃,去做别的,她不是非要做这个。他俩“鸡同鸭讲”,邵逸凡从这样的话里得不到丝毫安慰,对于当时的她来说,放弃都不是一个选项。
之前,她被“鸡汤”包围,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就什么都做得到,没有干不成的事,现实也给了她足够的正反馈,但是在宾大,这个信条失灵了。她成了差生,但是心态上还没有接受,也不敢接受,她陷入了持续的内耗。“我不会怀疑是‘鸡汤’的错误,我觉得是自己不行,觉得自己任何方面的极限都很低,然后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
其实2009年邵逸凡在德国斯图加特交换的时候,她就已经觉得不太对了。她一直很喜欢弹钢琴,那时候她经常去音乐学院“蹭”钢琴弹,认识了一个在斯图加特音乐学院念钢琴系本科的朋友,她就发现自己背谱没她快,弹得没她好。有的人有绝对音感,甚至可以用钢琴还原汽车刹车的音调。在这条路上,虽然挫败,但她接受了自己怎么努力都很难做到,宣布了自己钢琴梦的破灭。那时候她有理由可以找,那个同学的父母都是音乐学院教授,从小就走了专业道路,而自己大部分时间在学习文化课。到了宾大,连可找的理由都消失了,她不得不认定自己在学习这条路上也似乎没有什么天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