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藏品的数字化应用
作者: 王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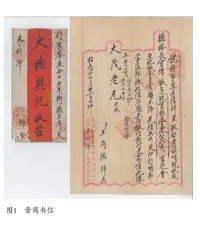
博物馆藏品的数字化是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有效手段,是博物馆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主要从藏品数字化对博物馆发展与观众参展的重要性,如何建立数字藏品档案信息系统以及如何做好系统的更新、完善,怎么做好数字化展示等方面进行论述分析,在探索数字化展览的同时思考如何有效解决现阶段数字藏品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博物馆与数字化的融合发展提供参考思路。
博物馆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重要场所,但传统的藏品展示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展示空间受限、展示内容有限、藏品管理的工作量巨大、藏品保护与展示的矛盾与冲突。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与运用,数字化的概念也被引入博物馆的保护工作中。不得不说,博物馆与数字化的有机结合,重构了展览的工作中心,使观众化被动接受为主动参观。博物馆历史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博物馆突破了传统的线下参观方式,增强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播力度,也为博物馆未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藏品数字化的重要性
博物馆作为一个时代、一个特定区域的文化传播窗口,其传播的途径与通常的新闻、广告等有所不同,它主要依托藏品,通过特定空间、时间段藏品的集合,并配以一定的文字解说来进行陈列展览。藏品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通过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在展陈中发挥特有的作用,而观众感兴趣的往往不仅仅是藏品本身的文化特征,更多的是藏品背后的历史故事。因此,藏品的数字化保护不仅满足博物馆发展的需要,更是响应观众参展的需求。
有利于文物的保护与管理。藏品数字化是将博物馆的藏品进行数字化拍摄、三维扫描等,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将藏品进行数字化还原的过程,实现了“文物”资源到“数据”“文件”资料的转变。藏品数字化将静态、无声的文物转变为动态、有声的多媒体格式,拓展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模式,也是博物馆打破时间、空间限制,建立与观众连接的重要媒介。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不仅避免了一些藏品与观众的直接“接触”,也避免了有些“脆弱”的展品的“损伤”,如晋商博物院《天下晋商》展览中晋商账本、书信、照片等纸质文物展品可能因多次翻阅而造成磨损、破损等,而这些损伤大多是很难修复的,加之这类纸质文物具有稀缺性,不少纸质文物都是“孤品”。与其修复不如从源头上进行保护,藏品数字化便为此类展品的展示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效解决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此外,纸质文物容易在展示过程中受潮、发霉等,数字化技术也避免了这一情况。
优化游客参展模式。藏品数字化本身不受展示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让游客随时随地观看、查阅展品信息,提高文物资源利用率,尤其是通过三维数字扫描与建模实现展品与观众的“零距离”接触,而且还可以放大展品看其细节处,如纹饰、图案、铭文等。这样一来,尤其是对一些又高又大或者摆放位置较高的展品,观众甚至可能比实地参观都看得清楚、了解得仔细。对于一些已经丢失或保存不完整的文物,也可以“完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样不仅丰富了博物馆的展览展示方式,也满足了游客随时随地看展的需求。如天龙山石窟博物馆《复兴路上 国宝归来——天龙山石窟回归佛首特展》中通过3D打印、数字复原等形式还原了佛首所在的第八窟。天龙山石窟博物馆还对流失到海外9个国家的108件石窟造像进行了三维数据采集,完成11座石窟的数字复原工作。
数字藏品档案系统的建立
确定统一的藏品信息收录标准。数字藏品档案是指对不同藏品数字化资料进行信息收集、存储、管理等,主要通过藏品的平面图、3D立体展示、文字描述等信息的管理、分析与呈现,实现藏品的基本信息存储、更新、检索与应用。在大量数字藏品信息收录过程中,由于不同类别藏品的差异性,需要有不同的信息采集、录入格式,如博物馆常见的古籍、字画等纸质文物,也有青铜器、陶器、瓷器、玉器等大型器物,还有古树名木等植物。这些实物资料由于类别、保存方式、形态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信息采集过程中,需要依据具体的规范和标准进行,如依据《博物馆藏品信息指标著录规范》,在确保统一录入格式的前提下,不同类型器物又体现差异化的信息。
建立数字藏品档案系统。数字藏品档案系统通过建立合理的分类与整理标准,收录藏品基本信息,实现藏品信息存储、更新、检索与利用。这样不仅方便藏品管理,也可以快速查找、检索藏品信息,丰富了博物馆藏品管理的手段,大大提高了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也方便了藏品的研究与展示,能更好地服务观众群体。数字藏品档案系统不仅需要藏品的数字化电子资料信息,也需要藏品丰富的历史背景信息与深度解读,这就要求档案系统不仅要不断完善、更新现有信息资料,还要加强与高校、学术界等的大力合作,与其他博物馆进行信息的分享与互动,为藏品获取更多最新的资源信息与研究成果。
档案系统中大量藏品数据信息的收录直观地展示了馆藏现状,也为藏品统计分析提供了完备的信息资料。同时,通过对数字资料进行备份处理,可以有效避免传统藏品丢失的风险。博物馆也可以利用数字档案系统中高清的藏品图片与视频等创新展陈形式。例如,制作宣传片,将藏品图片、视频投放到地铁、商业街等人流密集区的大显示屏上,进行博物馆展览的宣传,这加大了博物馆展览的宣传力度,拓宽了博物馆的宣传范围,提高了博物馆的运营效率。
藏品的智慧化展示
展品作为博物馆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博物馆文化遗产与受众连接的纽带,是大家了解、认识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智慧化展示是数字藏品与博物馆深度融合的产物,是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头戏”,观众通过官网、微信小程序、手机App等线上途径可以直接观展。
智慧化展示是藏品数字化集合的产物。在陈列展览中,博物馆数字化与智慧化是分不开的,智慧化展示是基于数字藏品档案系统,以数字化藏品信息为前提,结合虚拟现实手段、语音导览等,并辅以文字信息进行介绍,为观众提供多元化、深层次、多角度的藏品信息展示。观众可以依据自身需求选择局部信息解读,或整体展品介绍,或基础问题回复,还可以选择辅助讲解,了解藏品深层次知识体系。如晋商博物院《热血山河》展厅中毛笔、报纸、书信、草鞋、地图、徽章等的相关讲解,不仅介绍了这件展品的使用时间、使用人物,还结合1935年八路军挺进山西的历史背景,延伸了人物的生平事迹、生活场景还原等,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完整的历史画面。
智慧化展示支撑智慧博物馆建设。智慧化展示主要通过使用电视、电影、幻灯片等现代视听形式,调动观众的感觉、听觉、触觉等,让观众实现沉浸式的虚拟现实体验;也可以依据不同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服务,如观众可以绑定微信小程序或点击展厅电子互动屏,获取语音导览讲解服务等。
展陈过程中运用3D打印技术,可以让计算机在三维物理空间中复制出与当时人们生存环境一样的空间环境,通过巧妙的灯光设计与布局结构,结合听觉、视觉等感官刺激,可以让我们在其中真切地感知到当时的情况。同时,观众也可以转化自身角色,通过触摸、听觉、感觉等主动探索,感知藏品的历史文化背景,这种沉浸式的数字交互体验形式,为观众提供了全方位的“真实感受”,仿佛置身于当时的历史场景中,给人直观且深刻的印象。例如,云冈石窟音乐窟通过运用3D打印技术,将其“完全复制”“平移”到浙江大学,这个可移动是复制品不仅在重量上要轻很多,而且在运输和组装上也很便捷。3D打印实现了石窟的远距离“搬运”,也为下一步巡展提供了新思路。
这种智慧化展示模式为智慧博物馆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例如,晋商博物院《天下晋商》展览中,“九边重镇”展厅就是通过还原明朝防御外敌入侵的场景,展示了九个重镇的具体地理分布、具体防御路线,以及发生战争时的炮火声,让观众能够切实感受当时的场景,给人不一样的参展体验。晋商博物院勤远楼数字多媒体展厅还原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远赴恰克图进行茶叶、丝绸等大量货物的边境贸易的场景。其中,阵阵的驼铃声、优美的音乐以及触手可及的“贸易场景”让人有一种深深的代入感,深刻感受到明清晋商的辉煌时刻。总之,智慧博物馆从展览场景还原、语音导览服务、咨询等多方面入手,为游客提供便捷、及时、高效的服务体验。
数字藏品在应用过程中面临的新挑战
博物馆数字化面临信息安全问题。随着网络安全问题的出现,藏品信息的隐私泄露、侵权使用也不可避免,数字藏品资源的安全受到了巨大威胁。我们可以通过设置访问权限、加密等技术手段,以及签订保密协议等方式进行藏品数据保护,谨防数据资料外泄。数字藏品资料信息系统作为博物馆藏品的管理系统,不仅需要定期更新藏品信息,满足博物馆展陈的需要,还需要有专业技术人员对藏品系统平台做好日常监测、更新与维护。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招聘专业技术人员,同时对员工进行定期培训,以做好信息系统安全工作。
此外,在馆际合作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博物馆的展品信息标准不统一,所以馆际合作困难重重,而且不同博物馆的系统之间也存在不兼容的问题,这就严重影响了数字资源的管理与利用。尤其是一些小型博物馆,如县区博物馆、私有博物馆等,数字化程度普遍较低。因此,制定标准化、统一化的数字资源信息平台,保证藏品数字格式统一是必要的。未来应加强馆际合作,加大数字资源整合与共享力度,尤其是为小型博物馆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助力小型博物馆提高知名度,同时增加游客量。
博物馆是藏品与观众建立联系的重要纽带,藏品的数字化是博物馆藏品管理、收藏与保护的重要手段,也是博物馆智慧化展示与服务的基础保障,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为了满足现阶段博物馆收藏、展览工作的需要,以及观众不同的参展需求,博物馆需要通过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构建统一的数字资源信息平台,不断地改进、完善数字化技术,不断更新、升级数字藏品档案系统等方式,提高数字资源管理能力与水平,在藏品保护与管理、优化游客参观模式、丰富博物馆展览展示等方面创新性发展。
(作者单位:晋商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