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静》的时空叙事
作者: 邓雅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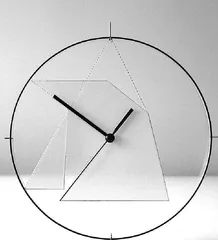
《静》是沈从文创作于1932年的一篇短篇小说,它讲述了一个战争年代逃难家庭的故事。不同于以往的战争题材文学作品,小说中少有直面战争的文字描述,取而代之的是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淡化情节与含蓄表达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拓宽了读者的审美想象空间。在缓慢流淌的时间里消解等待的无尽期盼,在绿水青山的空间中展开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以看似平静的语态为我们展现了不平静的战乱纷争,凸显了沈从文的人道主义关怀。在笔者看来,这部小说最大的特色是其独特的时空叙事结构。
时空叙事重点关注文本中的时间与空间,二者是故事中人物生存所依赖的基础环境,也是小说叙述语言建构的两个基本维度。《静》在空间的转换与时间的延续中,一方面凸显了空间并置下的“时间空间化”,另一方面又深刻揭示了个体生命时间与历史叙述时间的困境。在这二者之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希望与失望”的反差作为文本的精神内核自始至终贯穿于字里行间,彰显着作者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一、空间并置下的“时间空间化”
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小说作为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自始至终离不开对叙事空间和叙事时间的依赖。同样道理,对于小说意义的探究,从叙事时空视角切入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这就如当代学者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中指出的:“叙事学研究也是既存在一个时间维度,也存在一个空间维度。”可以说,将小说叙事研究置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美国文学评论家约瑟夫·弗兰克在《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一文中,就提出了“并置”的创作批评概念,即“在文本中并列地置放那些游离于叙事过程之外的各种意象和暗示、象征和联系,使它们在文本中取得连续的参照,从而形成一个整体”,他强调打破叙述时间流,使单一的时间叙事空间化,处于多个空间的意象与短语并置存在并相互参照。
空间往往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对于揭示人物行为、性格、心理、情感等方面均具有独特作用。其中,阁楼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历来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在文学作品中总是关联着特定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例如,在巴金的《寒夜》中,阁楼是小知识分子汪文宣一家走向没落的发生地,楼上的寒气扑面与楼下的空阔凌乱互为参照,预示着主人公凄惨的命运;在张爱玲的《金锁记》中,阁楼是曹七巧一家沉沦于金钱的集散地,楼上的清冷寂寞与楼下的决绝无情互为补充。可以说,文学中的阁楼大多超越了实际的本体意义,而形成它的独特的空间隐喻,成为生活经验与审美意识交织的复合体。同样,在沈从文的小说《静》中,阁楼不仅成为主人公的生活场所,也分隔并连接起了世俗与诗意、时代与个人,支撑起了整个小说中的生命书写。可以说,沈从文的短篇小说《静》正是巧妙运用并置技巧,“楼上”与“楼下”作为小说主要的叙事空间,两个空间场景并置叙事,人物在二者间来回切换,以此推动叙事展开,这既摆脱了传统小说的单一线性时间的沉闷与乏味,又体现了现代小说时空并置而创造出的时间空间化的美妙境界,进而让我们又一次见识了沈从文“现代文体家”的独特魅力。
在小说《静》中,晒楼的“楼上”显然是一个暂脱现实的幻影空间,是浪漫理想与内心希望的代名词;而“楼下”则是寂静祥和下悲戚等待的现实空间,是残酷现实与落寞失望的同义词。“上了晒楼,仍然在栏干边傍着,眺望到一切远处近处,心里慢慢的就平静了。”对河小庵堂里的桃花、漂浮在河面上的渡船、染坊中人们收拾的白布,尽收楼上观望者的眼底。对于岳珉来说,“楼上”是一个眺望远处、遐想未来的空间,她在这个空间里看到的所有意象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和宁静的氛围,共同营造了楼上一个远离战乱和喧嚣的宁静世界,使她感受小城生活的静谧美好,暂时脱离母亲病重、音讯未见的现实。而与楼上的宁静相比,“楼下”的空间则主要聚焦于母亲卧病的小房子内。家里其他人各有事情,为窘境所困,如母亲有病吐血躺在床上,大女儿和媳妇出外求神问卦,丫头在洗衣服等。面对病痛中的母亲,岳珉常讲述自己的好梦,姐姐与嫂嫂也是勉强微笑的状态,文中有这样的细节描写:“女孩岳珉不知为什么,心里尽是酸酸的,站在天井里,同谁生气似的,红了眼睛,咬着嘴唇。”在楼下,人物直面现实世界,其复杂的情绪和在楼上时心中的宁静全然不同。在历史的沉重与生活的艰辛交织、死亡的阴影与希望的渺茫共存下,信件和梦境带来的只是虚妄,剩下的是死寂中对于现实的无奈酸楚。“楼下”作为人物直接发生关系和情节发展的场所,是一个在乐观笔调下揭露人物在历史战争下等待、彷徨的现实空间。“楼上”与“楼下”两个场景虽然相互独立,但因岳珉在它们之间来回地穿梭而建立起联系与对照,两个空间场景便巧妙地形成一个叙事整体,共同指向孤独而冷寂的现实世界。
而在“楼上”与“楼下”两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场景之中,楼梯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既是岳珉和小男孩情感交流的空间,也是独处楼上的岳珉心灵慰藉的通道,更是理想梦境与残酷现实来回切换的桥梁。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借助小男孩一次次在楼梯上爬上爬下来实现的。楼梯的这种升降功能就如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所说的:“一切上升和下降的地方都重新开始被生动地体验。”当岳珉在楼上“望到一个从城里不知谁处飏来的脱线风筝,在头上高空里斜斜的溜过去”,正享受一时的宁静遐想与满心期盼时,小男孩上升的脑袋又让她回到无可奈何的现实。与此同时,小男孩一次次试图加入楼上队伍的试探,表明了同样作为弱势群体的他,同样渴望得到比他年龄大不少的小姐姐的关爱。可以说,楼梯意象看似寥寥几笔,实则起到了连通人心以及理想与现实关系的作用,其意义同样不可替代。
场景时间空间化理论是弗兰克时空叙事理论的一个起点,当场景插入小说中,叙述时间被中断,即时间空间化的完成。罗钢在《叙事学导论》中认为:“在停顿时,对事件、环境、背景的描写极力延长,描写时故事时间暂时停顿。”小说《静》中场景时间空间化、情节时间空间化打破传统小说单一的线性叙事,充分体现了静谧之下人物的情绪表征和生命流动。在小说中,岳珉上到晒楼后,大部分描写其眺望到的景观和小城中的人和事,如文本中反复渲染“对岸那块大坪,有几处种得有油菜,菜花黄澄澄的如金子。另外草地上,有从城里染坊中人晒得许多白布,长长的卧着,用大石块压着两端”,“对岸那块大坪”“另外草地上”等要素构建一个空间、一个场景,读者跟随叙述能够在脑海中构建这样一座小城的空间样貌,此时故事时间凝结,叙事时间即文本的展开却仍在继续,转到了对场景的描述。“场景实际上是反直线的。”(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场景作为空间表现形式,通过打破时间的线性流动,使叙事文本中原本以时间性为表意基础的结构呈现出空间化特征。
而其中“这渡船宽宽的如一条板凳,懒懒的搁在滩上……那船在太阳下,灰白憔悴,也如十分无聊十分倦怠的样子,浮在水面上,慢慢的在微风里滑动”,人物的情绪潜藏在场景描写中,对远方父亲来接人的憧憬化作对船开动的盼望,扩散在文本给予读者淡淡的且静谧的伤感氛围中。场景时间空间化是一种减缓与停顿的手法,这种方式展现了湘西叙事中的静谧与和缓,使得时间在文本中呈现出一种停滞的状态,强调了故事中的静态美。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场景“充满生命情感又往往‘暗藏玄机’”,能够“直接体现着作家的宇宙时空意识”(赵奎英《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看传统叙事结构的空间化倾向》)。
二、个体生命时间与历史叙述时间的困境
如果说小说“时间空间化”的空间叙事还体现了沈从文对于生命主体情感流动的赞美与同情的话,那么小说《静》在时间叙事方面则更多地体现了对于个体生命面对历史宏大话语时无法逆天改命的弱小与无力。在这部短短五千余字的短篇小说中,作者巧妙地将微型的个体生命线性时间置于庞大的文本历史时间之中,个体时间如水滴融于历史长河,个体生命时间呈现出一次性与短暂性,文本历史时间则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二者的交织将个人置于庞大的历史叙述中,显现出个体生命的荒凉感与悲戚感,同时也强化了小说时空叙事所蕴含的悲剧与底层同情。
小说《静》中全文大部分根据岳珉个体生命的单线时间叙事,如楼上眺望、晒衣、下楼为病重的母亲倒热水……尽管中间穿插一家人逃难到此的背景,但仍然是由人物遐想思绪带出,前文多是单线时间叙事,且聚焦于岳珉这一个体生命,小说里“女孩岳珉心里很希奇的想到:‘谁在问谁?莫非爸爸同哥哥来了,在门前问门牌号数罢?’”人物处于现实与幻想的横跳中。而结尾“日影斜斜的,把屋角同晒楼柱头的影子,映到天井角上,恰恰如另外一个地方,竖立在她们所等候的那个爸爸坟上一面纸制的旗帜”,时间叙述跳出岳珉的个体生命时间,转至历史叙述时间,文本揭示岳珉幻想中的父亲已经过世,现实与幻想的界限在时间置换中被打破。
在个体生命线上对父亲来信的期待随着置换变得荒谬与虚无,生与死的界限被打破,叙述文本产生了奇妙的效果,将渺小的个体与时间洪流的宏大命运两条时间线交织,反衬人物在当时处境的荒凉感,造成个体不可知的感伤。另一层面,除故事人物之外的全知视角,是从历史角度中以超越历史的姿态实现对个体生命的观照,展现个体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困境。个体处于失语状态,但文本具有发声作用,明知渺小而去展露渺小,体现了沈从文的人文关怀。随着“日影斜斜的……映到天井角上,恰恰如另外一个地方”,这种隐含的人文观照和情绪潜流汇聚在这个点,达到一个高峰,将处于历史“意义”裂缝中的空无所在与生命相连,发现偶然的人与事以一种缄默的方式绵延重复。生死的无常与历史变迁相互浸漫,个体生命线性时间和文本叙述命运时间的交织丰富了沈从文小说叙事的意义深度。
这部小说取名为“静”,“静”字一共在文中出现了九次,但这个“静”字无疑包含了多重的时空审美意蕴与社会现实内涵。显而易见,“静”并不仅局限于时间的无声静流,而是囊括了人被死亡阴影包裹的“楼上”和“楼下”空间上的寂静,以及等待男主人信件与讯息的安静;“静”并不仅局限于生命在时间上的无助承受与默默等待,而是喻示了个体被社会空间裹挟下的无声反抗与惨然面对。在这部小说中,故事情节无疑是作者的关注点,这就如夏志清所指出的,短篇小说《静》无疑是沈从文文学艺术成就的集大成者,小说“糅散文和小说故事为一”,“成为现代中国小说一格”,“自成一个新的型式”(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沈从文的小说《静》表现出散文式的美感,其通过各种意象与联系将“楼上”与“楼下”两个场景并置,楼上的恬静安宁与楼下的寂静现实相对比;同时,场景的大量描述使时间空间化,时间的停滞和流动随着空间转化而变化生动。另外,小说的碎片化叙事,较多地展现出人物的情绪潜流与生命体验。而在文本叙述情节当中,个体生命时间和历史叙述时间在文本中置换,揭露了文本中的人物困境,丰富了小说叙事的意义深度。小说的主旨除了山水之静外,更有梦幻割裂感中的“感时忧国”的情结,这种悲怆就像结尾处屋角晒楼柱头的影子,潜在却笼罩在诗意的文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