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上海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吴方笑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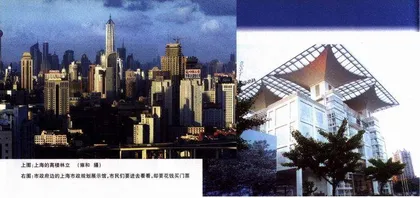
上海高楼林立(雍和 摄)
市政府边的上海市政规划展示馆,市民们要进去看看,却要花钱买门票
磁悬浮列车与金茂大厦
中国首条磁悬浮列车将在浦东上马。这条线如果建成,也将是世界上第一条商业区运行的磁悬浮列车。未待更多的争议,市府和专家们已经进入确定这条轨道到底修在哪里的议程。最佳方案是把磁悬浮列车从9月刚刚开始运营的浦东机场修到东方明珠塔下。造价昂贵,运客量小,
还不是反对者的主要意见,人们对于德国原本要在2000年开工的一条磁悬浮线路工程的下马有些警觉,他们不做,我们引进来做?从技术到资金能力方面是否到位?
但上海人的决心已不容游移不定。因为这一举动,就像矗立在东方明珠身边1999年初建成的420米高的金茂大厦一样,在塑造着上海外滩新景观的同时,也向全世界表明上海争当国际化大都市的姿态。
磁悬浮列车将势必构成另一个象征。中科院院士、我国最早参与磁悬浮技术研究的科学家严陆光表示,“在此项目的带动下,可以有效地开展国际合作,引进消化国际先进技术与经验,进而有效地组织我们自己的研究发展队伍,逐步建立起我国高速磁悬浮体系。”
上海市政府的很多行为正与此种思路一脉相承。“上海有很多组织纪律严密的产业工人,他们很善于琢磨,建第一座南浦大桥时,钢板架上去的工程难度非常大,他们用了2年时间建成;到了第二座杨浦大桥的时候,只用了一年半,第三座徐浦大桥,就用了9个月。”上海交大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方华不无感慨地说,“第一座盖得很努力,第二座就可以马上建得非常好,很快技术就输出了。”
像企业一样的政府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民族的竞争将越来越落到城市对城市的竞争。世界将是一个全球城。”从90年代初就开始搞全球化对城市影响研究的吴志强教授,以非常赞赏的态度看待上海市政府的作为,“我真的很吃惊,西方城市管理刚刚从管理主义走向企业主义,上海市政府就已经是在经营城市了。南浦、杨浦大桥建好之后,他们前面还在宣传,后面就悄悄地把大桥的经营权卖掉了。这样钱滚钱,不断地投资新的项目。”吴志强教授认为,一个有作为的市政府,不必非要走与企业联合、帮企业拉合同、挣钱、解决就业的老路,“上海市政府直接自己去做,这么强的经营意识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利用有效资金把城市的基础设施做好,这是很有政绩的。”
据了解,金茂大厦现金流量最大的一天,经观光厅流人公司账本的现金是50多万。东方明珠,50元一张票起步,每天登塔观光的人数也不在百人之下。“东方明珠也是政府投资修建的项目,现在的利润就疯了。这种既能在城市面貌上大做改观,又能攒大钱的事,做起来多聪明。”吴教授说。另一件让学者们赞赏的举动,是高架桥的一次到位,“五任市长,一直想修高架桥的,钱不够就拿在手里,不乱花,时机一成熟,立即就把这件事做好了。当官的任期就三年,为一个城市真正长远的目的打算,不容易。”
有消息称,从全球资金流动中,上海招徕了最多的外商投资。王方华教授指出,外资所以大量流向上海,与政府对政策的灵活恰当运用密切相关,“土地批租,就是把外国大公司请进来,50年或者70年你拿去投资这片土地,50年后能带走什么?管理留下来、环境留下来、人才也留下了。”据王教授介绍,目前上海比较好的合资企业都是中国人在做管理,“德国大众对物资的有效利用做得很好,上海马上在全市推广;跟日立合资,头五年是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学,不要讲创造,那时没有能力创造,就看人家怎么做;第二个五年是双方共同创造,到了第三个五年把技术全学过来了,就完全自己创造。上海就善 于这么做。”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目前拥有高层建筑达2600多幢,100米以上的超高层有50多幢。这列超高速列车,近七年来国民总产值每年以12%的速度递增,到1999年人均GDP已超过3700美元。它已经超过了北京。
然而也有人对这个“大企业政府”的某些决定不满意:“市政府花14亿修上海大学,因为它需要一个大学的窗口。我本来上的是上海工业大学,它的名气总比上海大学要好一些,可学校合并,我要拿一张上海大学的文凭。真泄气。”
“修桥还是修隧道,修桥贵,修隧道便宜,但大桥谁都看得见,所以有的官员喜欢修桥,让它成为标志性建筑。”一位上海学者说,“你可以感受得到,这座城市正竭力把自己装扮得美丽,充满诱惑力,到处霓虹灯,到处高楼大厦,复旦拆掉老建筑,要修一座30层的高楼,哪有这样的大学,这个举动太像这个城市,物质性的东西太多了,人文精神的东西太稀薄。”
“西方人很喜欢上海”
去年11月从中央电视台到上海一家美国公司做高级主管的陈骞告诉记者,他觉得在上海越来越像在美国。“我在美国、北京都待过,在北京每天都会知道总书记、全世界人民在干什么,好像这是很自然的。到了上海以后,开始我还买报纸,看新闻,慢慢发现你周围没人这么做,也没人跟你谈这些,大家就是注重眼前做的这些事,上海的新闻也不活跃。”
对于商业社会而言,更重要的也许还是人的因素。对于上海人的职业感,陈骞一直存留着1982年第一次来上海的印象:“我在一家小国营饭店吃饭,人很多,都站着等坐,一个老师傅戴副雪白的手套就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收拾碗筷,动作非常利索,一次手里拿很多杯子,却绝不会让人感到受影响。1982年上海人就是这么干活的,非常勤劳。
港人高建伟在北京遭受了一次长达5小时的堵车之后把他的“醉高台”餐厅选定在了浦东乐凯大厦,他说他看中这里交通便捷,更能感受到浦东蓬勃发展的势头。“这里的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
让陈骞们感到欣慰的事还有很多,例如到上海机关里办事更像是进公司,解决不了的问题公务员帮着想办法,连警察都更温和;上海还在推行将各种磁卡——看病的、坐车的、买东西的、存钱的——都搞成一卡通行,以减少人们带卡的负担;除了汽车和住房贷款,第三种医疗消费贷款又在推出;上海的商业意识甚至体现在一张刚过期的报纸上,卖报人绝不会以同样的价钱在周六卖出一份周四的报纸……很多人把上海的重新崛起比作又一个香港,但只有上海人清楚,他们的目标不是香港。每年春节,世界各地的大财阀都来上海聚会,上海人在与他们的交流中看着世界舞台上的纽约、欧洲的表演。
不及格?
吴方笑薇
“首先这个市长不及格,干部不及格,民众也不及格”上海徐匡迪市长两个星期前在上海一个“中华学人与21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上致开幕词后,回答提问时作出以上评语。
上海刚刚举行了“大都市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上海2000"国际会议。参加者多是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中华学人加上世界顶尖儿的国际专家共二百多人汇聚上海共同探讨上海21世纪的未来发展路向。笔者是惟一一位来自香港的民间环保工作者,专题探讨民众意识和参与的重要性。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令我最难忘的是“上下一心”的积极气氛。每位专家在提问或建议之前也都是这样介绍自己:“我是在荷兰工作的,我是上海人”、“我现在澳大利亚做事,我是上海人”,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及本国各省市的上海学者专家都是那么的齐心,关心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家乡,甚至出钱出力筹办会议,邀请国际权威学者和专家为上海提出新概念、新思维。作为一个香港人,亲身参与、观察三天的会议讨论过程,真是有莫大感触。首先本人很钦佩上海人的主动性,追求新理念的进取,为自己城市的未来动脑筋,集思广益,而香港人为什么少有这般齐心?仿佛是少了那份“以港人自傲”的冲劲?坐在两百多位众志成城的上海学者专家当中,我感到有点儿孤独,有点儿失落。
有些在海外留学工作的上海学者专家不但亲自回来参加交流讨论,还找到国际权威和策略家一并来献计。其中两位是美国总统的能源科技顾问,也亲临上海论述“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并预测未来世界人类、科技、生态、工业的挑战和机会,立著于其书《自然资本论》。年轻有为的副市长翻阅此书片刻,第二天便下令订700本并要求所有上海市主要干部参阅。敢于创新,接受前瞻性的思维,这些都是领袖人才的特质。
回到香港,翻开报纸,又是一段又一段的批评、谩骂、指责。现在的香港是否一个充满愤怒仇恨的城市?香港为什么成了一个找毛病的批斗擂台?香港人为什么“以港为傲”?香港人为什么不可以齐心合力为香港寻找21世纪的定位和突破?人家广东省都决心换调环保局长,去搞好环境,人家上海市也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平衡,那么香港有没有勇气站起来说一声“我也不及格!”新时代、新世纪的挑战和变量太多太
复杂,现在是需要我们集体学习、集体醒觉的时候,否则我们只有被淘汰,被别人赶上。

政府打造的一个窗口——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