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在看电视?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三联生活周刊)

电视的降价和普及给人们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刘向前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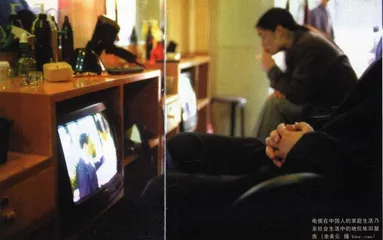
电视在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依旧显贵(余美云摄/fotoe.com)
“电视机的价格已经降到了令人轻视的地步。”北京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指着他客厅里的那台当年价值1万元的29英寸彩电说,现在国产的超平29英寸彩电不到2000元就能买到,“电视机的空前普及给中国人带来变化是显而易见的,电视彻底成为大众文化中最活跃和重要的传播者。”
根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CSM)发表的1999年度《中国电视受众研究》显示,中国的电视观众总数已达10.94亿,97.9%的城市观众和96.1%的农村观众可以在家里看到电视。在北京,家庭电视普及率已经可以约等于100%,46.5%的家庭有两台电视机,有5台的甚至超过了1%。喻国明带领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今年5月受北京电视台之托所做的调查表明,从周一到周四,北京市民平均每天看电视时间3小时23分钟,到周五达到3小时48分,周六周日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再增到4小时25分钟,比1年前的同期调查已经高出了1小时左右。
“我们还比不上美国人日均5个小时看电视的时间,一回家就把电视打开当作背景声已经成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他们与其说是看电视不如说是在听电视,”喻国明说,相比而言,“中国人打开电视后看的忠实程度就高多了。”
观众:是该从电视机前离开了
但越来越爱看电视的中国人似乎对电视越来越挑剔。“电视曾经是我们惟一的业余生活——甚至到现在几乎所有的三口之家还是这样,每天一到固定时间,人们已经习惯于打开电视。”在摩托罗拉公司上班的王军平说,“但你敞开的大脑现在几乎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人们只有机械而徒劳地用遥控器搜寻着各个频道,就像翻腾一个个垃圾箱,然后就这样翻腾一晚上,装了满满一脑袋垃圾上床睡觉,连浪费时间都浪费得这么无趣。”
这是年轻一代对电视最常见的不满。尽管王军平的丈夫就是一家电视台的节目制片,但丈夫比她更不喜欢看电视。“那是他们那个圈子的通病,有时间他们宁愿听着CD看书。”王军平说,“一帮高智商的文化人,却制造出最弱智的文化和信息垃圾,这是费解而难堪的事情。”
但电视在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依旧显贵。在家庭的客厅格局中,电视总是像被供起来一样安放在最黄金的视觉中心位置,然后沙发什么都是围绕着它设置。连续多年的调查,中国人节假日的娱乐活动,高高排在第一位的全是看电视。对7个城市18000名12-19岁青少年~课余生活所做的调查,67.6%的娱乐方式也是看电视。
“中国人该从电视机前离开了。”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对本刊记者说。1994年,白岩松去瑞士的时候,曾经参观过一个在日内瓦湖里有游艇的商人的家,在客厅里没找到电视,最后在卧室里看到了一台18英寸电视。“而那时候,我们早就21直角遥了。”白岩松说,“我们聊电视在他生活中占多长时间,他说占的很小。有点像咱们以前临睡前为了解决失眠的问题找本无聊的书看看。”同样,在电视业发达的西方许多家庭,现在晚上8点到9点已经成了无电视时间,家里人在一块聊天,孩子在爷爷奶奶之间跑来跑去,说说学校、社区和城市里的事情。“我希望在节假日的时候,人们去海滩,去河边,去迪厅酒吧电影院,朋友聚在一起聊天打麻将都行,别舍不得电视。”白岩松一再地说,“电视是生活的一种背景或者一种选择,但决不应该是生活本身。”
白岩松承认,让人们远离电视不能依靠习惯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它取决于全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取决于生活和娱乐休闲方式的多元选择,以及人们沟通的渴求。但在2000年谈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挺有意思。“1999年12月31日下午6点,我开始进直播间做迎接新千年的24小时直播,等凌晨2点多我出电视台,我蒙了——满大街全是人。然后我特高兴。说明那天人们不像春节一样只能全家守候在电视机前,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生活多样化而不再做电视奴隶的开始。”
一个电视人说这样的话并不是矫情,白岩松是聪明人。“人们开始离开电视前的沙发的时候,电视的水平只会更高。”在白岩松看来,表面上很挑剔的观众实际上并不挑剔,“当年东方时空开播的时候,获得了广泛的赞扬,可我们主任说,我们真有些对不起这种赞誉,因为我们只刚开始做电视应该做的事而已。”
“只有观众们有选择地打开电视而不再是沉迷于按遥控器打发时间,不再是做什么都有人看,电视人的压力才大了,竞争才真正地残酷了,才会绞尽脑汁去把节目做好。”白岩松说。
电视台:面对遥控器时代
对电视节目的不满常常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对电视人的不满。“他们要么是既得利益者,要么是被宠坏了的孩子。”北京一家报社的记者邓婷说。她本有机会进入电视台,但她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因为那是一个“缺乏竞争和动力的地方”。
在中国,电视这个最强力的媒体获得了双重优待:体制的垄断保护和商业环境的追捧,全国上下,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最多的时候各级电视台超过1700家,这一数字比电视业最发达的美国都要多出很多。即使经过近几年的反复整顿压缩仍有600家左右,它们所拥有的政府扶持和
频道资源垄断,使它们毫不费力地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中“最后一个暴利行业”。
然而,电视台的日子并不因有权获取暴利而高枕无忧。“从中央到地方的四级电视台中,中央台日子是最好过的,省一级属于惨淡经营或略有盈余,地县一级小台就基本上入不敷出。”喻国明说,“他们最普遍的问题是只管投入,不管产出。”即使是中央电视台,近几年的净收益也在急剧下跌。这家电视台每年的运作费用投入在35亿~38亿左右,而去年的收入已经降到40多亿——几乎全部来自于广告。去年11月进行的2000年中央台广告竞标给新的千年又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为了收获一个好价钱,中央台一改过去“坐地收钱”的方式,到各地联络感情,还取消了对酒类企业的限制,但最终的进账只有19.2亿元,比1999年大跌7.6个亿。
“中央台内部,尤其是高层心里其实都很明白,情况已经非常急迫。一旦净收益降到临界点的时候,它许多独有的优势——包括资金和人才——都会迅速丧失殆尽,他们内部的说法叫突然死亡。”喻国明解释说,电视是钱堆起来的东西,是重装备的产业,“不可能像报刊杂志那样可以小本支撑。”
航空母舰中央电视台尚且如此,其他大小省市台的危机就显而易见了——当然也有像湖南那样开始把电视节目当成商品经营的极其个别的例外。1999年6月30日,全国31个省级电视台全部实现卫星传送,总共41个上星频道和其他多达3000个无线、有线频道日复一日地播放着电视节目。在北京,40%的家庭能够看到40个以上的电视频道,“但预料中良性竞争的态势并没有出现,”北京广播学院教务处长胡正荣教授说,那些被寄予希望的卫视都像一个个没有区别、庞大而杂乱的综合频道,“大量低水平同质重复的节目令人愤怒地拥挤在这些毫无特色的频道中。”
“当我们手拿遥控器,我们已经从一个短缺时代到了过剩时代。”喻国明说,在足够多的电视台提供足够多播出时间的今天,观众手中的遥控器并没有点击到足够多的好节目。“观众的忍耐性再强,网络平台的出现、全球化影视业开放和产业化潮流也不会再给太多太长的机会。”常常出席各种电视业界研讨会的喻国明不断告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