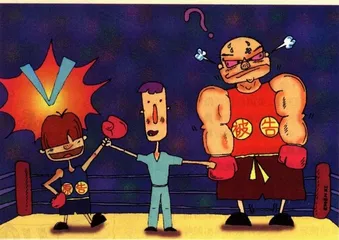要告就告大公司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刘芳)
麦阿密的律师阿比·卡普兰某日听朋友抱怨,他通过美国在线上网,按月购买上网时间,每次登陆不见页面先见广告,并被询问“是否需要了解详细情况”,答案肯定是不需要,可是必须回答“否”,才能被允许浏览。点击“NO”不过半秒,可那是用户买下的时间,美国在线凭什么强塞广告?卡普兰意识到,这是违约,于是他把美国在线给告了,当然不是以他朋友的名义,而是以所有像他朋友那样的美国在线用户、即一万多受害者的名义,要求美国在线赔偿数千万美元。
如果官司打赢,赔偿金额的二至三成就是卡普兰的律师费,那他将与告通用汽车的、告万宝路的、告美国之音的同行并列,登上集体起诉告倒大公司的美国律师英雄榜。
几百、几千、几十万或更多潜在受害者为同一事由状告同一事主,专业说法是“class action”,这在美国早就有先例,这10年更是达到高峰,仿佛大公司一告一个准儿。美国优秀的律师一般都从顶尖法律院校毕业,从法官助手做起,再加入著名律师事务所,但是近几桩集体起诉大公司的案子当中,原告律师的出身并不显贵,他们都是从办公室纠纷等小案子办起,一级级达到目前的位置。
让烟草制造商头疼的理查德·斯克鲁格斯出生在密西西比贫民窟,他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带着一帮律师与烟草公司对抗,那时候烟草堡垒牢不可破,谁都没料到,后来一退休专家透露万宝路厂商几十年前就知道吸烟会引发癌症却向公众隐瞒,民众的健康意识和国家的政治风向变得更加有利于反烟草。终于,今年7月,斯克鲁格斯的队伍打了大胜仗,法庭判烟草公司赔2460亿美元,其中100多亿归律师。
这可是美国司法史上的大事,是“class action”的福音。美国律师从此分成了两拨儿,一拨儿是大富翁,斯克鲁格斯刚买了一架喷气式飞机;另一拨儿咬牙切齿,自己当初怎么就想不到去宰烟草公司呢?两拨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思考着同样的问题:谁是下一个目标?
原则很简单,先找个有钱的机构,想想有没有可能找它索要赔偿,媒体辩论得正热乎的事通常都有官司可打。紧跟时代也很重要,校园杀手层出不穷,所以斯克鲁格斯和微软案大出风头的大卫·博瓦现在已瞄准了枪支制造商。不过,事关民众健康和公共安全的集体起诉大案难得遇到,律师们还得多开动脑筋,加州最近热闹的是250000个男人告一家健身俱乐部,因为它在场馆保留了女性专用的活动场地,有“性别歧视”的嫌疑。
目标锁定,律师就该忙了。潜在受害者上的必须是同一条船,就是说,受了同一种害,索要同样的赔偿。像卡普兰告美国在线就比较简单,某一类型的用户及其经历很容易表述,但有时法官会要求提供几十位几百位潜在受害者的诉状,反微软垄断案的诉状就是119份几乎一模一样的证词,这样律师就得拼命发电子邮件联络受害者,或者登个广告:谁损害了谁的什么权利,被损害的如不明确表示反对,就是默许我以你的名义告它了。
然后就是时间和金钱的先期投资,律师们要搜集材料,访问专家,说服法官,没日没夜的工作去对抗有钱有势的对手,他们很可能一败涂地。但是如果有点把握,法庭较量之前不妨先给对手点厉害尝尝,斯克鲁格斯曾在华尔街简要介绍自己的战略,一次演讲让烟草公司股票跌了20%。最后的胜利就意味着赔偿费的20%~25%、甚至40%归律师所有。如果不是米歇尔·霍斯菲尔德第二(他告倒了瑞士银行,让它们吐出二战遇难犹太人的存款,还告倒了二战期间使用非法劳工的德国企业,但他应得的律师费分文不取,全捐给慈善机构),这位诉讼英雄就真的发了。除了败诉的大公司暗地里把英雄骂作讼棍,烟草公司背上了巨额赔偿费,香烟可能会涨价,烟民肯定不满意,对律师一贯爱恨交织的美国人对集体起诉应该不会有特别的情绪。大公司在华盛顿拥有院外空间,国会迟迟不批限制烟草和枪支制造商的法案,地方法庭的赔偿判决就是另一种形式的限制,其中包含的不过是司法和立法权力制衡的传统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