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悍然鼓掌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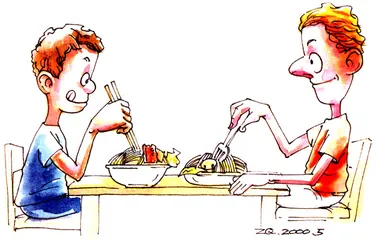
出席音乐会是一件愉快的事,出席一场古典音乐会,更是一件愉快又体面的事。不过,那不愉快又不体面的事,偏偏就最容易在这种场合发生。
有关的报道总是不绝于耳,来来去去也总是一个老问题:失礼的听众和生气的音乐家。去年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发生的一起,差不多集中了中国听众的所有劣迹。据报道,当时美国“朱丽亚四重奏团”正在演奏巴托克《第四弦乐四重奏》,听众们不是在乐章之间鼓掌,就是任意调换位子,上半场演出只进行了一半,“完全不理解艺术家返场小休的惯例,误以为是中场休息,纷纷自动解散,使演奏人为中断。艺术家被发生的事惊呆了,大提琴手在台上发出阵阵冷笑,”继而欲“愤怒罢演”。
迟到早退以及滥用移动通讯器材,是一切缺乏公德心者在公众场合的通病,神憎鬼厌。至于音乐厅一切不愉快事件的要害,集中在听众于不适当的时候做出了不适当的行为或反应,如前述对于“惯例”的“完全不理解”以及常见的“在不应该鼓掌的时候悍然鼓掌”。不过,懂不懂规矩是一回事,要到哪里去学习这些规矩,却又是另一回事。这毕竟不具备“饭前便后要洗手”、“见了长辈要请安”那样的普遍性。上海音乐厅和上海大剧院公布的“进剧场观众须知”,也只有如下七条:
1.关掉随身携带的手机,呼机调整到震动档;2.不吃带有声响的食物或翻动塑料袋、开启易拉罐;3.迟到者幕间进场;4.因故退场要轻扶座拉,以免发出声响;5.未经许可不得摄影摄像,特别不能用闪光灯;6.少儿入场须有家长看管,不得随意走动。婴幼儿谢绝入场;7.禁止在场内吸烟。
除了暗示可以进食“不带有声响的食物”之外,无一字提到鼓掌和退场的程序。谁来对听众们做出事先的指导?反正乐于做批评报道的报纸是不会的,现场的报道者,大概也只能依据台上演奏者的脸色来做出正误的判断。但是,音乐家嫌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部分中国的听众,还嫌交响乐闹得慌呢。“文革”初期,上海的革命群众就曾批判贺绿汀他们净搞那“交关响的音乐”。就古典音乐而言,教堂和宫廷里的繁文缛节,绝不比其他任何地方少,而现在被尊奉为里程碑式人物的古典大师,都有把音乐从上述地点解放出来的事迹。
每一个行业,尤其是其中的技术工种,多少都有自我保护同时自动生成沙文主义的机制。写作的、打网球的,都和音乐家一样,对安静有很高的要求。其实,真正需要肃静的,倒是人命关天的行业,例如正在手术室操刀的外科大夫及其同僚,可这些人偏偏就最无所谓。去年,香港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向医院管理局投诉说,某外科大夫一手拿刀一手持大哥大,一面摘他的盲肠一面讨论一辆私家车的出让,此举令他的患处至今仍感到不适。此言既出,社会上附合者甚众,我老婆就骄傲地对我说,盲肠算什么,她生孩子的时候,医生护士嘱咐她“自己用力”之后,就坐到一边用力聊天去了。后来,“朱丽亚”转道上海演出,对当地听众的临场表现称许有加.,甚至返过来表示,在乐章之间,也可以有一点掌声。这种说法在令上海的演出组织者感到欣慰之余,亦怀疑上海听众是否给音乐家留下了“过于循规蹈矩”的不良印象。有报道说,很多上海人知道如何避免自己因无知而成为众矢之的,不过要满足朱丽亚四重奏小组那种额外的要求,在不该鼓掌的时候鼓掌,已超出常识的范围。
常识告诉我:在家里听唱片比较稳妥,你可以在躺在床上听,可以坐在抽水马桶上听,爱鼓掌就鼓掌,想什么时候鼓掌就什么时候鼓掌,高兴了甚至还可以像看京戏那样叫一声好。说到京戏,我终于想起了一个令人愉快的老段子:老外看京戏,听到满场叫“好”,也跟着叫,但是他的发音听起来就像是“How”,像是对“好”的质疑:“怎么就好了?好在哪儿?”偏偏台上的那位老板懂点英语,心里很不爽,遂复翻筋斗一串,台下复“好!”洋人复“How?”如是者往来数回之后,该夷终为同胞们合力逐出场外。
值得安慰的还有:幸好并不是所有的严肃音乐家都那么严肃,幸好世界上的音乐家多少都还有点人来疯。再来一个老段子:某美声,惯于演唱时故意拉长尾音,博得热烈掌声之后方肯告一段落。一日正在炫耀,忽然从前排站起一名观众,背对舞台向全场喊话:“都别鼓掌,憋死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