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亚特兰蒂斯》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刘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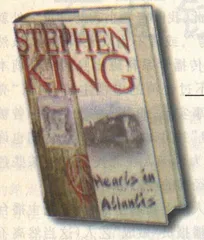
犹如往年一样,临近感恩节和圣诞节,美国的出版界又迫不及待地推出了大批新作。仅本期的上榜新书,就有七部之多,而且内容也丰富多彩,不只由警匪故事垄断一切。
不出我们所料,哈里·波特的故事,以新出的第三集《哈里·波特和阿兹卡班的囚徒》为新卖点,连带着前两集继续占据着《时报书评》畅销书榜的三甲。奇怪的是《出版家周刊》的书榜上竟不见哈里系列的书名。这恐怕是各自侧重点和统计渠道的差异吧。
在上榜新书中,最有深度的大概要首推斯蒂芬·金的《心在亚特兰蒂斯》了。在美国文学作品中,有关越战的主题在近20余年来是屡写不衰,诚如我们写“文革”那场灾难的“伤痕文学”,大概是给人们的刺激太深,似乎只要稍稍挖掘,总会写出些震撼人心的故事。斯蒂芬·金本以写惊险故事著称,此番涉猎这一梦魇般的题材,自有其一番创意。
首先来看书名,“亚特兰蒂斯”本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作品中所描写的一处神秘的陆地,位于赫拉克勒斯之墩(指直布罗陀海峡东端两岸的两个岬角,相传由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所置)以西,那里本有高度文明,后为火山和地震所毁,沉于海中。后来许多人为这一传说所惑,多次设法找出其所在。“大西洋”一名即由此而来。作者用了这一传说中的神秘岛作为书名,大有深意。
这部作品由两个中篇、两个短篇和一个匆匆的结尾构成,本身就很别致。
第一个中篇小说题为《穿黄外衣的矮个子们》(Low Men in Yellow Coats),讲的是仍具有50年代特色的1960年的故事。11岁的鲍比·加菲尔德和他吝啬的寡母住在康涅狄格州一处美丽的郊区。他家的楼上新搬来一位奇怪的房客,叫泰德。鲍比被这位新的成年朋友迷住了,他母亲则担心这位房客会“触动”她儿子。事情若是如此简单就好了。但泰德却认为自己着了魔,只是说不出中了谁的魔法。于是,他雇下小鲍比,要他留心丢失宠物的通告、刮跑的风筝、用粉笔画在“跳房子”格旁边的星星和月亮,以及贴倒的超市布告——总之,是泰德认定他那位神秘的迫害者的种种征候。……到故事过半之后,作者的笔锋一转,把儿童对平常事物的畏惧感变成了鲍比的自我发现:原来他并非自己原先认为的那种人,他并不是自己生活中的英雄。他没找到勇气的源泉,也就没有走历险之路。这样的结局不是作者所惯用的,或许使许多读者感到失望,但胆怯的孩子终于成了懦夫,其寓意颇值深思。
作品的第二部中篇与书名一致,就叫《心在亚特兰蒂斯》,可见这是全书的核心。在这部中篇小说中,作家写了另一个明智而非英勇的故事。1966年,在越作战的美国青年正受着战争的折磨,而缅因大学一年级学生皮特·莱利却迷恋于纸牌戏。这个人物实际是第一部中篇的主人公鲍比的继续,虽然他们未同时出场,却爱恋着同一个女孩子,而且泰德给鲍比的那本书《苍蝇爵爷》最终也落到了皮特手中。按照那种纸牌戏的玩法,谁用不幸的13点得到了黑桃王后,就会被压得透不过气(有点像我们玩的“拱猪”)。
皮特的母亲担心儿子玩物丧志,告诫他:“你得努力学习,不用功的男孩子会萎靡不振的。”但皮特对此置若罔闻,一心只想打牌。他宁肯对学业掉以轻心,也要赢牌。他的主要对手是个其貌不扬、身材矮小、心胸狭窄的人,叫作罗尼·马朗方特(其姓有“坏孩子”之义)。皮特就是想让他“笑不起来”。
校园中人人都揣着这样那样的黑桃王后,这些牌迷们彼此公开敌视,其实个个所怕的都是投入越战。不过,这些不重学业的学生为某种力量驱使,投入了反战活动。抗议运动的领袖叫斯托克利·琼斯第三,是一位拄拐的“新英格兰的希思克利夫”(《呼啸山庄》中的男主人公)。他嫉妒同伴们的健康和愉快,而且如同生物的尸体一样,由于腐朽而发臭:“唯一与之相似的气味只有吃力地跑了长途的电气机车变压器。”是斯托克利的几乎自杀,才激起全校园一致团结抗议越战。皮特的女友卡萝尔·格博后来参加了一个类似“气象地下组织”(由“气象员”派建立的激进组织,名称来自一句歌词“你不需要气象员才能知道风向哪里吹”)的激进派,协助枪杀了6名面试在一家化工厂谋职的学生。卡萝尔虽然有罪,仍保持着圣结形象;而斯托克利求死的愿望则在叙述者的忆旧中不朽。作者没有写出皮特挽救自己的决定,除去花费数年于政治抗议之外,还可能付出什么代价,不过书中确实有人上吊了。
总之,第二部中篇和第一部一样,主人公都没有成为由恐惧而挺身冒险的人物。但在两部短篇中,却出现了这样的主人公: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老兵约翰·苏利文和威利·谢尔曼。他们为战争的梦魇所笼罩:苏利文总觉得一位被害的越南妇女携枪与他同乘“雪佛莱”汽车;每周有五六天要乘火车去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在那里扮演一个瞎了眼的越战老兵。“看似假的不一定真是假的。”
除去故事内容多有象征含义,结构与写法颇有新意之外,越战的主题引起众多读者的共鸣,大概是该书畅销的主要原因。
这个女人!
(刘芳)
法国女影星碧姬·巴铎最近出版了自传第二部,她的名气实在太大,书的销售量不可能不好,但是书评界对她的写作怎么也不敢恭维。
《解放报》说:“掂掂这700多页的长方形吧,打开来,看里面一个接一个的惊叹号和问号,一串串形容词乘以形容词的描述,作者似乎要表达一种阴沉执拗的痛苦,可她根本写不出来,她恨不能让纸上所有的文字直接喊给别人听。真难理解居然有50万人声称读过这样一个作者写的上一本书。
“如果你有耐心字字细读,碧姬·巴铎会毫不隐晦地告诉你一些丑闻,关于前总统怎样摸她的屁股,关于极右分子怎样赢得她的青睐,但是不要停留于此,让我们看看她的叙述特色,恐怕只能以每段文字都有脏话来概括。脏得让人头晕,让人心生厌恶和怜悯。如果你追求情节,你会读到这个男人俘获她然后被她抛弃,那个男人被她俘获然后抛弃她,还有一些男人被她俘获被她抛弃,另外的男人俘获她抛弃她。这个女人值得同情吗?如果你说她疯了,那你结论下得太早。瞧出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虚伪了吗?她的宠物死了比她本人打胎更让她伤心。瞧出种族主义者的潜台词了吗?她居然说‘阿拉伯人真可怕,他们的长袍和头巾、他们发暗的肤色和深陷的眼窝,我一看见就难受’……”
《巴黎竞赛画报》以一贯的名人吹捧对待法国人心目中“永远的玛丽亚娜”,为她的访谈和传记大肆泼墨。《解放报》的知识分子虽然百般嘲讽,他们真正挑剔的是非理性,刻薄的书评原文是这样结尾的:“她自封为玛丽莲·梦露,可她错得太多了,绝无重生的可能。不要笑,要理解她。谁叫她曾是明星,而且现在也不过65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