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江湖》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卞智洪)

远大歌舞团的“全家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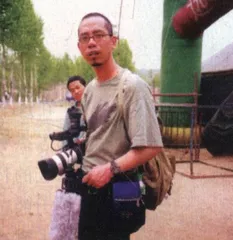
吴文光在“江湖”上
1988年,吴文光把自己关在昆明某单位的剪辑房里,用三天三夜来剪辑他采访几位艺术家的录像素材。他脑子里并没有关于纪录片的任何概念,他只是想做到真实、客观。但那部名为《流浪北京》的录像片为中国的纪录片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去年8月,当吴文光决定拍摄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流动歌舞团时,他脑中仍然没有关于纪录片的概念。他只是放弃了以前所用的采访形式,放弃了若干人的摄制组形式,和助手苏明二人轮流用数码摄像机和录音机跟随纪录这个歌舞团的生活。近一年时间里,他们断断续续地随团到了北京郊区、山西、河北等地。尽管这种拍摄到目前仍不能算终止,但吴还是先从70个小时的录像素材中剪出了一部完整的纪录片:《江湖》。
如果说《流浪北京》中的喋喋不休多少让人联想起80年代那个“口水时代”,那么《江湖》真的使人感到现在是一个“肉搏”的时代。通过《江湖》,你能看到那手脚、那身体的撞击。远大歌舞团每到一地,先要和当地的派出所、文化站,有时还有工商、卫生部门打交道,要租场地,做宣传,演出及维护秩序,然后搬家,一切再来过。而他们内部也始终充满了矛盾。想家的女孩哭了,某人撬了某人的箱子,老婆拿着刀要砍丈夫,家乡的计划生育又紧了,这时“跑外交”的小伙子在帐篷外打手机:“卫生大检查过去了没有?我是歌舞团的呀。11号以后?什么?‘十一’以后?那我们现在可以去了吧。现在去了全给没收了?”后来,老板的一个朋友洪哥来到大棚,吃喝、交心、撒酒疯,几天后拐了他们的一个人不辞而别。队伍继续前行。
但这的确是一个歌舞团,这里充满了歌声,从《祈祷》、《囚歌》直到《忘情水》与《心太软》,还有崔健的《一无所有》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他们是“花城伤感歌王”,是“广东甜歌小妹”,是“东北歌王”与“北京摇滚巨星”(以上均是歌舞团的招贴用语),他们的舞台表演则更是粗糙而生动。去年风靡国内的《好汉歌》,几乎成了远大歌舞团的“团歌”,他们到处走,到处唱,正是“说走咱就走”,“风风火火闯九州”。《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同样在片中反复出现,但令人心动的是,这些“歌星、舞王”并没有看过那部影片。他们只知道它很火,他们从市场上买了它的中国版歌曲带——毛宁的《我心依旧》,现学现卖,开始在祖国广褒的土地上,在他们的每一场演出中,深情地演唱。
吴文光更愿意把他的工作称为一项田野调查,而不是一部纯粹的纪录片。他原只是想拍摄一种流行文化现象,但他发现这些流行文化是一些人的精神食粮。片中小谭宁愿在团里做杂工,10个月拿了300元钱,也不愿在建筑工地一个月拿600元。他跪下来请求收留,也许是为了歌舞团能游走四方,也许是为了在遇到大棚之外的女孩时,可以上前搭讪道:“你喜欢文艺吗?我是歌舞团的。”
几年前,吴文光的拍摄队伍曾一度扩大化,从一个人到三个人到更多。但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纪录片作者常会在心理上与故事片攀比,用什么机器拍摄?什么题材好啊?好看不好看啊?长度多少?“当你开始在意这些,开始精心设计时,你同时失去了你最想做的东西。”他几个月前曾看到一张纪录片工作照,一个老太太在写字,周围是导演、摄影等一共4个人,是摄影机和录音话筒“那些枪”在指着她。“你说这怎么可能真实呢?虽然说只要拿起摄影机就无法做到真正的客观,但我们毕竟不能一步错,就有理由步步错啊。”
因此,吴文光尽可能削弱摄像机对生活的干扰。而这也恰恰产生了《江湖》最感人的细节。比如:几个人围在一起哭穷,数点着身上最后几块钱,说还可以买斤猪肉;接下来是一阵让人尴尬的沉默,然后,一个女孩突然说道:“你放屁了?真臭!”为了适应所谓“观赏习惯”,吴文光曾把片子删到一个半小时,但他发现这时他失去的就不仅是“观赏性”了。
对吴文光来说,他的生活和工作是同步进行的。他与大棚人吃喝拉撒睡玩混在一起,而他偶尔会买几斤肉,给他们做上一顿饭。他努力平衡着自己作为同伴与独立工作者的两种身份。但有时被拍摄者不行。片中那位洪哥在与哥们儿说了一大堆醉话之后,突然对着画外(捧着摄像机的吴)问,“你……你说我干什么好?”
这些东西可能打动我们,也可能我们无动于衷。但它们,包括制作它们的漫长过程,都令吴文光心醉神迷。1997年后,价格变得极便宜的微型数码摄像机与数码剪辑软件,成了他的纸和笔。他如此热爱这种只听命于自己的“写作方式”,如此热爱那些并不完美,但充满颗粒感、充满新鲜的(或者是“肉搏的”)生活气息的影像。他说:“我不是拍别人的生活给你看,我首先觉得那生活是属于我的。我希望它也属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