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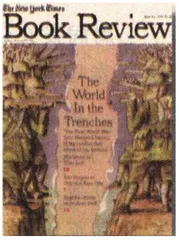
本期上榜的作品,无论新旧,多与健康有关,从中可看出今夏美国读者的兴趣所在。对我们来说,最值得介绍的当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书。
作者约翰·基根是一位军事史学家,或许是目前西方最出色的一位。这部体现了他多方努力的一战史,资料翔实,叙述清晰,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首先来看看数字。美国参战仅19个月,却损失了11.4万人(是越南战争中死者的两倍),但二战中牺牲为29.2万人,而南北战争的阵亡人数要超过60万人。英军在二战中牺牲的军人与美军相当,为26.5万人,一战的伤亡人数为42万人。法国伤亡军人19.5万,德国为60万(西线)。东部战场一向不为西方人重视,其数字更加惊人,除俄国军队损失与法国相仿外,塞尔维亚15%的人口在一战中被杀,而土耳其根本没有统计数字,据估计也会有几十万人死于战火。
书中记叙了最为惨烈的几次战斗。1916年夏,在法国北部阿拉斯城南20英里处索姆河谷的梯耶普瓦尔村一役中,英军即损失7万人。索姆河战斗是西线的十余次主要战斗之一,仅在1916年7月1日开始的首次战斗的24小时之内,英军就伤4万、死2万;而在一年后的依普里斯(或称帕斯陈代尔,比利时一村庄)的战斗中,英军的伤亡人数分别为17万和7万。作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军事史上损失人数最大的战争”,“索姆河一战标志英国生活中生机勃勃的乐观主义世纪的结束,从此便一蹶不振”。
然而,英国毕竟在境外作战,其平民死亡人数仅有2000人。德国人则死亡约200万。至于充当一战主战场的法国,死于战争者估计为170万。1918年战争结束后,法国有战争造成的寡妇63万人,还有数以万计的单身女人再没结婚,60年代末还可见到这些老妇,在公共场所做清洁工,在地铁中剪票。
要把这样的战争经历及其对本世纪的意义传达给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并非易事;但作者那种有纵观、有细节的叙述还是尽其所能的。对战争如何开始,如何进行,协约国如何获胜,也讲得有头有尾,而且插进许多感受。
对于人们费解之处,如:这样不得要领的大战怎么会发生呢?这样毫无用途的大屠杀怎么会持续这么久呢?在如此无法形容的条件下人们怎么会继续投身战斗呢?等等,作者并没有回避,而是用当代人可以理解的词语作出了回答。他认为,战争由一系列偶然事故和决定而引发,根本没有考虑后果,包括德国主战将领们也没想到会出现世界大战的局面并延续多年。如此看来,他们既无意发动一场大战,也就不必负责了。至于参战的士兵,职业军人则别无选择,而应征入伍者也莫名其妙。所以到后来,厌战情绪普遍滋生,拒不服从命令的事件屡有发生。1917年夏,法国有49个师只肯固守索姆河沿线,拒绝出击。战争已难再打下去了。
作者在解释伤亡惨重时,理由较他人有说服力,他认为这仍是一场旧式的战争:法国人动员了71.5万匹马,奥地利是60万匹,1914年法国骑兵的胸铠和一个世纪前滑铁卢战役时相差无几,海上通讯仍用旗语,陆上则靠传令兵和手势。那场面是英国纳尔逊海军上将(1758~1805)和惠灵顿将军(1769~1852)都看得懂的。炮兵不知是否命中目标,冲上去的步兵也无法通知炮兵该向哪里瞄准和何时开炮。简言之,将领们在指挥中有屠杀和毁坏的技能,却不知如何有效地用于进攻。以前炮火威力不大时,他们可以亲临战场直接看到部下的进展,后来也可以靠无线和有线通讯设备与前方沟通,但一战却是这当中的空白。理解不等于原谅,作者对指挥官们的无能颇多嘲讽,对他们草菅士兵的性命大加谴责。
在该书的最后部分,作者也没忽略一战对欧洲各国人民心理上投下的暗影。但连批评家也指出,对战争的起因分析不够深刻。作者诚然是站在英美的角度来看待那场大战的,他不可能抓住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列强中新崛起的德国要求在全世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这一根本动机,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对各国的影响这一系列基本因素,因此,全书的价值也只在参考了。
另一部虽未上榜,却是写二战中英国谍报中密码史实的书叫《在丝织品和氰化物之间》(Between Silk and Cyanide),作者为利奥·马科斯(Leo Marks)。他是伦敦一家旧书店(曾被海伦·汉夫写进《84年,切灵十字路》一诗中而著称)创办人之子;8岁时,早熟的利奥就破译了书店中的价格密码,就此奠定了其生活道路。1942年,22岁的他被英国高级秘密机构“特别行动执行处”(S.0.E.)征召,负责为谍报人员设计密码。50多年之后的今天,他才不再保持缄默。
英国军事情报机构原来只有五处与六处,分别负责战时国内外的反谍和间谍工作,后来随战争需要而发展,才有了S.O.E.。该处所用密码原先采用莎士比亚、济慈和吉卜林的诗,结果不断被熟悉英国文学的德国人所破译,利奥的任务便是编制新密码。当时派到欧洲大陆的英国间谍的该密码记在一块丝织物上,遇事一烧即可,另一种随身携带物是氰化物,准备不得已时自杀,故有此书名。作者是位爱国者,在书中揭示了迄今鲜为人知的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及英国战时机构的内幕,从资料和趣味角度都颇值一读。
偏爱巴尔扎克的理由
巴尔扎克诞生200周年之际,迦里玛出版社新近出版了哲学家阿兰对他充满敬意的评论。警惕当权者,仇恨重要人物,蔑视教会势力,唤醒理性良知,在阿兰眼中,小说家巴尔扎克和司汤达一样,都有激进哲学家的一面。
但是,司汤达写作随兴所至,临场发挥,巴尔扎克则小心翼翼,落笔沉重;司汤达让孤独的主人公生机勃勃,展现自己,巴尔扎克则把他们闷在千层油酥一样的社会秩序中无法挣脱;面对教会压抑,司汤达愤怒暴躁,巴尔扎克则平静思索,就当那是再自然不过却迟早要被取代的必需品;司汤达喜欢清晨轻快的青年准备向未来走去,巴尔扎克则喜欢夜晚将老之人丈量人生经历的起伏;司汤达从不费心描写,对巴尔扎克来说,外部世界的分量却是无可替代的。
最后一点决定了阿兰偏爱的是巴尔扎克。这位大文豪从不忽视一级台阶、一把坐椅、一盆残花、一束光线,因为它们就像马夹、帽子和领结一样,组成了人物的性格。
阿兰还认为巴尔扎克是真正伟大的哲学家。他会让自己的思想以化身的形式出现——“不写金钱,只写角落里数铜子儿的吝啬鬼;不写政治,只写猫一样诡谲的政客;不写爱情,只写或贫或富、或信任或嫉妒、或不幸或幸福的恋爱中人”。
《新观察家》称,8月假期的旅途上,即便行囊再沉,也要把阿兰的《巴尔扎克》塞进去,因为“它能把读者指向更加美好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