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丹奶奶》到《魂牵梦系的殖民地》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刘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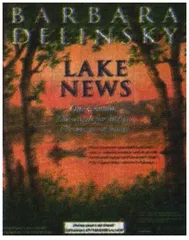
在本期的6部上榜新著中,有3部女作家的作品颇值一读。一是斯蒂尔女士——我们无法不佩服她的高产和题材的广泛,而且确实为读者所欢迎——的《丹奶奶》,虽说难以摆脱由历史和铁幕时期造成的偏见,但终归介绍了异国的风情文化。事实上,美国的犹太裔居民大部来自俄国和东欧(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他们对祖居土地的眷恋和抱憾,构成了该书的主题,也吸引了相应的读者群。二是芭芭拉——杰林斯基的《湖泊新闻》,写一个出名歌手为逃避谣言的中伤,从城市跑往给她留下美好记忆的故乡。逃避一向是文学作品中男性主人公的一种倾向,如今已蔓延到职业妇女身上,但该书的“逃避”更带有“回归”的意味,后工业化时期,从城市向乡村的倒流,反映了人们对都市文化的厌倦和对大自然的向往。现代化的交通和信息手段为这种城乡双向选择提供了方便。但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有这样的理想中的田园净土吗?
其三便是米琳达·黑尼斯的《珍珠之母》,这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故事的背景的50年代的南方小镇:密西西比州南部的佩特尔(Petal)。这是个地图上有的真实地名,当然,在作家笔下只是用于烘托的艺术环境。在那个时代的那种地方,没有电视,书中为我们展开的是一幅普通生活的日场戏:一名受跛足之苦的妇女正在生儿子,而孩子的父亲隐瞒着身份,只是出钱来作养育费。一对十几岁的少年男女早恋,结果却是单亲相同的兄妹,女孩怀了孕,死于分娩,一个黑种男人负起了养育那婴儿的责任。一个搞同性恋的女人,其兄弟是个教士;一位脾气古怪的女士爱上了一个殡仪馆的人。一个有一半“印吉(第)安”血统的人住到河边,专门给人算卦画符……总之,那里是个如同乱麻一般纠缠不清的地方。
黑尼斯女士在众多的人物及他们的故事中主要讲了3个人: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孩,按照一块地产的招牌取名为“值钱的柯尔诺”(Valuable Korner);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孤儿,按照一条路取名为“平坦的斜坡”(Even Grade);一个虽随父取名,但尚不知其父为谁的男孩,叫作乔列勃·格林(Joleb Green)。
女作家不只是在写50年代的南方小镇的生活,而且就像是她身处彼时彼地,所写的就是她周围的事情。我们虽不甚清楚她的年龄和经历,但确知她并非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就是说,她不像威廉·福克纳那样写自己耳闻目睹的故乡小镇的沧桑及人物在历史重负下面对现实的困惑时的种种心态,却依然能够写出一幅50年代美国南方小镇的生动图画,实属难能可贵,真可以与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1909~?)、卡尔森·史密斯·麦卡勒斯(Carson Smith McCullers,1917~1967)、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 Connor,1925~1964)这些著名南方女作家相比了。
作者在描写十余岁孩子的强烈和疏远情感方面尤其出色。如前边提到的那对单亲血缘兄妹,“值钱”14岁,杰克逊15岁。他们稚气地琢磨着他们父母:“值钱”觉得“她母亲寡居的阴郁憔悴使她那张心形的面孔像个炒菜锅”,而杰克逊则注意到“他爹的吊裤带挂在双肩上而不是缠在腰间……这里边有点学问”。乔列勃也是15岁,则在追求宗教上的净化:“5次卫理公会教徒,9次是浸礼会、卫理公会和新教结合的教徒。”但他们都渴望长大成人,愿意现在就有成人的自由和作派。从这方面讲,这又是一部写青少年的小说。
总之,米琳达·黑尼斯以南方蔓生的植物那样丰富的语言展示了在美国南方特有的温暖风光中,男女老少各色人等的画廊,并通过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身世之谜,既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线索,又揭示了黑人、白人、印第安人、犹太人间的深刻的社会内涵。尽管有评家认为作者重人物刻画而忽略严密的结构,但无论是谁都承认这部作品是写50年代南方小镇生活的绝响之作。
与该书相对的,是一部写加拿大纽芬兰的冰天雪地的小说。近来已有两部回忆性的作品写那个人烟稀少的北国故事:安妮·普鲁克斯的《船讯》(Annie Proulx:The Shipping News)的霍华德·诺曼的《鸟类艺术家》(Howgrd Norman:The Bird Artist),引起文学界的注意(前者我国已有作家出版社的马爱农的译本)。由于人们对那遥远的北方很不熟悉,因此,那广袤的荒漠就更具神秘性,引人遐想。
韦因·约翰斯顿(Wayne Johnston)的《魂牵梦系的殖民地》(The Colony of Unrequited Dreams)为写纽芬兰的作品添上了一颗新星。这位当地出生的作家(如今住在多伦多),深知这样题材的难度,尽管写本乡本土的故事,仍然在发表了四部小说之后,方才谨慎提笔。
首先在处理题材上就别开生面,当二战后全世界席卷着民族独立风暴时,本书的高潮却是1949年4月1日愚人节那天纽芬兰并入加拿大的情节。其主人公便是后来成为该省首任省长的乔·斯莫伍德(Joe Smallwood)这位力主联合的领袖。
一望无际的冰天雪地,一位平凡普通的主人公(他本人是建筑师),一番似乎是逆潮流而动的政治活动,本身便像是北方的魔幻现实主义(崛起与兴旺于拉丁美洲)。于冰冷中显热情,于平淡中显神奇,这就是该书的独到之处,也必然是吸引读者的入胜之处。
海明威的短篇
(刘芳)
今年7月21日是海明威诞辰100周年,伽利马出版社近期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全集共4册,海明威的写作风格与私人生活又一次成为美欧书界热点。
海明威一生写了78个短篇。与他同时代的福克纳写了76个,菲茨杰拉尔德写了160多个。但是菲茨杰拉尔德在文学史上留名更多的是长篇,写短篇对他来说只是挣外快,而福克纳干脆把自己的短篇小说叫作“副业”,只有海明威,将他卓越才华中最卓越的部分奉献给了短篇小说的创作。
其实,也许正是因为明白自己其他方面的不足,海明威才将精确措辞和使用短句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他只使用土生土长的英语,避免一切拉丁词源的字眼,他创造的对话全是单音节词,读起来跳跃感非常强。《快报》周刊评价法文版海明威集时,不无遗憾地提到了翻译的无奈:一位文学教授向他的学生介绍海明威笔下某人物点早餐那一段写得如何如何好,他的法国学生说,“不就是点了鸡蛋和火腿吗?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呀。”
有人说海明威是“行为主义作家”,因为他只让自己描写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辞,绝少直接以他们的心理示人。这种风格对其他作家很有影响。加缪的《局外人》出版时,就有评论家称之为“海明威写的卡夫卡”。
海明威爱写的主题超不出父爱陪伴下的童年、战争中的爱情、西班牙的经历以及钓鱼和打猎。但他写出来的作品就像用太旧的线织成的外套,稀薄透明之处反而能让人看到更多的东西——对生命的焦虑、恐惧、绝望和因此更要生活下去的力量。
有评论家说过,好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比现实更真实,你读完以后,会觉得幸福与不幸、善与恶、快乐和痛苦、食物、葡萄酒、床、人物甚至那时的天气都被写出来了,都从此永远地属于你。写过好作品的海明威是在1961年的夏天自杀的,因为他发现自己再也写不出比生活更真实的作品了,所以情愿放弃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