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蝇式的繁衍战争
作者:王星(文 / 王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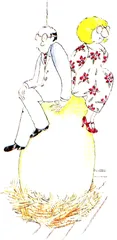
“男性与女性在繁衍后代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这种说法初听起来很难使人信服。按照传统的进化理论,生命的关键意义在于使有机体有机会把自己的基因复制品传递给它的后代。其中有些有机体(例如蟑螂)凭借繁衍尽可能多的后代来实现这一点;而诸如像与人类这样“较高级”的生物的选择是繁衍较少的后代,但给予它们更多的照顾。
毫无疑问,母亲与父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生存下来。在实行所谓“一夫一妻制”的物种里,假如为父的一方有足够的证据确信那是自己的后代,他会与母亲合作共同完成抚养的任务。然而,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物种(例如猩猩,甚或是我们的祖先)中情况却有所不同。举例来说,假如雄性一方意识到有办法使雌性一方尽其最大可能获取食物,从而使他们的后代生长得更强壮、更魁悟,他会不惜以牺牲雌性达到这一目的。许多进化学家相信,这也是人类男女之间所谓“胎盘争论”的根源。当女方怀孕后,胎盘的大小往往会成为夫妻间一个隐秘的争论话题:男方总希望胎盘尽快长大,女方却希望它能保持在一个适当的尺寸范围内;换而言之,男性或其他雄性哺乳动物都向他们未出生的孩子传递了一种基因,这种基因可以促进母亲的胎盘生长并尽一切可能养育胎儿——哪怕这些将以牺牲母亲的健康与她未来的生育能力为代价。
雌性也希望自己的后代生存,但她们不会以自己未来的生存能力为代价。以哺乳动物为例,由于哺乳会抑制雌性的排卵机能,因此她们不会终生哺育自己的后代——即便这样做会大大降低后代的存活机率;如果不这样选择,这些雌性将永远不会再次排卵,因而永远不会再次怀孕,拥有更多的后代。
这种竞争最激烈的范例是果蝇。果蝇从来不会和伴侣白头偕老,相反,它们总在不停地变换伴侣,而且从不会和同一对象交配一次以上。雄性果蝇的精液中含有一种可杀死来自其他雄性果蝇的精子的毒素。当一只雄果蝇和一只不久前刚交配完的雌果蝇交配时,它的精液就能杀死前一果蝇留下的精子。这种为保存自己的后代而进行的“改造工作”很彻底,但不幸的是这种毒素也会损害雌果蝇的健康。不过这对雄果蝇来说算不了什么——反正它们不会见第二次面。
类似的繁衍竞争实际上也发生在人类与其他哺乳动物体内。不同的只是我们拥有的是一种被称为“印迹基因”(Imprint gene)的改造基因基础的武器。“印迹基因”这一概念于1989年首先由哈佛大学进化学家大卫海格提出。这一学说直接威胁到门德尔遗传学说的基础,即基因特征取决于来自父母双方的基因共同构成的基因编码。“印迹基因学说”认为:只有来自父母一方的基因能在后代的基因系统中显现,剩余的一方将被遏制。目前这一领域的绝大多数研究者相信:这类基因只存在几百种,但它们的影响力极大,而这其中又有半数以上与包括胎盘、胎儿乃至新生儿在内的生长过程有关——来自父方的基因鼓励更茁壮、更快速、耗费能量更多的成长,来自母方的基因则努力控制这种过于迅猛的趋势。
研究者们从一些与生育有关的稀有病症中找到了验证这一理论的证据。在这些病症中,来自父方或母方的基因有一方缺失:当父方基因缺失时,受精卵将永远无法进入母亲的子宫内膜,因此胎儿永远没有机会长大;相反,如果母方基因缺失,母亲将因胎盘生长过快、过大而患绒毛膜癌。
从医学上来讲,印迹基因的发现将为治疗一系列涉及肿瘤、不育、胎儿过重或过轻等问题的令人不快的病症铺平道路。但从更“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一事实有些令人难堪:果蝇可以进行精子战并对雌性一方的未来置之不理,人类的行为似乎也不比它们更为文明。进化学家对此给人们提供的安慰是:人类的解剖学或生理学特征都显示出人类不是天生“习惯”于一夫一妻制的生物;换而言之,我们很可能比自己所想象的更像果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