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又是一个物权法
作者:王珲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开始有了法律上的依据
贺蕾终于在5月底移民加拿大。国内事业蒸蒸日上,而加拿大的生活是乏味是宁静难以区别,但贺蕾犹豫再三还是走了。“好像心里踏实。”贺蕾说。她选择了一条中国很多先富起来的“少数人”都走的路:商业移民。
何雄与张思敏早在1992年就进了外企。他们在烙下一身深重的白领习气之外,也攒足了钱,于是一个留守,一个辞职自办公司。像这个阶层里的很多夫妇一样,他们开的公司既小又无生产规模。何雄夫妇告诉记者,政策法令的随意性,使个人资产仿佛面对着一种可被任意剥夺的危险,“所以好多人不敢扩大投资,挣点儿是点儿。”
5月26日《北京青年报》刊载的一份调查证实:在私企老板中表达最集中最强烈的呼声便是“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另据有关数字统计,尽管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467亿美元,流失在境外的个人资产总额也有800亿左右。是否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如何给私有财产以合法的确认,成为几年来呼声高却始终相持不下的焦点。
199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修宪。《宪法》第十一条正式写入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同月,对于市场经济建设极为重要的《合同法》出台,它对于人们利用契约的方式进行合理、合法的自由交易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而更具意义的是,将在今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合同法》,将另一部更为重要的法律提到了立法议程。
1999年5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物权法”研讨会。这一天被法学界人士视作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会上,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梁慧星宣读了由他历时一年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梁教授称,这个由12章445条法规组成的草案其贯彻原则是:凡合法取得的财产,不分公有私有,均予平等对待,一体保护。
物权,一个长期被回避的法律概念
“物权法?到底是个什么?被法学界如此看重的法律,百姓为何对它竟一无所知?5月28日,记者走访了梁慧星的得意门生、物权法研究课题组的年轻学者陈华彬。陈告诉记者:“在民法整个体系中,‘物权法’是涉及到财产的归宿和利用的重要法律制度,它是民法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石。”
“物权是对财产的直接支配权,而所有权便是物权和债权的基础。所有权对于每个公民来说都非常重要,财产就是人格。”在农村长大的陈华彬一直记得,小时候,家里想买一部拖拉机都不敢,还要请示乡政府。“人们的所有权如此有限,这怎么可能鼓励人们去追逐财富呢?我记得1991年北京街头开始有私家车了,媒体大肆报道,这事给我震动很大,因为这在国外天经地义的事,在中国还特别新鲜。”
“20世纪末,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信用经济的时代,信用经济是资本运动的一个形式,借和还的统一,借了钱要还,社会总资本才能运动,在物权法中建立担保法,就是要确保债务和债权的顺利实现,这是确保市场经济有效运行非常重要的基础。”
事实上,对于物权的提法,法学界在共和国成立后便开始了很长时期的沉默。“‘物权法’是与《合同法》并驾齐驱的一个关于财产权和债权概念的法律,人们承认债权,却认为物权是私有制的,与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的本质相拒。”《中国法学》杂志1987年第1期曾发表北京大学民法教研室李志敏、钱明星等人的文章——《论建立我国民法物权体系的必要性及其意义》,成为国内学术界首次公开碰触物权概念的文章。
直到1994年全国人大将物权法列入立法计划,计划经济的阴影仍使许多立法者、学者对物权的观念难以接受。梁慧星的课题组坚持了6年,而这期间许多同道者都因为各种因素而退出了。“物权法是中国建立民法典的一个瓶颈,你可想它的难度之大。”陈华彬说。
美好的设想与困难重重的现实
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是因为西方在1600~1900年间通过建立完善的所有权机制积累了财富,而中国仍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属”、“劫富济贫”的无财产界线的传统中沿袭。当今中国因此而希望通过立法,使所有权的观念——财产的观念深入人心。有了物权法,人们可以隆重地期望很多事情,比如翻开本刊1998年第21期对于房屋拆迁的报道,那里面所有开发商打着征用名义对个人、集体的土地使用权强掠豪夺的行为,都将受到明确的法律裁决,受害的弱小者起码能获得的尊严便是法律要尊重他们的私有财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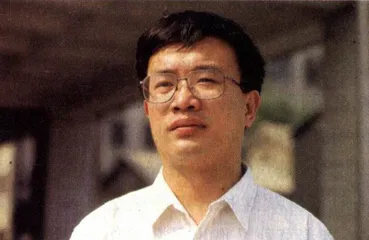
钱明星(上)、陈华斌(下)(娄林伟 摄)

但是正如最初的沉默一样,今天又将物权法的重要性推至无以复加亦是令人可疑的。什么样的物权法将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不弄清这个问题,人们容易过于乐观。陈华彬说:“我们从来没有像西方社会在宪法上就写入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实际上我们要在立法上达到同样的表述,我们强调说所有权受到保护,但也不允许有钱的人利用财产随意损害他人的利益,所以要用法律加以约束,我们在所有权的立法时坚持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协调发展的思想。运用各种手段——国家政策、行政法规、条文对他的行为加以引导和限制,但不能对他的财产加以限制。”而陈表述的这一点正是另一些法学者心存疑虑的。
6月2日记者在北京大学法学楼内见到钱明星博士。他特别指出,中国目前不是自由太多,而是限制太多,“这其实是个如何适应世界法律趋势的问题。西方国家的物权法经过了两个阶段——二战前的近代法律和二战后的现代法律。近代的物权法中观念是以绝对的所有权为核心,对所有权强调的是无限制的支配,法律上很少有限制,而现代的物权法让所有权负有义务。但西方经历了早期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法律就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而我国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的早期,而面临的世界却又是现代化的世界,我们的物权法是借鉴过去还是现在?这是两难的选择。如果过于强调借鉴现代的物权法,就会像小孩戴大人的帽子,是戴不住的。法律与社会本貌严重脱节,可能不会给社会带来进步,反而成为障碍。我们个人的所有权发展还没充分的时候,却要强调对个人财产的限制,那么这种所有权到底会不会在我们的社会孕育出来?对这个问题我个人是表示怀疑的。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不光是物权法,在其他的法律方面都有同样的问题。中国的物权法制定得好不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钱博士坦率地承认,制定一部物权法是需要慎之又慎的事情,“作为立法者,在法律制定中一定要有良好的愿望,这尤其不可少,但他还应该对中国将来的发展有很好的把握,有一种良性预测,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法律,才会对社会的发展起到引导的作用。”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钱博士对目前物权法制定的时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在他看来,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条件不成熟,对物权法的研究也不是很成熟,“十一二年对这么重大的问题的研究是非常非常浅薄的。”
一个并不需要“拾金不昧”的法律所引起的争议
民间的反应不必如法学家们一样高屋建瓴,他们却有着自己的敏感。人们对物权法的注意,缘自3月份报章上的一则消息,拾到小钱收归已有,大钱必须归还失主并可向其索要报偿。这实际上是《物权法》中关于动产所有权的一个非常微小的分支,然而它却引发了人们的疑虑:法律是否有必要对道德领域的事进行规范?
立法者有他们的想法。“民法通则79条第二款把‘拾金不昧’列为法律条文,几乎没有法律效果,假如捡到5分钱也要去寻找失主,对于一个有正常行为能力的人来说,他是不愿意做的。这是立法者立法时没有正确考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对利益的要求,对人的自觉性和能动性估计的太高了。”
陈华彬引用西方一个知名学者的话说:“法律如果不被信仰,便形同虚设。要正确考量人的利益,就得把人放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位置上。价值微小的东西可以归拾得人所有,法律肯定后,既让人良心踏实,又利于财产有效的利用和物尽其用;而价值高的东西,拾得者有义务就近向公安机关或居委会汇报,并登报寻找失主,失主找不到时物品才归拾得者所有,否则失主应向拾得者支付遗失物价值的20%~30%作为报酬。”
陈华彬强调说:“立法者们对这个社会既有的观念加以调整的出发点,是效率至上。”“效率”理所当然成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所认同的东西,然而它潜在的危险可能是什么呢?苦恼的家长纷纷打电话质问社科院法学所,“面对这样的法律规定,该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
作为知名社会学家,李银河一直认为“道德管道德的事,法律管法律的事”,怎奈热心的法学家们却一再把手伸向社会的道德层面,因为他们坚信,“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必须要有其相应的规范,而人们只有在这种规范中,达到有限资源的有效使用,这样的法律机制才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我们无法指责这些法学家们,事实上早在几年前,伫立在北京西单商业街上有40多年历史的“失物招领办公室”就已经不再接待来受教育的孩子们了——连孩子们也不煞有介事地学习“拾金不昧”了。只有在此工作的人们不解地问到,“小东西可以据为己有,这不是占小便宜嘛?时间长了,捡和偷有什么区别呢?”
无庸置疑,法律对人观念的改变有着潜移默化的力量,正是这一点才值得那些以推进社会进步为己任的法学家们警醒。对法律制度的迷恋,也许会损伤那些法律起不了作用的部分。
什么是物权
物权法(指建议草案)的主要内容
其内容涵盖了民法通则、担保法、商用法、民用航空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所涉及的物权范围,并增添其他重要内容,如:
重构国家征收制度——指国家强制收买自然人和法人财产的使用权,主要是土地使用权时,必须严格限定其公益目的。
建立统一的、与行政管理脱钩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如财产抵押登记,不再由各类行政层层管理,设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机关,且不赋予其行政管理权。
建立基地使用权制度——即当基地使用权期满,其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如何处置?法律规定期满后,基地使用权人有权请求补偿或延长其使用期限。
设立农地使用权——即对农民承包土地在使用权限内可继承或出租,并可以延长其使用期限50年。
建立善意取得制度——为保护交易安全所设,即买了偷来的东西,购买者在不知情下可取得补偿。
确立物权变动与基础关系分离原则——规定,“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合同,自合同合法成立之时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在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时,有过错的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
关于遗失物拾得法:
捡到的东西该归谁?草案中第一章第三节关于“拾得”的规定:拾到东西,应当及时报告,失主“应向拾得人支付相当于遗失物价格20%~30%的报酬。”
拾得者在拾到贵重物品后必须向邻近街道或派出所登记,并在相关范围内登报(登报行为由拾得者实行)寻找失主,3个月内若东西无人认领,其所有权归拾得者所有(中国目前的现行规定,遗失物上交后若查无失主收归国家所有);遗失物失主被找到的情况下,失主必须支付其物品价值的20%~30%给拾得者作为酬谢。除非发生民事纠纷,酬谢金额的多寡由两人在其规定范围内自行商议,拾得者有权放弃酬谢金——拾金不昧。拾得者故意隐匿不报将受到刑事处罚。
(以上资料部分引自《中国青年报》) 陈华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