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一张圆桌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施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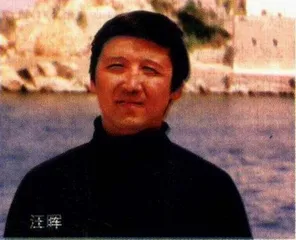
汪晖
问:今年4月是《读书》杂志20年纪念,这本刊物在近年引起很多议论,这种议论与你和黄平接任主编以来刊物讨论的问题和文字风格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你作为主编如何考虑这种变化或调整?
汪晖:《读书》的大多数文章是好读的,这可以从杂志的读者群的扩大和读者的来信看出来。《读书》有变化但也有延续性,它的风格不是从头到尾一样的。原先有许多老的作者,由于年龄、身体的原因写得少了,还有一些作者离开了我们。老一代人中身体好的仍然在写作,例如费孝通、金克木、黄裳等等,我们很感谢他们。老一代受传统文人的教育,他们的长处是对中国文化的修养,文字的能力,能写出那样一种味道。我的同代人中会写文章的人也不少,比如韩少功、葛兆光、陈平原、甘阳、刘小枫、张承志等等,他们至今仍是《读书》的作者。与此同时,新一代学者成长起来的很多。有些在国外受教育的也介入到国内的讨论之中,介绍一些新的知识。他们的优势是他们对新的知识的了解和对当代问题的敏感。《读书》想在这两者之间做一种平衡,一方面是在老作者与新作者之间做点平衡,另一方面在文字风格上倡导活泼一些的、不那么么专业化的写作,但不愿因此牺牲掉新的知识和新的问题。《读书》的风格的变化不是激进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那么,最为主要的是现在《读书》的文章关心的问题确实与过去有了差别。
问:无论如何,《读书》过去是偏向文人化的,现在似乎有些偏向专业问题的谈论,这种调整变化有什么非常确切的理由吗?
汪:与其说是偏向专业问题,不如说是有更多的学者参加了有关各种大家关心的社会问题、知识问题的讨论,他们的文章不是专业论文,而是从自己的研究专业出发,谈论一些一般读者能够理解或感到兴趣的话题。有些话题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感兴趣,但仍有相当数量的读者感兴趣。例如经济学与道德问题的讨论,比如关于金融风暴、初始积累的反思,比如关于婚姻法的讨论,都是专家在写,但大多数读者感兴趣,因为这些问题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果我们拒绝这些讨论,而只要我们的文人趣味、人生智慧啊,那才是精英主义,虽然在形式上可能是传统散文。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问题很重要,但不能单单从文字上看——当然文字是重要的。比如律师的专业,我们不能因为律师知识的专门化就说它是精英主义的。
这样的文章阅读起来可能比文人化的随笔稍难一点,但有些坚持文人化的刊物并没有更多的读者感兴趣,这是为什么呢?70年代到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那个时期面对的问题相对要单纯一些,大家用来谈论这些问题的知识背景也相对单纯一些。80年代末至90年代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的深度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想象和预期。比方市场化过程中的问题,又比如全球化的问题,单纯用文人化的方式来谈论恐怕很难,你不可能总读几本旧书,新的知识领域带来新的问题、概念,甚至谈论方式。《读书》过去基本上是一个文化人和人文学者的天地。可是,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化,使得经济和其他社会问题成为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那么,我们要不要把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其他领域的问题也容纳到《读书》里来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人在变,社会在变,刊物也随之改变。《读书》发表的许多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有不少文章引起了争议,许多过去不看《读书》的人也开始关心《读书》的话题。比如过去经济学界是很少关心《读书》的讨论的,现在经济学家的许多争论就在《读书》上展开。
问:那些专业性背景很强的问题如何进入专业之外的读者的视野,或者说它会不会造成阅读兴趣的减弱和理解的障碍?
汪:某些专业性较强的文章确实可能造成阅读的难度,所以虽然《读书》发表许多专家的文章,但还是希望写得通俗易懂一些。比方我们经常与作者沟通,请求他们尽量写得短一点,文体尽量活泼一点。对于许多作者朋友,我们一直觉得有点抱歉,也是为此。我们希望《读书》成为一座桥梁,一座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之间、不同的知识群体之间、不同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座桥梁,而不是一道由专业知识划出的鸿沟。比如我们组织过考古学的讨论,反映似乎不错。原因是考古学者在这里写文章与他们在专业刊物写文章不一样。但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够用通俗化的语言表达。有些外来语,就是在英语中原先也没有。怎么办?是放弃呢,还是尽可能地向读者作些介绍?如果《读书》完全放弃新的知识,那还是《读书》么?晚清以降,特别是五四以后,出现了许多新名词,有些留下来了,有些淘汰了,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自己不太赞成过多地使用新名词,但我也知道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用熟悉的语言描述的。几年以前,电脑方面的知识有多少人懂啊?大家都用电脑了,有一段时间,朋友们见面就谈电脑。现在大家都懂了。我在担任《读书》主编之前,曾经为《读书》撰写和组织过有关“关键词”的文章,那时《读书》发表的一些文章涉及了一些新的理论和名词,有些作者觉得不那么好懂,所以“关键词”栏目刊出后得到读者的欢迎。我自己做过这样的工作,知道这里面的难度,也体会到作者与读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阅读的难度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加以克服。如果文章提出了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那么,即使语言不是那么通俗,大家还是感兴趣。《读书》发表的有关考古学的讨论,有关当代中国的乡村图景的讨论,关于婚姻法的讨论就是这样。最近一期《读书》发表了一组有关“性别与民族主义”的讨论,很快在邮局就卖完了。读者不仅关心文体,而且也关心问题、信息量和分析的深度。当然,内容和形式都好自然最好,这是我们一直在追求但没有达到的境界。
问:现代社会里知识精英与大众文化有一种脱节的倾向。就一般的印象,读者是把《读书》当作非专业的读物来阅读的,过去那种文人化的品书作为一种趣味也给《读书》赢得了很多读者,现在涉及了专业讨论会不会显得有知识精英的倾向?
汪:首先是《读书》并没有因为讨论我前面提及的那些问题而丧失读者。我是1996年起担任《读书》的编辑工作的,那一年组织过许多讨论和针对某些问题而发的文章。《读书》的订数在那一年中上升了26%。最近两年来,图书市场的情况不是太好,许多刊物的订数下滑,但《读书》的订数始终保持在10万份以上,可以说是比较稳定的。这种情况说明读者既希望得到可读性强的文章,也希望读到有一定水准的讨论。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读书》也免不了面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大众文化呢?怎样才能是大众化呢?这里有形式上的问题,也有取向和内容上的问题。《读书》的宗旨始终是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它的目标之一是通过阅读敏感地发现重要的社会或文化问题,引发各种讨论,而不是像写学术论文那样完满地解决问题。但另一方面,如果《读书》把商业化作为自己的目标,就会彻底丧失掉自己,即使发行100万,那也不是现在的《读书》了。何况一个刊物总有自己的定位和风格,不能要求所有刊物都变成通俗消费品,那样的刊物已经很多了。《读书》杂志在80年代的订数不是很大,但很有影响,这是因为它发表的许多文章提出了重要的、大家关心的问题,推动了知识界和广大读者的思考。《读书》成为知识界和广大读者不断议论的事情,主要还是因为它发表的许多文章触及了许多尖锐的问题,所以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同意还是不同意,大家关心《读书》。
《读书》离不开广大的读者,但也离不开知识界和学术界。如果《读书》变成了文化快餐,知识界的朋友不喜欢,不愿意参与和阅读,《读书》恐怕不可能办好,也不可能提出多么深入的思考。1996年我刚到《读书》时,我们在北大开过一个作者的座谈会,许多朋友这么提醒过我,我至今记得。我们要在学术界和其他领域的读者之间做一点平衡,这里也有一个平衡的问题。我当然希望《读书》的读者越多越好,但我们不会为了商业的目的来办《读书》,这一点《读书》的前辈们大概也会同意的,《读书》的许多读者也是这么看的,他们希望刊物更好看,但不希望《读书》成为一份单纯的文化消费品。以我们这几年的感觉看,不能完全说通俗就好卖,就读者多,这不是绝对的。1996年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不那么通俗的讨论,看起来内容是很专门的问题,但用的是比较简洁的方式把知识界的成果带给普通读者。回头看,读者对这些讨论的兴趣有高有低,主要原因不是专门不专门,而是讨论的水平、问题的价值和表达的清晰与否。这些问题如果不是在《读书》上讨论,而是在专业刊物上,很多读者永远不会看到这些问题。
好读的文字不只一种,如果只容纳一种语言方式,比如文人方式,那也形成一种排斥。现在《读书》的作者中不仅有几代人,而且还有许多海外的作者,其中包括中国留学生、华裔学者、香港和台湾的朋友,甚至外国学者。《读书》还在香港和台湾发行了它的繁体字版。不久前就有一位作者对我说,如果我们过分强调一种语言风格,对别人就不太尊重,在别人的眼里就不平等。其实《读书》的文体从来是多样的,只不过在某一个时期,文体可能偏向某一方向而已。如果只有一种文体,即使再好,大家也会厌倦的。更主要的是,对一些公众关心的问题,仅仅用文人方式说话,或者拒绝别的讨论方式,恐怕不公平,那样就太精英主义了。《读书》在最近几年扩大了讨论问题的范围,涉及大量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问题。例如,1997年,黄平主持《读书》工作时开设了“田野札记”这个栏目,把乡村的普通的生活和习俗带到《读书》的天地中来,现在这个栏目仍然延续着。张承志先生曾经对这个栏目的标题提出过非常值得重视的意见,但就栏目的内容而言,我觉得不是更精英了,其实是更大众了,不那么孤芳自赏了。
问:从哈贝马斯的意义上理解,杂志有形成公共意见、表达民间批评等功能,这几年读者对《读书》也有这方面的批评,你怎么评价《读书》在这方面的作用?
汪:中国需要真正的批评空间,但如果对自己关心的问题还没有探讨清楚,仅仅满足于发几句牢骚,恐怕没有真正的批判力量。我在《读书》的编辑手记中打过一个比喻,说《读书》是一张圆桌,许多不同的人因为有了这张圆桌而了解了相互之间的距离。有不同的意见才是真正的公共空间。公共意见只有在争论中才能形成,任何人的意见也只能是公共空间中的一种意见,最后要由广大的读者和社会来评判。民间的声音是多元的,任何一种声音都不能代表全部的民间。因此,在发表有争议的文章时,我们也会有意识地做一点平衡,力求保持多元并存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衡量一个公共空间的尺度,就是它能否包容少数的声音。我认为《读书》涉及了大量的尖锐的问题,否则它根本不会引发那么多的争论。真正自由的讨论需要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就是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第二就是大家习惯于不同意见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