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允许“权利”!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何西风 赵小帅 劳乐 杜比)
文●何西风 图●王焱
新学期伊始,孩子学校的“社会课”讲授《未成年人保护法》。那天放学,不到10岁的孩子拿着老师发的“保护法”讲义,进门就像土改时的翻身老农民一样瞪着眼对我说:好啊你,爸爸!骗了我那么多年!你不是说我不到18岁就“不算人”吗?
如是两天,我和孩子的妈切实感受到了这《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威胁,它简直就是反家长,要不然就是社会课老师在挑拨孩子和家长的关系。然而这是误解。以后几天孩子告诉我们,老师在课上还教了他们许多别的自我保护方法:比如不到12岁不要单独骑自行车上路,在街上不要随便与生人说话,应当督促父母为子女购买各种保险,购买小吃时不要亮出大票子……等等,总之,内容是挺全面的。
这一天我去旁听孩子班上的观摩课,放学走到校门口恰好看见一个男孩正仰着脸与一位女教师眼对眼、鼻尖对鼻尖地对视着,孩子的眼神是惊恐的、无奈的,而那教师则是严厉的、甚至有几分凶恶的——待了一会儿,孩子的眼珠儿向左一动,老师便啪地拍在他左颊并厉声说:精神集中!一会儿又拍在他右颊说:你又走神了!原来这教师在向一旁的孩子他妈传授让孩子精神集中的方法。
事后我半开玩笑地问儿子,这算不算侵害未成年人权利?你怎么不报警呢?儿子见怪不怪地说:这算什么?上回我们数学老师看到某某上课看词典,就把词典从三楼窗户扔下去!又一回老师还把某某的彩笔扔到楼下去了,那一盒彩笔可是400多块钱呢!我问:你们在社会课上有没有讨论过教师这种行为是否正当呢?社会课老师有没有告诉过你们学生在学校内应当享有什么权利呢?没有,孩子黯然地摇摇头,然后说:老师不可能告诉这些东西!
其实我早就知道,如今多数学校只会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却决不会告诉他们有哪些“说不”的权利。否则教师还怎么能用浩如烟海的作业来淹没学生呢?他们还怎么能动辄给孩子排出好、中、差的座次呢?让人觉得十分残酷的中考和高考制度还怎么可能延续至今呢?
学校成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治外飞地,这透露了我们现行教育的一种实况:它太关心分数,不大在乎人格!它通过师道尊严让孩子们领略了太多“权力”的含义,却从不告诉孩子,还有一个与“权力”同音不同义的词,那就是“权利”。
由此我想到老马克思讲过的一件事:19世纪中叶,一位老板面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自由观念,坦然地在他的车间门口贴出一张告示:这里不允许“自由”!如今我们的学校似乎也可贴出类似的告示:这里不允许“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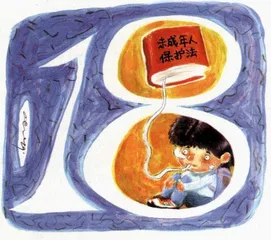
文化斗争
●赵小帅
3月26日,星期五,“All-4-One”演唱组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歌,上座率有七成以上,我去听了,他们的歌我只知道两首,一首叫《I can love you like that》,另一首叫《I swear》,通过这两首歌,我判断这个演唱组就是个“小虎队”的意思。现场演出的气氛不错,演唱会历时90分钟,散场之后,大家蜂拥至附近的酒吧街,喝酒。
近几年有一个流行的英文词,叫Happy Weekend,就我的理解,意思是周末三日要痛痛快快玩一把。
3月27日晚,玩的机会又出现。北京的摇滚乐队“唐朝”在一家快餐厅办演唱会。可惜我累了,没去。
3月28日晚,又是一个演唱会,崔健的“时代的晚上”,地点是一个叫“艺术家俱乐部”的地方,面积不大,容纳一两百个观众。崔健唱了两个小时,在唱《混子》一歌时,崔健先说了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写一个年轻人,改革开放后进了一家公司挣了点钱,别人问他过得怎么样,他说“好”怕别人嫉妒,说“不好”怕别人看不起,就说“凑合”。讲到这儿,崔健向观众发问“你们过得怎么样?”观众们齐声回答:“凑合。”崔健问:“除了这个你们还能说什么呢?”——“凑合”。
“All-4-One”现场演出时也有这调动观众的问答“You have a good time?”6000多观众齐声回答:“Yes!”
我想,崔健如果有机会在工人体育馆再办个演唱会,6000多观众一起说“我们过得还凑合”,那场面肯定挺好玩,可是,他只能在3月28日的地下室里向一两百个观众发问和演唱。
“have a good time”和“凑合”之间没什么矛盾,我的意思也不是说,美国的“小虎队”只该在酒吧或俱乐部里唱,而中国的摇滚乐队应该搬出快餐厅和地下室去体育馆里唱歌,在哪儿唱都无所谓。可这是一场“文化斗争”,要对付美国文化,你得有东西,你还得有阵地。
这城市能看到6000个听了美国“小虎队”演唱去喝啤酒的年轻人,也该能看到6000个听了我们自己的歌曲而兴奋、疯狂的年轻人。否则就不大公平。
(本栏编辑:苗炜)
电话
●劳乐
有人告诉我,恐怖片中一般有3种必需的道具,其中之一就是一个白色电话。不幸的是我家里的电话就恰好是白色的,而且我经常会接到一些铃响拿起听不到任何声音,甚或是找我那位已死去多年的亲戚的电话。如此回想起来,我真的有点毛骨悚然。的确,电话的可怕之处在于你只能知道它响了却不知道是谁打来的。
有了呼机后情况好了点。呼机的好处是你不必马上作出反应,有足够的时间与信息去作判断;坏处是你无法与呼你的人直接联系,一旦错呼而且没有留下电话号码就很麻烦。当年我曾经在凌晨3点收到一位陌生小姐的留言,要我马上去一个名叫“沙窝”的地方见面。那时我刚有呼机不久,因此很当回事地打电话回呼台向寻呼小姐查询了半天。如今我已经学乖了,任何时候再收到诸如“在派出所老地方见”这样的错呼也不会有反应。不过我们呼台的小姐也着实敬业,什么样的留言都给发。到现在为止我收到的最惊心动魄的留言是:“董存瑞先生:你送来的炸药包我已收到。”
但这些与我的一位同事的经历相比还算不了什么。他曾经连续几个晚上不断收到一位陌生小姐发来的错呼。
谢天谢地,如今我又有了手机。手机上不仅可以显示出对方的电话,而且有时能显示出对方的姓名。更妙的是有的手机可以对接到的电话进行分组,然后用不同的铃声表示。这样在接听电话之前你就可以做到心里有数,准备好适当的语气与措辞,乃至决定接电话的速度。比如每当听到《斗牛士舞曲》响起时,我就明白是老板来找我了。然而这其中还有问题,因为毕竟只有5种分组,而我认识的人远不止5个。于是我又幻想能在手机上录上每个人最喜欢的音乐当作他们各自的铃声。这样我的手机上就可能出现《极乐世界》、《玫瑰之吻》、《时代的晚上》乃至一部马勒交响曲的整个乐章。但在幻想之余我仍然害怕。我怕自己有时会只愿意听那段音乐而不想接电话,或是久已期待的音乐总不响起,只好自己跑到铃声设置的地方凭空给自己添上几分钟的忧郁。
吃肉
文●杜比 图●王焱
最近市面上有一套书,共4本,叫作《与毕加索喝咖啡》、《与雷诺阿进下午茶》、《与梵高品葡萄酒》和《与莫奈赏花》。4本书构造差不多,比如梵高一册,将梵高的画作与葡萄酒的知识参差排列。尽管梵高当年生活窘迫,喝葡萄酒未必喝什么上品,(梵高的传记中总提到他喝苦艾酒,没尝过是什么滋味),但如今把梵高跟葡萄酒掺在一起就显得挺有品味了。
这套书是台湾人策划的,看来,他们很有点儿风雅之气。我看完这套书就跟朋友讨论,为什么不做“与苏东坡喝茶”或“与李白喝酒”的题目,把他们的诗词和茶叶公司的简介、酒厂的广告编在一起,也算弘扬民族文化。
朋友们说,与雷诺阿进下午茶,那是英国茶,与梵高喝酒,那是法国酒,如今中国茶太没品味了,茶叶市场太混乱,没什么叫得响的茶叶品牌,英国人乔治·奥威尔写过一篇文章,说,当人们谈到泡一杯好茶时指的是斯里兰卡茶叶或印度茶叶,绝不是中国茶叶。至于说中国酒,茅台酒或五粮液之类,总让人跟公款吃喝、请客送礼联系在一起,更是没品位。
这么一讨论,猛然觉得咱们历史悠久的茶和酒都变了味道,“与苏东坡喝茶”、“与李白喝酒”都不行,那就改为“与苏东坡吃肉”、“与唐伯虎卡拉OK”吧。
看来唯一可做的就是“吃肉”了。北京有线电视台刚刚播完一出电视剧《食神》,里面讲一个名叫赵十两的胖子对厨艺孜孜不倦的追求。此前,我们还看过周星驰的电影《食神》和徐克监制的电影《满汉全席》,值得欣慰的是,在英国茶、法国酒、美洲咖啡的包围之下,中国菜立于不败之地。
早几年,北京曾经有一家名叫“二月”的餐馆,打出的广告是“纽约最好的中餐馆”,这句广告真是自寻死路,纽约最好的中餐馆在北京恐怕是最最末流的,因为它的味道肯定变了。
在我认识的一些钟爱英国茶法国酒的朋友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外国菜不屑一顾,他们津津乐道谁的红烧肉最好吃,谁的土豆丝切得最细,他们家中都有一口烧茶的铁锅、一把沉甸甸的王麻子菜刀(绝不是190元一个的日本铁锅和5000元一把的德国菜刀)。朋友们聚在一起总要讨论去吃什么,上海菜、涮羊肉、炸酱面,确定之后又要切磋北京哪家饭馆的炸酱面好吃或哪一家的海鲜更妙,这时候谁要说去吃肯德基或“星期五”,他招来的必是鄙夷——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