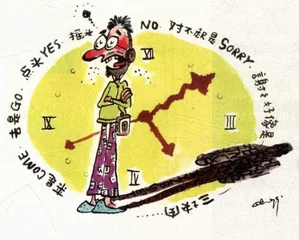生活圆桌(84)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史东东 徐斌 施武 应明)
改编
文●史东东 图●王焱
有一位先生曾经对我说,每次他去听中国乐团的现场音乐会,回家之后都要再找出相同曲目的唱片再听一遍,唱片都是外国乐团录制的,这样做的原因是现场听的东西不太对劲,耳朵不舒服,回家听了唱片,耳朵才舒服些。 前些日子我看电视剧《天龙八部》,感觉有些类似,看完电视里播出的两段戏,总得找出小说来读几遍,才会觉得心里舒服些。这次的电视剧据说忠实于原著,实际上不然,小说里到了第5册萧峰才和慕容复相见第一面,他见慕容复暗箭伤人,道:我萧某大好男儿竟与你这样的人齐名。可在电视剧中,萧峰在此之前与慕容复见过好几次,彼此还都挺客气。
一流的小说总难以改编,二流的小说则容易些。最近听说《小李飞刀》要改编成电视剧,这应该比《神雕侠侣》的改编要好办些。
有些小说,一出手就奔着二三流甚至四流去写,比如《马语者》,读小说的时候跟读分镜头剧本似的,这样的家伙太无聊,不能搞出点儿独特性的艺术家太无聊。
然而人们总难克制改编一流小说的欲望,我的一位朋友,挺有钱,酷爱金庸小说,他说他的梦想是投资把《笑傲江湖》改成电视剧,自己去演令狐冲,这样的人可比往年的票友更可怕。
我倒挺想看看有谁会把《麦田里的守望者》改编成电影,霍尔顿说:有的姑娘大腿很好看,有的姑娘大腿很难看,有的姑娘叉着双腿,有的姑娘没有叉着双腿。这是多漂亮的电影场面呀。可霍尔顿还说过:我最讨厌电影,最好你提都甭提。
我相信,想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制片人和导演多的是,但塞林格不答应,这样倔强的人值得佩服。
斯蒂芬·金的小说很好看,这样一个全球最有钱的小说家居然还要一部一部地出卖他的小说改编权,由此可见赚钱是永远不嫌多的。可是,这家伙老不愿意别人把他当通俗小说家看,老念叨自己的作品深刻,这就有点儿好笑了。
如果你珍视自己的独特性,就不会允许别人改变它,何况你不缺钱花。

我说乡下英语
●徐彬
我当年上大学,入了英语系可是误打误撞,没想到这玩艺儿很快成了时髦。现在回想起这事儿,我还颇有些得意。
正儿巴经学起英语来可使我开了眼。尤其是学着知道听多波段的收音机,知道VOA电台了。我如获至宝,毫不迟疑,义无返顾地跟着那“原汁原味”的美国音学了起来。赖父母所赐,本人舌头根子不是太硬,因而很快就知道如何让舌头打着卷儿嘬美国腔了。美国腔练了两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得到一位外教的认可,在朋友拉我去找她老人家学语音的时候她说我已经是“Perfect”了。然而这时却是我要背叛美国腔的开始。
因为此时美国腔开始时髦起来。借用英语的说法,或者是蹩脚汉译英文作品中的句式,就是“美国腔开始变得如此时髦,以至于我开始感到腻味了”。更使我腻味的是许多英语学习者不分就里,胡乱学美音,终导致了“泛美音”的泛滥。好在一般老百姓平常不会接触这类东西(其实到底是不是东西我也拿不准),所以泛美音还没有达到破坏生产力的程度。本人不幸,工作、娱乐都不免接触学英语的人士,所以常常受到泛美音的煎熬。这种东西,或称“不是东西的东西”,听上去的感觉就是说话人的滑腻腻、潮乎乎的舌头没地儿搁,楞要往你这边蹭。
更让我无可奈何的是泛美音,由于其多卷的特性,得到许多外行人的称许,认为这才是“洋味”实足的英文,所以,操一口泛美音的英语学习者往往能处处逢源,广受好评。
所以我决定不再学美音。改,改回英国腔吧。可怜大英帝国,板板正正的牛津腔竟一夜间不时兴了。我坚持听BBC英国广播电台,VOA从我的收听节目表中消失了。一段时间后,我的腔调又回来了。可是“业内”人士认为BBC腔太“势力”,是贵族自视太高、太贵的腔调。所以我学起BBC腔调来老不敢太放开,搞得我很别扭。
上学期来了位访问学者,是苏格兰人。说话甚是纯朴可喜,令我听后有闻陕西方言的亲切感。于是我大搞啤酒攻势,借机学他的苏格兰口音,一个夏天过去,竟也有不少收获。现在我跟学生念数字的时候,No.l就不念“拿磨温”,也不念“拿磨晚”了,而是念“拿磨旺”!
正在此时,接到一个电话,是熟人来咨询英语学习的。说她的儿子上小学一年级了,家人认为英语要从娃娃抓起,所以想让孩子开始学英语,遂买了磁带让儿子学。可一日忽然听人说,不能让孩子先学说英国音,不然搞坏了改不回来了。此人大惑,想起给我拨电话,问我这“业内”人士的观点。我说英国音搞不坏孩子的发音的,我倒是怕美音弄不好会搞坏孩子的发音,尤其是不幸请了满口泛美音的毛头学生做家教。友人于是旁敲侧击,说我的话肯定权威,自然教孩子英语也权威,……云云。我顿悟她意,忙说,咳,我的英文口语最糟糕,是乡下英语。
(本栏编辑:苗炜)
想象力贫血
●施武
有一个心理学小测试,测试人的想象力。试题是一个图形,被试者要说出这图形画的是什么东西。有的说是山,有的说是绳子,还有的说是驼峰,都被认为是没有想象力,只有一个小孩说是折皱的纸从横侧面看,被认为有想象力。这种评断其实并没有什么说服力。总的印象是,这种试测就够没想象力的。
有一个说法曾断言,莎士比亚之后,一切情节都是滥套,好像说得武断了,至少是对人类想象力的蔑视。莎士比亚就没有外星人的情节。美国电影大腕们弄出的E·T等等一系列外星人故事肯定是动用了想象力的。可是看上一两回,就觉得人的想象力真的有点贫乏,没有一种外星人与人的样子没点瓜葛,无非是变形而已。在一篇科幻小册子里的外星人倒是不像人了,可是那也不是想象力的结果,不过是说反话的一种,就像我们小时候说的“反唱歌”“颠倒歌”的逻辑。
有时候我看时装设计师的发布会也常有这种感觉,服装越来越怪,怪到人没法把那些东西当做衣服,这还不仅是趣味问题,是累。有想象力的创作让人看了会为之振奋,会像吸了氧一样有舒了一口气的开心。
我应该也算爱读书的人,但从来没积累下什么知识。小时候爹妈觉得我是好孩子,爱学习,后来没往他们认定的学问之路上走,就说我白读了那么多书。他们说的不对。做学问和读书肯定是两码事。我之所以读书,是因为我的想象力贫乏,从书中可以通过别人的脑子得到想象的快感和精神的飞跃感,就好比我吃饭不是为了变成饭,是为了让我健康地活着。从这种比较中可以看出,有想象力的人类作品就像有蛋白质有维生素ABCDEFG的食品一样重要。
有些东西刚一知道觉得它特有想象力,但经不起考核。比如对外星人的想象设计,比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最后发现所有事物都被分为两种类型,不是尖柱的,就是洞状的,这世界这人心未免太简陋了。可能人的想象力是贫乏的,所以,那种掏空心思编故事,一心想在莎士比亚之后趟出新套的作家总让人觉得胡说八道。
一辈子学外语
文●应明 图●王焱
夫人参加了一个什么班又开始学外语了,这在近二十年中已经是第n次。我免不了开玩笑地对她冷嘲热讽一番。
实际上我并没有多少嘲讽她的资格,许多同胞包括我本人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一辈子中几起几落、不屈不挠地用功学外语。可恨的是汉语实在与热门的外语毫无共通之处,日常生活中又几乎没有相应的语言环境,学起来真是难上加难。
我第一回学英语是在中学里。也不知是因为缺乏天赋呢还是别的原因,对之毫无兴趣。上课时老师讲的既听不进也听不懂,脑子里浑浑噩噩的不知在想什么。实在百无聊赖就拿支笔将课本上带圈的英文字母,如b、e、o、p等统统涂黑,使其看上去好像一只只眼睛。惹得老师好心地劝我:“与其同它大眼瞪小眼还不如背几个单词。”好在那时的高考着实体恤下情,虽然外语也考,但只占总分的10%。就这样半点英文不懂的我竟也踏进了大学校门。这像个陈旧的创疤,日后一提起来就让我脸红。
如今想起来,那时没能学好英文几乎使我一辈子都有些跛足。因为不得不承认我确实过了学外语的最佳时期,后来再补需化加倍的力气。直到今天,当我被看作一个读书人而问及念书问题时,我的建议总是一学好中文二学好英文,这样走路能稳当些。
当然所谓的“学好”谈何容易,容易的只是忘却和不断的反复。不久前我看日本电影《鳗鱼》,除了零星的片言只语,如いいえ”等,其他的对白一句也听不懂;元旦在电视上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对指挥洛林·马泽尔的德语祝词更是不知所云。令我丧气的是在念“打狗脱”时我是正经地学过一阵日语甚至德语的。真的是“书到用时方恨少”!而眼下需要外语的“用”又偏偏如此之多,使我至今还不时会重起学外语的念头。有次偶而听到电台里的一个法语教育节目,内容是杜拉的《情人》,一段法文一段中文地交替朗读。虽然对法文我一窍不通,但还是觉得杜拉的文字用法文读起来更加韵味十足。当时就想如果我懂法文该多好,想立马找个先生去学法文。
当然,为读《情人》而去学法文在老师眼里至少属动机不纯。但不管老师对这种学习的目的意义怎么说,外语的重要性被诠释得最淋漓尽致的还数最近看到的一则电视新闻。说有位法国农民订购了一批英国奶牛。不多日,奶牛们来到了法国农场准备安家落户。不料,这位牛主人想尽一切办法也无法将它们赶进牛棚。牛主人很快意识到他与英国牛之间有语言隔阂,可惜他不会英文。电视上可以看到他一手捧着本法英词典一手拿着根木棍在向牛群吆喝。具体吆喝什么不太清楚,大概总是“Moo—”,“This way, please”之类。也不知是他用词不当还是讲的英文带有法国腔,反正牛们全无反应。幸好在法国农村找个能说英语的人不难,我们看到奶牛们在这位说英语的法国人指挥下乖乖地排队进了牛棚。您瞧,不谙外语就是与外国牛都难打交道,何况与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