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姆斯特丹》到《沉默的公爵夫人》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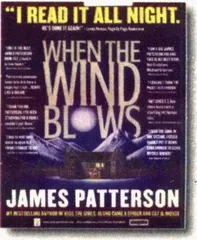
按照西方圣诞 - 新年假期的惯例,本期并没有什么新作上榜,我们可偷暇来介绍其他一些佳作。
一部是由伊恩·麦克伊文(Ian McEwan)所著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该书荣获1998年英国布克奖中的小说奖。
这部作品虽以荷兰首都作为书名,写的故事却主要发生在伦敦和湖泊地区(这是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多湖泊地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诗人华滋沃斯·柯尔律治和骚塞等即因居住于此而被称作“湖畔派”)。故事开始时,莫蕾·雷因的葬礼正在火葬场的小教堂举行。出席的人中除去她极善经营的丈夫乔治·雷因之外,还有死者早年的两位恋人:作曲家克莱夫·林利(Clive Linley)和报纸编辑弗农·哈利棣(Vernon Halliday),所有送葬的人都是在“充分的就业,新办的大学,色彩鲜明的简装书,盛行的摇滚乐,伸手可及的理想”的英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以当撒切尔夫人执政,以申斥取代恩赏时,他们都已经不为生活发愁了。
克莱夫和弗农是全书的主人公,他们的命运构成了全书关注的焦点。克莱夫自认是以民歌为英国民族音乐之源的拉尔夫·沃恩·威廉斯(1872~1958)的继承人,曾写过一本书反对现代派音乐的“保守派”及其排斥旋律与和谐的意图,书名叫《重现美》。他在书中描写由一个现代主义狂热分子所写的乐曲,“由公众赞助在一座几乎荒废的教堂大厅中演出,在一个多小时里,钢琴腿不停地受到一把小提琴的撞击”。后来,他又受命谱写一曲交响乐,委员会希望他把一个单一的曲调糅进千年庆典中。经过两次推迟交稿日期,他终于接近完成,按照“不可抗拒的旋律”,他将创作出“已死世纪的挽歌”。由于他把这一任务看作模仿贝多芬创作《欢乐颂》,这种好高骛远注定只会失败。
弗农所在的那家伦敦报纸《评判》的销售量正在下降,他为了维持职务,不得不拼命为提高其发行量而奔波。这时莫蕾的丈夫给了他一些由莫蕾拍摄的朱利安·加门内的非常有损形象的照片,让他拿去发表,定会收到奇效。但当弗农向克莱夫讲起这一机会时,他的朋友却深为厌恶,并责备他侮辱了对莫蕾的美好记忆,结果导致二人友谊的破裂。照片见报后,适得其反,把弗农拖入困境。
麦克伊文的小说使读者最难忘的便是他喜欢制造悲剧场面。而这种悲剧情节及结局又常有黑色幽默的效果。作家在《阿姆斯特丹》中描写这两个主人公走向灾难时,态度冷峻,甚至略带挖苦。当年曾有人问俄裔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他笔下的人物是否有时会失去他的控制,他回答说他所写的人物都是戴枷锁的奴隶,须臾也逃不出他的手指。麦克伊文在这方面也是不容置疑的。当然也有评家提出:既然这两个人物都很聪明,为什么会落个悲剧的下场?笔者认为,这恰恰是作者的深意。
另一部作品是达西娅·玛莱尼(Dacia Maraini)所著的《沉默的公爵夫人》(The Silent Duchess)。玛莱尼是意大利的杰出作家,她写散文、剧本,也写小说。她的这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全是杜撰,只是利用了当时的时代背景。
故事发生在18世纪初的意大利。又聋又哑的7岁女孩玛丽安娜,陪着她父亲—一位西西里公爵乌克里亚去看一个13岁的男孩受绞刑。由于他们的贵族身份,先是在屋檐下看地牢中的囚犯忏悔,后来又在刑场边上坐看他被处死。父亲这么做是想让女儿的听觉受到刺激,进而开口讲话。但女儿的感受竟然是“地狱居然能看着挺美”(她能读会写,这是她和别人交流的途径)这样颇有文学和哲理的评论。
玛丽安娜13岁时被父母强制嫁给母亲的哥哥也是父亲的堂弟皮埃特罗·乌克里亚公爵,用她母亲的话说“因为他爱你,所以什么也不要”,也就是省掉了父母出不起的嫁妆。于是她不久就嫁给了“总是穿红衣服,在家中被叫作‘大虾’的伤心又暴躁的男人”。在她和她这位“叔叔(舅舅)丈夫”婚后的27年中,她为他生下了5个子女,并掌管那栋大宅的家务。这位公爵夫人的古怪之处不仅在她的沉默,更在于她的嗜读。
玛丽安娜40岁成了寡妇后,益发埋头读书。她的聋哑却增强了其他感官的功能,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仍能明察秋毫。从外表上看,她似乎依旧年轻,一副端庄神圣的样子,无疑是一位天使。实际上似是对尘世妇女兼有母亲和姐妹关系的“无言的圣母”。
据介绍,女作家是接受了别人的建议,才以她的家乡西西里18世纪时的社会背景,写出当年骄横和虚伪的贵族政治,尤其是对穷人和妇女的残酷压迫。作为一名妇女作家,达西娅·玛莱尼一向关心妇女命运,在她的50余部作品中,这始终是一个重要主题。本书中的哑女形象含意深刻:一方面,在一个男女不平权的社会中,妇女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另一方面,这种“生理障碍”是由于她幼年受到男性凌辱造成的,从而把咎责归于居于欺压者地位的男性。
《陌生女子》和《围攻》
1月15日出版的《陌生女子》被《新观察家》周刊誉为“令人惊奇的出色小说”。写小说的是个53岁的、一直跟父母同住的笨拙男子,小说里面却是3个年轻女子的自述。
这3个16至19岁的女孩的独白令人迷惑和心痛。她们都很孤独,都很美,都出身平凡,她们的痛苦经历充满戏剧化的情节。故事发生在60年代初,那时阿尔及利亚战争正如火如荼,到处是秋冬季节的颜色,雨是冷的,雾是细密的,街是灰暗的。第一个女孩从里昂来到巴黎,她爱上一个男人,可当她明白他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积极参与者时,他已经被捕了;第二个女孩美得像魔鬼一样,可她从小就没有父亲,长大以后只身跑到瑞士,藏着一支手枪要杀掉欺凌她的男人;第三个女孩从法国南部来到巴黎,被拉丁区文化的骄傲和地铁那种城市特有的紧张迷惑之后,在咖啡馆遇到一个哲学家,哲学家带领她加入了神秘的教派,在那里她莫名其妙变成了被人使用的人。
3个羞怯的外省女孩幻想成为模特或者大学生,可她们进入的世界却使她们成了受害者。有钱的人、出身好的人、说漂亮话的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巴黎人伤害了她们。而她们对这伤害似乎又不很在意,作者也不在乎她们将来会怎样,他只是把笔借给她们,让她们把故事讲出来,然后担子就卸到了读者肩上,读者的心会沉重着,不得不思索。
这部160页的小说引起书评界关注主要是因为,一个男性作家以女性第一人称写作,写得非常细腻。“这对我来说很自然,”作者帕特里克·蒙迪亚罗解释说,“我当然不是在写纯虚构的东西。小说里有我自己的记忆,她们都是我在60年代遇到过的女孩,她们的许多经历我都曾有过。”
《移民》在风靡了德国、美国和英国之后,最近在法国也取得了成功。这本书讲述了四个无名无姓的移民的故事,其表现形式无比怪异,有照片,有文件,还有日记摘抄和明信片选登,甚至还有小孩子的乱写乱画。阿瑟·米勒称之为出色的作品,苏珊·桑塔格也评论说,此书成功描写了人失去自我世界的状态,其实“移民”的状态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状态。本书作者W·G·塞伯尔德本人就是移民。小说的主人公有两个犹太人,还有作者的爷爷和童年时代的老师,他们都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将自己封闭在过去的世界里,最后都非常优愁绝望地选择了在生命的半途死去—自杀。
《围攻》是又一部成功小说,《快报》书评说:“它虽然是纯虚构的,可它比任何有关波斯尼亚的纪实文字都更有力。”作者胡安·戈斯蒂罗历来认定小说就是要发声,要质疑,要探索,他这部关于战争的小说可以说是典型的“介入的文学”:一个人来到一座被包围的城市(读者很容易看出,这城市隐喻着萨拉热窝),在城里经历种族灭绝分子的暴行。可贵的是,戈斯蒂罗的“介入”绝不生硬,他把这篇小说写得像侦探小说一样充满悬念。
(刘芳) 文学小说文化公爵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