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岁片:没事儿偷着乐?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卞智洪)
现在,似乎所有的人说起电影,都是在商业电影范畴内—它无疑是重要的,但不应该是垄断的
看电影已经越来越像是去超市买日用消费品。约伴儿,定地点,乘车,买票,坐在漆黑的大厅里,把目光集中在一块两维的幕布上,有劲或者没劲,乐一乐再发两句牢骚,有亲朋问起来会告诉他们值不值得看—就此打住。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生产厂家,电影的流通目的已经完成,没人会期待它对我们有什么精神上的影响。
然而逢年过节,更多的人还是会到超市去采购,尽管这个偌大的超市如今只卖一样东西:彩色气球—在1998年圣诞节到1999年春节之间,如果有人谈起电影,他是说贺岁片如何如何,他是在说以下这几部电影中的某部:《不见不散》,《没事儿偷着乐》,《好汉三条半》,赵本山、宋丹丹主演的《男妇女主任》,成龙的《尖峰时刻》,李丁、侯跃华主演的环保题材儿童片《兔儿爷》,吴倩莲、陈小春主演的《春风得意梅垅镇》,以及艺玛公司的《美丽新世界》等。

《没事偷着乐》剧照
《没事儿偷着乐》讲述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恒小说题目)。影片开头精心设置了大民一家局促的生活空间,以及由此决定的同样局促的人际关系。冯巩扮演的张大民无力也并不试图拓展空间,而是勉力辗转腾挪,划地为牢,营造稍显人道的生存空间。他以自己的方式为四个兄弟姐妹排忧解难,并为此暗暗得意。导演杨亚洲曾任黄建新的副导演,他学得了黄的现实主义立场,却没有其冷峻的审视态度,对大民更多采取了一种认同的视角。在影片结尾,大民的生活自然改善(因旧屋拆迁而分到较宽敞的新房)以后,他背着老母上山游玩,接着又在一条充满象征意义的铁轨上,对儿子说:“孩子,你就没事儿偷着乐吧!”—若仅就生存环境而言,今天多数观众与大民的差别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别,但这种“张大民精神”却难免令他们寒心。在叙事结构上,这类题材的优秀影片往往前松后紧,最终的矛盾解决能超越琐事本身,给人以震惊的体验,但《没》片的后半截却有些勉为其难。
《不见不散》几乎沿用了《甲方乙方》的原班主创人员,但外景地搬到了美国,故事也变得比较完整:葛优和徐帆扮演的两个新移民在美国的情感故事。编剧熟练地运用了喜剧片的一些技巧,比如对某个角色或者对观众隐瞒信息以造成喜剧效果—当徐帆为了见见葛优的新伴侣而装作不经意地上厕所时,这种幽默感是令人欣赏的;但当吊起观众的悬念(比如遭抢劫)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轻易解释成虚惊一场时,这种噱头就不再是噱头了,它像一个人总是在背后冲你猛地大喊一声。不断有这种出局的搞笑段落恐怕是因为影片没有一个立得起来的主题(无论新颖的还是俗套的),而对于一个缺乏性格与热情的角色,葛优又能赋予他什么呢?无非是贫嘴罢了。
《好汉三条半》:兵营好汉李琦强拉从前当过兵、如今做了老板的陈佩斯和如今搞健身器械发明的温兆伦去参加预备役训练,两人均舍不下事业逃了出来,但最后却心悦诚服,你好我好全都好。这样一部影片拿到大众影院里放映,令人要么有一种国难当头,全民皆兵的恐惶感,要么有一种时光倒流若干年的荒诞感。贺岁片并非理所当然就应该是喜剧片,但喜剧片(尤其是滑稽搞笑片)似乎天然地适合贺岁:平时你挤个对对眼或者掉进水池子里别人会觉得你挺怪,但过年的时候这就成了幽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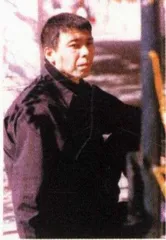
《不见不散》导演小刚
《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的票房成功(后者在北京的1998年12月24日—1999年1月18日间已经取得1100万元的票房),很容易让一部分电影人、观众、媒体甚至政府官员认为,这就是商业化的中国电影范本,更严重的是,国产商业片就应该是这样—喜庆、轻松、赚钱,并且不触及现实生活矛盾。应该说,两片只是商业片运作上的成功,而非商业片制作的成功。《中国青年报》上一篇题为《贺岁片“不赔不散”?》的短文,引述了导演田壮壮的一番话,恰说到节骨眼上:拍电影无非是两种方式,一种是描述自己的经验世界,另一种是重新造出一个谁也不知道的世界。好莱坞更偏爱后者,像《E·T》、《拯救大兵瑞恩》,都是由工业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但是一点也不生硬,还让人觉得地道。我们现在的贺岁片是市场化的电影,但还不是电影工业的成品。冯小刚的两部作品拍得很聪明,但也很容易让人看出他的来历,因而并不是好莱坞的“造构”。如果他还要在市场电影的路上继续走,倒希望他在《不见不散》后,能拍出一部“制造出”的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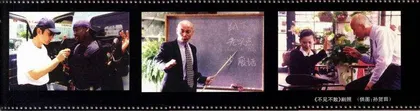
《不见不散》剧照 (供图:孙贺田)
这样两部影片的宣传攻势和明星号召力(不仅是葛优、徐帆,还有冯小刚)都是强大和成功的;主创人员利益与影片收益直接挂钩的方式也是成功的(冯小刚从《甲》获益100万,又为《不见不散》出资200万);更为成功的是档期安排,—所谓贺岁片说到底就是一个档期问题。事先确立一个最佳的放映档期,实行倒计时操作,这是极为标准的商业化模式之一;而贺岁片则是另加一些港台特色。以中国巨大、复杂的电影市场,引入港台的贺岁片模式是否合适仍是一个有待讨论和检验的问题,就像流行音乐创作风格走港台路线最终没能成功一样。而且一旦决定“贺岁”,就没能为非贺岁片(假定不是所有的电影人都要在过年时向观众拜年,也不是所有的观众都需要电影人给他们拜年的话)留下一点喘息的空间,也未免有些武断。
贺岁片的暂时卖座除证明商业化操作的成功外,还表明观众需要电影、观众暂时还比较相信媒体宣传,此外,目前国内的商业片质量基本不超过《不见不散》的水平。影片的商业化并不仅指内容的娱乐化和大众化,主题的完整性和现实性也应是题中之意。再则,就整个工业系统来说,产品不断更新是最基本的一个要素,而更新显然不是指把故事背景从中国搬到美国。如今电影业信奉发行商说了算,意即观众想看什么决定生产什么;但问问发行商吧,他们总是说:某某片子不错,就要这样的。
当我们说起商业片,首先想到的总是好莱坞,好莱坞的制片/发行/放映体系,好莱坞的技术力量,甚至好莱坞的创作观念。然而还有很少为人提及的一点:商业电影如果想持久发展的话,是否需要一些并无商业性的外围力量?一些富有创造性和实验精神的艺术天才?为他们的出现所容留的空间?没有科波拉、斯科塞斯、斯皮尔伯格等人,很难想象好莱坞将如何从50年代的梦魇中蜕变出来,进入一个新好莱坞(现代主义的)时代;没有世界范围内的一流导演的加盟,没有为好莱坞提供翻版机会的法国电影,甚至没有美国的独立制片公司、另类影片导演,好莱坞如何可能健康发展?
然而目前铺天盖地的影片宣传已经昭示出国内电影的位置所在,以及我们所汲汲以求的目标。电影制作/发行/宣传/放映的整体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达到统一:如果不是主旋律影片,那就必须贴上商业片的标签—这不是鼓励观众去看电影的一种最佳方式。目前动辄就说电影市场,我们的电影市场比几年前的确活跃了许多,但是否就更健康呢?我们是否有一个健康的电影文化呢?80年代没有商业意义上的制片人,但是有优秀的电影、导演和演员,而现在有很多制片人,有各类财源,有美国的小公司,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不屑于区分艺术片和娱乐片,他们鄙视精英主义,他们不断在做市场策划和营销,但我们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好电影呢?
回首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会发现每一部富有成就的电影都是出于某人想说点什么的愿望而不是想卖掉什么的愿望:《黄土地》、《红高粱》、《脸对脸,背靠背》、《阳光灿烂的日子》等等。这些影片在商业上未必成功,但他们有助于建设一个健康的电影文化氛围,有助于开拓商业片领域和刺激商业片水准(就像80年代后期那样),有助于引导观众的消费品位(造势而非一味顺势)。如果我们过分看重几部贺岁片并由此为商业片下定义、划分电影市场,就像张大民在一个小小的杂院儿里辗转腾挪,辛苦恣睢,还要没事儿偷着乐—那无论此消彼长,都是令人感到悲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