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离你远?离你近?
作者:舒可文(文 / 舒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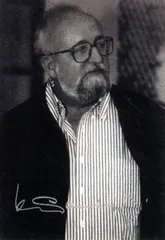
作曲家潘德列斯基
70年代末,小泽征尔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北京演出时,没有前期宣传,也没有后期乐评,对一场演出的操作显得外行,但那场演出的效果却非同寻常,至今让人不能忘记。我仍然记得小泽征尔特殊的发型,记得前几把小提琴手看指挥的眼神,还记得那些通宵达旦排队买票的热血青年。
20年过去,北京有了规模不小、档次很高的国际音乐节,能够在相对短的时间里,集中不同乐团、不同风格、不同演绎家于北京舞台,不能不说是北京的进步。而且对于听众而言,相对20年前,不能不说是一种福气。乐迷们事先可以拿到节目单,可以有选择地购票。
此次音乐节中,评价普遍很高的是捷基耶夫指挥基洛夫乐团和鲍罗丁四重奏乐团的表现。《爱乐》执行副主编曹利群说,听了基洛夫乐团在大会堂的演出就证明了一种说法——唱片就像罐头食品,唱片把音乐修整得过于干净,失去了现场的鲜活感。尤其是俄罗斯音乐,在捷基耶夫的处理下,野性、粗旷,虽然细节上可能有点粗糙,但鲜活,有力度。从大会堂出来,观众的兴奋都可以看出来。曹利群评价这场演出体现了俄罗斯乐团访华演出中的最高水准。他说,捷基耶夫和他的基洛夫乐团充分展示了管弦乐表现的魅力,既体现了浓郁的色彩感又有精彩的速度对比。《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奏处理得像是旋风卷过,而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夫第三乐章年轻的王子和公主的爱情,以极慢的速度,表现出迷人的抒情性,在叙述中因为有浓郁的情感注入而味道十足。
这次音乐节使国内的古典音乐爱好者,能从不同乐团的现场表现中,来真正体会西方古典音乐经典作品的魅力。同基洛夫乐团具有同样魅力的是柏林广播交响乐团,这支乐团演奏的纯正的德奥音乐作品,与基洛夫乐团演奏的纯正俄罗斯音乐作品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大概听现场与听唱片的区别中这也是一点,即有所期待,你在听之前不知道将听到怎样的贝多芬,怎样的肖邦。
傅聪带给听众的“肖邦之夜”音乐会,让听众对这位传奇的钢琴家再次凝神。国家交响乐团的王纪宴评价说,傅聪的肖邦完全没有19世纪的沙龙气,而是细腻而有力。这也许更符合波兰人理解的肖邦。相对于“肖邦之夜”,傅聪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合作演出,则有另一种反映,有人感叹为“廉颇老矣”。曹利群写的乐评就题为“老来不弹莫扎特”,因为莫扎特音乐中的无拘无束、过剩的精力、嬉戏玩耍完全是自然状态中的,老人演奏这种音乐时去捕捉这种东西,不自然。
潘德列斯基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合作的反响中褒贬反差最大,有人说作为作曲家的潘德列斯基在演绎别人的作品时能够比一般的指挥更理解作曲家,因此更为精辟;有人则认为正是因为他是作曲家,所以在解释别人的作品时过于独断。
其中是非见仁见智。
评价普遍不高的,也是圈内人在说起此次音乐节水平参差不齐时举例的是恩里克斯的吉它音乐会和日本的西崎崇子小提琴音乐会。但是没有人愿意细作评论。媒介所见的乐评也是一片叫好。
作为盛会的北京音乐节结束后,北京听众在慢慢消化了兴奋之后,此次音乐节前前后后的相关问题突出出来。甚至有圈内人说,这种景观是否适合中国也难说。
首先一个让很多听众,尤其是熟悉音乐的听众难受的现象是音乐会之后的乐评。虽然说对一场音乐会的高低好坏见仁见智,但是乐评的水准仍体现了音乐欣赏中的基础水准低下。曹利群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乐评起码不能出常识性的错误。他举例10月29日《生活时报》上的“名家随笔”中把基洛夫乐团演奏的4个曲目分别冠以“印象派、民族派、现代派和典型的古典派”,这是常识错误。社科院文学所的王毅也提到这个乐评,对其中以杜松子酒之类的4种酒,再后来的4幅画来说音乐非常不以为然。他的理由是,这种乐评反映出评家对音乐本身了解不够,只能用外在的东西往音乐上抹,评论的结果是损害了音乐。文学联想太多了,离音乐就越来越远。曹利群说:“其实何止乐评,在《莫扎特之魂》之类的专著中此类离谱的话更是比比皆是,书中引用了爱因斯坦、普朗克的物理公式和数学公式,牵强附会地与音乐作品套上。如果你不懂高等数学就不能听莫扎特了?其中还提到奥地利的地理环境,以作者的感悟告诉读者,如果你没到过那里就不能听莫扎特,这太过分了。”在中国目前音乐环境尚在建设之中,此类乐评对本来欣赏素质就不高的听众会形成误导。
第二是没有主题。在如此集中的时间里举办大规模的音乐节,如果没有主题会显得杂乱。有人形容这种杂乱像群众文艺调演。就此我询问了参加过多次音乐节的作曲家郭文景,他说,通常的音乐节是有主题的,比如1994年他曾参加的阿姆斯特丹音乐节,主题是“中国新音乐”,还有一次主题是“室内乐”。确定主题对选择乐团、演奏家会显得有的放矢,而且对于演出市场也是一个传播音乐知识的方式,主题鲜明、集中,无形中也是一种音乐教育。
第三个问题是演出场地的单一模式。这当然不是举办者所能解决的,而是一个关于城市建设的问题。音乐演出对场地的要求之高是其他艺术种类没法比的。耳朵敏感一点就能感觉到其中的区别,一个交响乐团和一场室内乐演出所要求的是不同规模不同规格的场地。场所可以直接影响音乐节的质量。郭文景提到过令他非常感动的一个小小的三重奏音乐会,在美国的密西根。这个音乐会就在一所普通的大房子的客厅里举办,10美元一张票。那个场地与那个三重奏音乐会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气氛。他还说到在纽约的一次演出,好像是比较“前卫”的演出,就在纽约下城一个很破烂的地方,一个像农家院子的地方,坐椅都是木头搭的。这也许是对北京音乐节举办者的一种提示,我们的专门演出空间有限,但可以利用一些别样的空间,也是一种补充,也许更有味儿。
此外,当然还有票价问题。80年代时,大家普遍不富裕,但买音乐会的票时没有因为票价思量过。而现在北京却有一个庞大的听众群是等着送票的。
无论如何,今年10月的北京很音乐。关于音乐的话题四处被说着,不管是有钱买票的、有人送票的,还是坐在家里听CD的都各有所得。 肖邦莫扎特艺术音乐音乐会演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