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系统中的选择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胡泳)
历史:一个技术驱动过程?
1989年6月,苹果公司出了一件事。有人偷偷拷贝了公司专有软件Color Quick Draw的一部分源代码,这种软件可以控制驱动麦金托什机屏幕显示的一种内部芯片。它是苹果公司严密保护的知识产权,只有受到高度信任的权威人士才能拥有。
但“新普罗米修斯联盟”却想改变这种状况。此人(或许是好几个人)偷偷拷贝了不止一份软件源代码,他(或她,或他们)随后把带有源代码的软盘装入信封中寄往美国各地,收信人都是在计算机业工作的人员。整个事情不是一起工业间谍案,而更像是一出有意侮辱自以为是的苹果精英的恶作剧。显然,在搞恶作剧的人眼里,苹果公司仿佛专横的宙斯,而他自己则是反叛的盗火者。
这一恶作剧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传说中洪荒年代的普罗米修斯没想过他在电子时代的重生吗?普罗米修斯一向在技术崇拜者的心目中具有重要意义。技术的发明者常常被比喻成这位反抗宙斯的“革命之神”,是他们将知识带到凡间,从而极大地解放了人类。例如,历史学家塞缪尔·弗洛曼把谷登堡、瓦特、爱迪生和福特都称作普罗米修斯式的革命者,也就是说,技术的本质是革命性的,因为它斩断了常规和习惯的纽带。从这样的类比中不难得出结论:反对技术就是反对革命。

技术是一种决定性的变革力量,这一看法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的“进步”观,它在当代思想中占有显著的位置。任何经历了计算机崛起的人都对此有切身的认识。他们亲眼看到计算机怎样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基本面貌,即便没有用过计算机的人也不得不在超市、邮局、银行、图书馆、学校、航空公司和医院里与之打交道。几乎现代生活中的各个层面都受到这一新的信息技术的影响。当然,计算机只是那些具有深刻影响的技术中的一种——电视、飞机、核武器、抗生素、避孕药、器官移植和生物工程等等,都加深了人们对技术变革性力量的认识。
技术能够改变社会的主题一直在历史上回响,由此产生了许多小型的神话的“此前—此后”的叙述方式。例如,在15世纪以前,据说欧洲人对大西洋彼岸所知甚少;其后,哥伦布等探险家借助指南针和其他航海设备穿越了大西洋,在整个新大陆建起了殖民地。指南针由此成为欧洲统治世界的“前提条件”。
同样,印刷机是导致宗教改革的动因。在印刷机发明之前,除了神职人员以外,《圣经》难以到达普通人手中;在谷登堡之后,手写的经卷被印刷品代替,教会和其他大人物不再那么至高无上,个人得以直接与上帝交流,宗教改革运动成为不可避免。再如,美国的历史书中充满了关于内战的发生与轧棉机的发明之间联系的假设。在18世纪末叶,实行奴隶制已经无利可图;但在埃里·惠特尼发明轧棉机后,使用非洲黑奴收获棉花成为赚大钱的行当,奴隶制重获新生,最后的结果是,北方与南方爆发了一场血腥的战争。
这样的叙述方式生动地表明,技术是历史发展的驱动力量:一项技术革新突然出现,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与历史学家笔下其他抽象的力量(如社会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力量)不同,技术的力量更直观,似乎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能够自动地激发变革。换言之,对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的人来说,历史往往可以定义为一个被技术驱动的过程。
在技术系统外生活的自由
技术决定论的想法在人们中间非常流行。这典型地表现在“技术”一词成了一个活跃的谓语的主语:“汽车造就了郊区。”“机器人剥夺了技工的工作。”“避孕药引发了性革命。”“网络消除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每一种说法中,一个复杂的事件都令人信服地被视作一项技术革新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些说法还暗示,技术创新造成的社会影响是深远的、累积的、不可逆转的。普通个人对技术无能为力。
一项发明一旦引入社会,就被描述成“获得了自身生命”。例如,计算机的不断改进遵循着一种内在的逻辑。在一个似乎事先定好的序列中,“每一代”更先进的计算技术都导向下一代。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推广,越来越多的机构不得不重新布局以与改进了的技术保持一致,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作为整体,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大型的、微妙地联结起来的技术系统。网络成为经济不可缺少的技术盔甲。它的持续运转,成为重建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
然而,人们是否想到过,人类面对技术时的那种无力感,可能是技术系统的设计者有意造就的?在设计之初,技术系统是完全可以响应人的要求、关心人的愿望的。那些致力于庞大而复杂的技术系统的人,是不是在蓄意制造技术决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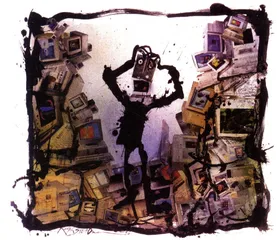
任何技术设计都融进了设计者的价值观,而驱使一些赫赫有名的工程师作出发明的,正是他们对技术的美学追求:渴望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技术系统。普罗米修斯式革命者爱迪生和福特都是绝好的例子。除了美学追求而外,建立复杂系统的政治原因也显而易见。哈维尔就曾说过,现代文明的基本思维方式是,通过聚敛更多的科学知识和更大的技术力量来建立更好的控制系统,从而一举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在现代技术环境中,我们似乎有了更多的选择(与古代社会中技术匮乏的情况相比)。然而“技术的暴政”的真谛在于,它不是通过摧毁人们的选择自由,而是通过塑造人们的选择心态、缩减选择的可能性来使人俯首听命于技术。以汽车为例,你的选择机会似乎很多:你可以挑选自己喜爱的颜色和各种配置;但是,重要的决定,诸如要什么样的推进系统,你是无权作出的。电力或蒸汽推进系统一个多世纪之前就已出现,然而对消费者来说,它们的存在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事实上,电动汽车今天之所以没有市场,是因为技术并非以单独的组件而是以系统的面目出现。目前的系统是为燃烧汽油的汽车而设计的。如果要想把成千上万辆电动汽车推上马路,就必须彻底改变整个支持网络——加油站、汽车修配厂等等都得改观。这牵涉到整体的技术基础设施。由此可见,人们选择的多样性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过,技术决定论只有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中才最见效,“技术变革的力量已被释放出来,而能够控制或引导技术的机制却付之阙如”。社会控制的缺乏使某些社会群体获利匪浅。毕竟,创造技术决定论的是人而不是机器。
还有什么比冷战时期的核武器更能说明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选择核武器作为一种防御方式,但它是我们最后的“自由选择”。选择了核武器,意味着我们必须遵循它规定的条件,按它的要求出牌。将决定权付诸一个技术系统,这看上去是反理性的,然而在政治上却站得住脚。为了使大规模报复的威胁显得可信,人类决策的因素必须被去除,因为有理性的人会选择谈判而不是战争。
文化批评家刘易斯·马福德在1963年写道:有两类技术在历史上共存,一类是民主的,一类是专制的。“民主的技术意味着小规模的生产方式,主要依托于人的技能和畜力,即便使用机器,这类技术也总是在工匠和农夫的娴熟掌握之中。”民主的技术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存在,而专制的技术则是新近现象;它依靠冷酷无情的强制手段,将个人编入工作大军和战斗大军,以实现大规模建设和破坏的目的。由此,马福德将冷战时期的核威慑政策归因于人类的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创造支配自然、最终也支配人类自己的技术系统。专制的技术就是要把权力置于技术系统之中,“这种权力是不可见的,然而却无所不在”。这类技术的最终目标是取消生命,或者,将生命的特性转移到机器上……
马福德的理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善恶对立观:以人为中心、力量虽弱而具有持久性的民主的技术同以系统为中心、力量强大但却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的专制的技术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对立。这种宏大的理论有很多方面经不起推敲。小规模的技术可能和大规模的技术一样限制人类的自由。而且,许多工程师会争辩说,技术系统并不具有内在的专制特性,在设计上完全可以做到灵活而民主。但是,马福德最成问题的结论是,技术决定论只是一种幻觉,只要我们抛弃“机器神话”,我们就可以重新获得对技术的控制。虽然有关专制系统存在理由的说法是一种虚幻的神话,系统本身却是非常真实的。如果系统有足够大的规模和范围,它们确实可以按照其创造者的旨意行事——剥夺人类在系统外生活的自由。
系统可以不和你玩,但你不可以不和它玩。 苹果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