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75)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孙志和 老杰 商连昌 邱贵平 张艺明 胡滨 王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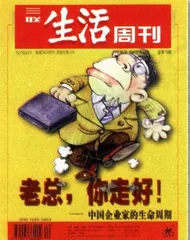
民营企业的兴衰,实际都与我们的商业化操作缺少规则有关。不仅因为管理能力,也不仅因为素质不够,一个没有规划的市场,不可能诞生真正成熟的大企业家。
北京 孙志和
号召“下岗”?
北京西城区官园 老杰
1998年9月24日,我骑车从北京图书馆门前经过,发现马路边上竖起了高高的广告灯箱,日:“做一个自立、坚强的下岗人!”呜呼!下乡之后闹下海,下海之后又开始闹下岗,难道我们又要响应号召,下岗进入21世纪,下岗“创造明天灿烂的辉煌”?
我非故意刻薄之人,然确实打算抠抠字眼。首先,“做一个自立、坚强的下岗人!”这句话制作成广告灯箱且公之于众,则显然有了广而告之、号召鼓励、宣传推广之意。其次,这句话(标语)对那些已经下岗或者即将下岗的人来说,感觉上绝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您想想,假如您已经失业赋闲,没工作、没收入、没办法,您不自立、不坚强、不自谋生路行吗?!再者,此举多少有些“事后诸葛亮”的意思。别人下岗了,你立马儿出来说“要自立、要坚强”,问题是,在人家面临下岗还未下岗的时候,你采取过措施付出过努力挽救过下岗吗?再退一万步讲,即便把制作标语广告灯箱的那一大笔钱用来接济下岗人员,也比华而不实喊口号要强过千百倍。
诚然,在市场经济体制建构、运作过程中,一些企业必然因体制转轨、经营管理诸种情况而导致亏损甚至倒闭,部分在职人员失业下岗在所难免。问题是,面对日益严重的下岗危机,不从根本上着手解决问题,却“几十年一贯制”地以标语口号、语录宣传来隔靴搔痒,这样做到底有多大意义和实效?
话说领导干部住宾馆
浙江嘉兴市振兴路 商连昌
县(市)级以上领导干部交流、易地任职,都住进了当地的宾馆,有的说这是“工作需要”,有的说是助长领导干部“养尊处优”,也有的说“有利有弊”。本文对此不妄加评说,但有一笔经济账可供大家商榷。目前,地(市)级行政单位有336个,县(市)级2183个,合计2419个,如果平均每个单位按有3个领导干部计算,共有易地任职领导干部7257人,以每天每人住宿费150元计算,一天即花去费用1088550元,一个月为32656500元,全年支付住宿费近4亿元。用这笔钱可以解决年收入5000元职工8万人,或者可以解决下岗后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200元的失业人员16.6万人,笔者不希望领导干部像50年代那样“背包下乡”,60年代的“同吃同住同劳动”,但该有个节制办法,当然这是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事了。
盗版“明星”
福建省光泽县水泥厂厂办 邱贵平
福建东南电视台有个综艺栏目“开心100”,每周一期,其中有个压轴栏目叫“模仿明星脸”,真是“百分百开心,百分百火爆”。每期都有3至4位来自五湖四海长得像某位明星的选手参赛。模仿者大都是年轻人,被模仿者也大都是年轻的影视歌明星,有一位刘德华的模仿者,既酷又似,酷似之极,几位姑娘忍不住当场献花,把“刘德华”激动得差点晕倒。
长得像明星,肯定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然而芸芸众生,长得非常像刘德华、张学友、巩俐、张惠妹的人毕竟少之又少,长得像的,当然要幸福得发抖,名声钱财前途暂且不提,现成的掌声和鲜花足可以风光一时。在这个明星辈出、明星更新换代比电器还快的年代,能够红上一年半载也是幸甚至哉了。如果长得像陈景润、张海迪,谁买你的账呀。至于长得谁也不像的,只好当狂热的观众,有志气和才气的,还可以去当发明家,发明一种印刷明星脸皮的机器,普通人只要买上这么一张脸皮,往自己脸上一贴,便拥有了一张明星脸,发明者能否获诺贝尔奖暂且不提,发大财毫无疑问。当然,也可能因此犯罪,罪名是“盗版”,侵犯肖像权。
盗版明星的应运而生,也是人们不分青红皂白过分崇拜明星所产生的副产品,明星虽然越来越多,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他(她)们永远都生活在电视和报纸的周末版上。谁都想当明星,当不了明星与明星亲近亲近也是好的。最新例证:谭咏麟、张信哲、张学友、甄妮、周华健赴北京参加10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爱我中华,重建家园”赈灾义演晚会后前往附近的一家麻辣火锅城吃夜宵,火锅店徐娘半老的胖老板娘兴奋不已,乘敬酒之机这个摸摸那个拍拍,着实过了一把手瘾,结账时虽然只收半价,而且酒水全免,明星们还是觉得吃了大亏,因为被老板娘“揩去不少油”。如果是盗版“明星”,恐怕就没有这种“吃亏”心理:既能打折又能享受按摩,何乐而不为,你以为你是谁?
不求真中假,但求假中真,这才是盗版“明星”成为明星的唯一出路和可能。
寄两盒磁带
广州 张艺明
这天我去邮局给外地的朋友寄两盒自录的爵士乐磁带,邮局不锈钢大钢管栅后的小姐告诉我有规定:“寄音像制品要有文化局证明。”我吓了一大跳。这事情怕严重了,可为了达到寄出去的目的,还是赖兮兮地跟小姐说,我这不是音像制品,只是空白带,给寄了吧!小姐笑着说,录音带怎不是音像制品。需要去市里文化局写证明。我碰了一鼻子灰,寄些小东西还要劳官员的驾,行吗?而且人家难免不问这带子录的是什么音乐、黄不黄?是否要扫黄打非办审查,国家版税局纳税,消费者委员会证实……太多了,我不敢再往下想,唯有对不起外地的朋友,放弃此念。
痛苦的本钱
南昌 胡滨
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的某篇文章这样开头:“恕我直言,……算是不太好玩的一个……”我就生活在这“不太好玩”的省会城市中。大部分文化人其实都明白,余先生所言的不好玩绝还不只是指这座城市的外延部分——我有点明白,但常常的羞于提它。
10月中旬的一天,地方有线电视台播出一则新闻,讲的是抗洪赈灾物资不能原样送到了农民手里。电视画面上展示的棉被多是那种破旧成丝条状的,连并非见多识广的农民也明白这绝不会是城里人的捐献。农民脸上只有失望和气愤。奇怪的是,身边许多在今年一再响应号召捐钱捐物的人懒于谈论此事,更别说为此表明痛苦。不用翻辞典,大家都知道“痛苦”是严肃的字眼,不过在恰当的时刻恰当的表明痛苦不应当是滑稽之事吧。
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丧失了痛苦的本钱呢?
两周前,我的一位在珠海工作的朋友深夜打来电话,语气沉重地诉说失恋的事。我为他焦急,甚至提出请假到南方陪他一段时间。因为大学时期,这位朋友曾经为爱情而发生轰轰烈烈的事件。结果,他居然笑了起来:“以为我还会为了爱情……”对方用一种带嘲弄的语气。我放心了,但后来又很不放心起来——究竟什么使一个人认为自己连为爱情痛苦的本钱都没有?
5天前,有北京的一封来信。信告诉我,另一位朋友与太太共同吸毒。“太太”我不熟,仅是婚礼上见过一面,是很美丽、家境很优越的女孩。信里故事讲的不光是吸毒这一事实,令听者痛苦的在于结局:身为独生女的“太太”自杀,而朋友在监狱。我心情沉痛。其他在京的朋友,兴趣却在不断补充那朋友逼迫“太太”弄钱吸毒,终于使她割腕的细节上。
在我看来,痛苦不具备攻击性,是内心世界的一种状态,带点情绪带点内省反思性。当一切痛苦都被用“非痛苦”这个方式表达时,世界才太不好玩。因为“没有了痛苦的本钱”,越来越多的人在应当痛苦时还满脸写着不在乎。
看起来,一段时间里盛行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态文化算是开了花结了果……从南到北,因而将会有太多“不太好玩”的城市和乡村。
我们结婚了
成都市实验小学 王婉
读着今年17期《我们结婚吧》,我结婚了。去年此时,苦恋两年的男友分手了,我几乎痛不欲生,一年过去了,似乎什么都变了,又似乎什么都没变,我依然要结婚了。他是谁?我好像也不大清楚,反正他的条件几乎都不如我意,可我们要结婚了。他给予我无比的关爱和包容,给予我无尽的深情与期待,当然还有无穷的自由与尊重,我对这一切都无力抵抗,渐渐习惯了他对我的包围,每时每刻每分每秒……
没有捧着玫瑰,揣着钻戒来求我,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来威胁我,只淡淡捏捏我的手:“我们怎么办呢?月底就要分房子了?”也只是一种淡淡的回应:“明天就去开介绍信,但还有好多事,可能下周才能领到结婚证。”似乎是闲聊着一件不关于我也不关于他的事,平淡而又平静中生命就划入了另一个轨迹。父母的震惊,朋友的惊呀,都不足以将我从一种“执迷不悟”的麻木或者是快乐中惊醒。我说:“管他呢,指不定这次就对了。”张爱珍说:“久赌必输,久恋必苦。”我信她。
人说恋爱是为了结婚,我说结婚是为了恋爱。婚前只当他是一个考察对象,万般刁难,气自己也气大家。婚后没有胡思乱想了,当然全心爱他,疼他,那个属于你的男人,那个要陪你一生,愿为你而改变的男人。
没有房子,没有家具,没有存折,没有……我们一无所有,却彼此给予了对方最高的赞美和奖励——我们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