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高峰中的安全感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高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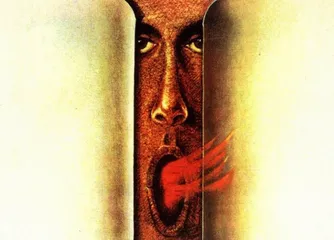
我们正在目睹第5次犯罪高峰
舒芳在北京安定门内大街上的一家公司工作,上下班出入的地铁站紧临着二环路上从早到晚车水马龙的安定门立交桥。尽管桥下沿护城河有人行通道,但舒芳每次过桥都从上面的路口穿行。同事们告诉她,河边人行通道有人专干把行人推下河抢包的勾当。舒芳说:“我宁肯在上面多等几分钟的红灯,也决不敢到下面拿生命开玩笑。”
9月10日晚,一个名叫张涛的安徽青年在这里将一对消夏的上海情侣推下护城河,抓起两个放在一边的手包逃跑时被埋伏的警察抓获。手包里有两个手机、一个BP机、2000元现金和37000元的转账支票。安定门派出所的杨力警司告诉记者,这个张涛就是老百姓闻声色变的“绿裤子”,“为了抓住这个恶棍,我们的4位民警,8位联防队员在护城河边蹲了四五宿。”
距杨力所在的派出所不远处还有一个公安部门——北京市盗抢机动车证明办公室,尽管坐落于胡同深处,每一开门却总是人来人往。一位在门口排队登记的中年人苦笑着告诉记者,他们公司两个月前刚买了3辆桑塔纳2000,开回来头一天就丢了两辆,到现在既没追回,保险公司也不赔偿,公司老总一看见那辆幸免于难的桑塔纳就“运气”。
“我们派出所管片方圆1.5平方公里,100名干警、联防队员每天都在这个豆腐块里疲于奔命”,杨力有点苦恼地说,“可老百姓却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白天怕被偷,夜里怕被抢。”杨力和他的同事们每天的日常工作一个是从早到晚地巡逻,一个是不厌其烦地告诉居民们一些基本的但却行之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房门要安防盗门、防撬锁,人走时要关紧窗户,家里不要放大量现金,午夜以后妇女儿童尽可能不要出门。但他们无可奈何地发现,治安案件仍然层出不穷,防不胜防。“我深深地理解群众的恐惧心理,”杨力说。
据透露,新的一轮秋季严打已于8月20日全面展开。这次严打虽不如以往声势浩大,轰轰烈烈,其针对性和力度之大却是显而易见的。执法部门承认,“近一个时期以来”,故意杀人、流窜抢劫、故意伤害等重大恶性刑事案件与日俱增。8月14日和9月16日,北京市分两批集中处决了18名杀人、抢劫犯。在广东,从6月份开始提前进行的严打斗争已破案27000多起,打掉犯罪团伙6000多个,抓获犯罪分子近3万人。
安全感的危机可以因为一批罪大恶极的凶犯被逮捕、处决而有所缓解,但另一方面也说明15年来“杀一儆百”的严打威慑并没有使犯罪本身收敛多少。“我们正在目睹建国以来的第5次犯罪高峰。”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学教授魏平雄说,这次高峰自1989年出现以来就一直没有下去,“更糟糕的是其质量,也就是恶性程度逐年上升,公开杀人、抢劫、强奸以及流窜作案、团伙作案、连续作案等对社会安定和公民安全危害极大的严重刑事犯罪是越来越猖獗。”1950年第一次犯罪高峰时,全国共发生刑事案51万起,而最近几年每年发案150多万起,其中重大恶性案件就有50多万起,比有据可查的1985年增加了六七倍。这组数据告诉了我们一个不祥的事实:目前全国每20秒发生一起刑事案件,每1分钟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
现代化进程中溜进来的讨厌的客人
按照犯罪学家们普遍认同的说法,本次犯罪高峰除“案件数量大、质量高”之外,至少还有4个值得关注的新特点:年轻化,组织化,流动化,智能化。
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犯罪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青少年犯罪的行为学。“50年代的中国曾有着无与伦比的青少年低犯罪率,”魏平雄说。1956年在整个犯罪总量中,只有18%是青少年犯罪,25岁以下的犯罪率只有万分之一。但最新公布的统计数字却表明,在全国发生的刑事案件中,约有70%是25岁以下的青少年所为,其犯罪率已超过3‰。在凶杀、抢劫、重伤、强奸和爆炸5类恶性暴力犯罪中,青少年平均占到70%左右,其中抢劫犯里青少年占80%以上;在吸毒者中,约有75%是青少年;在卖淫者中,又有70%以上在25岁以下。
与年轻化相伴而生的是犯罪低龄化,全国每年有15~20万越来越小的未成年人涉足凶杀、抢劫,其手段之残忍毫不逊色于成人犯罪。在北京所有18岁以下少年犯罪中,有创纪录的10.8%是13岁以下儿童所为。已经有报告说一些青少年犯罪团伙的平均年龄只有10岁,有的甚至幼小到7岁,以至于只能以“过错”来界定他们的残忍行为。
未成年的小孩子让我们感到害怕,这或许是世界上最令人恐惧的事情。在同样面临青少年犯罪高峰的美国,一些议员甚至建议把死刑年龄降低到11岁。这种以成人暴力对待少年甚至儿童暴力显然是怯懦和逃避责任的做法。年轻与暴力的结合说明新生一代正在社会边缘走得越来越远。至少孩子的父母、学校以及大众传媒应该对此负最大的责任。
年轻人往往将对伙伴的忠诚置于对长辈和社会主流规范的忠诚之上,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事实上,93.7%的犯罪团伙成员年龄在25岁以下,且半数在18岁以下。到1995年,中国已有这样的犯罪团伙二十多万个。另一个相关数据是全国60%~75%的犯罪属于社会危害性很大的团伙犯罪。更令人震惊的是,公安机关已经承认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正在中国凸现出来。
同样成为新边缘群体的还有自农民工进城以来难以计数的流动人口。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及珠江三角洲,外来人口犯罪所占比例都在50%以上,其可怕之处就在于几乎无法防范。魏平雄和杨力不约而同地向记者指出,从50年代直到80年代,中国的城乡居民都在户口本、街道居委会和生产队强有力的社会控制下,农民进城和罪犯流窜作案几乎寸步难行。魏平雄打了一个恰当的比喻:“流动人口犯罪比例的剧增可以看作是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溜进来的讨厌的客人。”
正如每次犯罪高峰都紧随某一重大社会震荡而至一样,犯罪活动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革气息相闻。当新技术革命将我们导引进入信息时代的时候,以计算机犯罪为代表的一些新型智能化犯罪形态也应运而生。对此最心惊胆寒的莫过于那些率先实现办公自动化,将机密数据信息存入计算机网络系统的部门和公司,不仅顷刻之间损失惨重,而且事后也大多不敢声张。开放式的因特网络为高智商的犯罪分子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以通过破坏银行信息系统进行盗窃为例,国外研究表明,犯罪分子每次只需千分之一秒到百万分之一秒的作案时间,即可得赃款25万美元,被抓获的可能性只有2%;而传统的抢银行每次只能得到3551美元,行抢者入狱的可能性高达82%。正如日本计算机犯罪专家鸟居壮行所说:“现在几乎没有一种手段能像计算机犯罪那样轻而易举地获取巨额财富。”
依靠我们自己的安全
遏制犯罪、打击犯罪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共同课题。自1983年我国进入第四次犯罪高峰起,“严打”的利剑频频祭起,一大批民愤极大的犯罪分子受到了从快从严的惩处,群众拍手叫好。但许多行业人士也指出,不能仅仅寄希望于每年搞一两次集中严打。“安全感靠打是打不出来的,严打只是在一个短期内缓解社会治安的办法。”安定门派出所的杨力说,“打防并举才是既治标又治本的根本途径。”
“5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那一段夜不闭户、每年发案不超过20万起的‘太平盛世’呢?”魏平雄自问自答道,“关键是有两点保障,一是有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有完善的尽职尽责的基层组织,二是社会风气好,群众集体主义道德观念强。”魏平雄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要遏制犯罪就必须加强社会控制。50年代所倡导的阶级斗争、群众专政固然降低了刑事发案率,但事实上也使处于严密控制之下的每一位社会成员人人自危。“我只是深切地感受到,”魏平雄说,“群防群治作为一种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行之有效的战略思想在今天也应被视为根本大计。”
与魏平雄是同一代人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冯锐也向记者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像50年代那样大搞人民战争当然不可取,但只要每个部门都恪尽职守,每一位公民都以保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为已任,大部分犯罪在萌芽时期就可以被消解掉。”但目前的现实是许多环节都给犯罪留下了空档,冯锐强调,遏制犯罪并不仅仅是执法机关的责任,也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不履行这个义务也是玩忽职守”。
犯罪危及每个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对于这一点,人们毋庸置疑会感到恐惧,但更致命的是怯懦和心存侥幸。“安全感关乎我们自身,”冯锐说,“也必须依靠我们自身去获得。”
建国以来的5次犯罪高峰
第1次:1950年出现,全年发案51.3万件。反革命破坏案和旧社会遗留的犯罪较多。夏秋两季,有近四万名干部群众被杀。10月10日发布镇压反革命的“双十决定”,同时缉捕盗匪,禁绝烟毒,取缔妓院,收容游民,翌年犯罪率即大幅回落。
第2次:1961年出现,全年发案43万余件,比上一年增长一倍多。盗窃案占81%。3年自然灾害是本次高峰的直接动因。1962年开始迅速回落。
第3次:发生在1973年,并一直持续到1977年。发案数一直维持在50~53万件。打砸抢等政治性案件较多,普通刑事案件中,强奸案是建国以来历次高峰中最多的。本次高峰没有回落。
第4次:1981年发案87万起,1982年78万起。1983年出现“二王”、“唐山百人菜刀队”、“上海控江路千人围观强奸事件”等恶性案件。同年8月第1次“严打”。1984年发案数降至50多万起。本次高峰出现较为松散的团伙犯罪,青少年犯罪开始超过半数。
第5次:从1989年至今。1989年发案170多万起,1990年升至230多万起。此后立案标准提高,发案数徘徊于150万起左右,但恶性案件增至50多万起。 杨力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