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六号彩虹》到《白鹤亮翅》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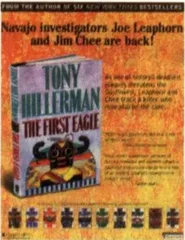
汤姆·克兰西擅写紧张行动环环相扣的小说。此次在《第六号彩虹》一书开篇的十页中就已经把读者带入了难以释卷的情节之中:一次早有预谋的劫机事件被行家迅速挫败。出手的人就是作家笔下常见的英雄之一:前中央情报局特工约翰·克拉克——他刚好乘那架飞机前往英国,准备组织一支多国反恐怖主义特种部队,其代号即称“第六号彩虹”。
事有凑巧,就在这支特种部队即将准备就绪之时,横跨欧洲爆发了一系列事件:在瑞士发生了一次抢劫银行案,在奥地利有一件试图绑架案,在西班牙的一家游乐园出现了一次袭击。显然,这些卑鄙的罪行无一能由当地军警力量单独处理,于是,克拉克的这支全部由武器专家、神枪手和全能勇士组成的影子部队,便纷纷出动,力挽狂澜。就在“第六号彩虹”的艰苦训练和振奋人心的活动中,揭开了一件更大的罪行:铁证表明,有一个恶毒的阴谋要发动一场生物战争让全世界传遍致命的病毒。那伙坏家伙与一名前克格勃特工联系,利用恐怖主义袭击手段达到他们自己的邪恶目的,准备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大干一场。
评家认为,克兰西先生在撰写此书前曾对有关资料进行过认真研究,他的情节也设计得很仔细,尽管他所写的阴谋有些牵强。当然,在他强调拯救地球时,并非指的臭氧层和濒临灭绝的物种,而是恐怖主义的危险,就该书而论,倒也写得顺理成章。主要的缺点还是篇幅太长,没有以精取胜。
托尼·西拉门已发表的十多部作品中曾有六部荣登《纽约时报书评》畅销书榜。他的惊险小说中均以乔·李普霍恩(Joe Leaphorn)和吉姆·齐(Jim Chee)这两位警探为主人公。作家这部新作《第一鹰》故事发生的地点完全在美国西南部的那伐鹤(纳瓦霍)居留地。那伐鹤本是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与阿帕契人是近亲。他们早在10世纪时就已在今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一带定居,向普韦希洛人(他们那种梯形多层平顶的城堡式结构的村落遗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点,笔者曾前往参观)学会了农耕、纺织和砂画等技艺,17世纪西班牙人入侵后,被迫转入以畜牧业为主。1868年起,被美国政府限定在居留地内。他们的文化有独具一格的神话和宗教色彩,手工艺制品以绘画、银器和地毯著称。西拉门在《第一鹰》中,借助一种古老的瘟疫复发的情节,把那伐鹤人传统和现代文化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为一部侦探小说增添了神话氛围,让读者随着两位警探追逐杀手的同时,也走进了历史。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开拓。
在笔者翻阅新书资料时,发现了一部叫作《白鹤亮翅》(Crane Spreads Wings)的小说。再一细看,果然是借助了太极拳中的一个招式为书名。原来作者想用这一书名既表现主人公对平和心态的向往和实践,又象征她对自由的追求。然而小说还有一个副标题,叫作《一个重婚者的故事》(A Bigamist's Story)。这就奇怪了,如果说重婚者追求自由尚可勉强,又如何能达到内心平静呢?说起来这正是作家的巧妙之处。
苏珊·特罗特(Susan Trott)此前已发表过11部小说,从中掌握了高超的刻画人物的技巧。她能通过简短的对话,勾勒出一个次要人物的性格,当然在有充分篇幅展开主要人物的各个侧面和深入内心分析时更显得从容不迫。至于本书,她用了喜剧手法——这使我们想起了《一仆二主》那部经典喜剧——来探讨在纷扰的当代美国如何达到平和的精神境界问题。重婚一语虽然在法律上可以立案定罪,但在现实生活和艺术作品中却不乏婚外恋的情人关系,这在美国恐怕更是事实。《白鹤亮翅》中的女主人公艾菲·克拉克尔比在开篇中即离开了她的新婚丈夫阿兰。阿兰是哈佛的年轻教授,夸夸其谈,他告诉妻子他正在写一部小说,却使艾菲确信他在吹牛。她已经无法忍受,便准备到旧金山完成她的艺术史博士论文并练习太极拳。
艾菲在波士顿的哈佛俱乐部小饮时,遇到了离婚不久的飞行员格莱德。格莱德误以为她是应聘来照看他8岁儿子丹迪的保姆。艾菲将错就错,却发现格莱德居住的小区就是她刚刚离开,而且她丈夫仍在住着的地方。
阿兰想让艾菲回到自己身边,而格莱德却爱上了她。艾菲虽然反对欺骗,却是个文饰专家。她向两个男人都隐瞒了另一个的存在,而且在未和原夫解除婚约的情况下与格莱德成了婚。种种笑料由此产生,如她怀了孕,却不知道孩子是哪个丈夫的。由于两边都有些亲属出场,就把事情搅得更复杂,也更乱套了。
作家当然不是为了逗读者发笑,当女主人公叙述这个故事时,虽有大胆冒险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冷静的思考,她在练习太极拳时(从书中描写来看,作者还是懂一点的),逐渐体会着心境平和的道理。可见,小说的正题是深意所在,而副题只是“借题发挥”。
性道德之悲哀景象
40岁的米歇尔·胡艾勒贝克是法国文化界的名人。他1985年创办《垂线》杂志,率先开始批评自由主义,1994年出版《斗争领域的延伸》,被视为研究68年人思想的必读书,今年9月,他的又一部小说《基本元素》一出版销量就非常可观,两周之后即成畅销书榜的冠军。法国各媒体对这部作品都非常关注,且态度迥异。《读书》杂志登了6个页码的作者访谈,对他赞许有加,《解放报》一篇书评则骂这本小说是夏季休假结束后的文坛败笔,就像环法自行车赛中的违禁药品一样,《星期四事件》同样采访了作者,同时设坛辩论,正方反方都把意见说了个够。
《基本元素》里面的故事其实很简单。胡艾勒贝克描写了布鲁诺和米歇尔两兄弟的生活(主要是性生活)经历,借此追述并探讨1950年以来西方社会性道德的变迁发展。布鲁诺除了性什么也不想,他在小说中代表的就是性欲;米歇尔完全忽视性的存在,他代表的是缺乏性欲。布鲁诺受的是文学教育,米歇尔则是理工科出身。
布鲁诺活得很下贱,胡艾勒贝克说他写这个人物遵循的是下列原则,“把手指放在伤口上,用力按。挖掘那些所有人都不想听的话题。展示布景的背面。坚持谈论疾病、焦虑和丑陋、嫉妒、冷漠、受挫折、不去爱。下贱吧,下贱的时候你是真实的。”
作者承认,对于初学写作的人,“下贱”是真实的方式之一。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米歇尔不懂得爱,连接受爱都花了很长时间。但是他在研究方面的兴趣让他慢慢有了许多关于生命的最基本领悟,作者说,他代表的是“对认知的欲望,这种欲望与寻常的欲望完全不同”。
真正引起人们争议的还不是胡艾勒贝克写出的内容,而是他写这些内容的方法。他写作那些感性人物就像对待科技问题,完全是做实验性的技术处理。他在接受《读书》的记者采访时说过:“现在还有谁谈灵魂?20世纪是科学的胜利,以后要解释某种人类行为,只要列出一个荷尔蒙和神经元的清单就行了。”
胡艾勒贝克还有其他一系列引人争议的想法。他赞成克隆人类,反伊斯兰教,公开说种族主义不是个问题,认为传统价值丧失殆尽后东方已经彻底堕落,应该彻底清除欲望;还说人类应该被某个新的物种完全取代。(刘芳) 小说艾菲白鹤亮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