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社会与性骚扰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高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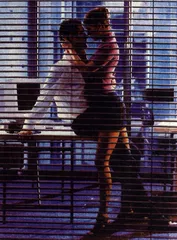
“受害者们还都是心存侥幸地默默忍受”
7月份以来,恰逢刚刚在访华之行风光无限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被莱文斯基一条蓝色连衣裙弄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有关性骚扰的话题在中国也突然沸沸扬扬起来。而在此之前,这类话题一直被视为禁忌。
捅破窗户纸的是江西省人大副主任陈癸尊。新华社7月5日援引这位全国人大常委的话说:“中国需要惩罚性骚扰和对异性滥用职权的法律。”
陈癸尊是在参加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时说的这番话。他指出,医生以看病为名对女病人进行性骚扰已成为当前日益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由于中国人历来对性采取保守的态度,最常见的情况是,许多妇女在受到性骚扰后从来不敢声张”。因此,陈癸尊建议,在《医师法》中增加禁止和处罚“利用职务之便对异性进行调戏、性骚扰、侮辱病人行为”的条款。
“性骚扰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医疗过程中,还广泛地存在于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陈癸尊进一步补充道,“事实上,利用职权来猥亵女性或对异性举止放肆都属于犯罪,应该受到惩罚。”他提出,有关立法既可以是不同领域的不同法律里增加相应的反性骚扰条款,也可以单独制订一部《反性骚扰法》。据陈癸尊介绍,他的提议当时就得到了许多在场人大常委的支持与赞同。
来自立法部门对性骚扰问题的关注无疑是十分耐人寻味的。3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一位名叫唐灿的女学者首次披露国内性骚扰状况的论文由香港报纸转载后,曾被有关部门视为有损安定团结和国家形象的“毒草”,作者被迫连写了四五份检查。全国妇联权益部部长丁露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这次陈癸尊等人大常委的呼吁表示欢迎,并承认如今各地妇联组织收到女同胞这方面的投诉日益增多,性骚扰已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社会问题”。这位负责人还提到,旧《刑法》中有流氓罪这样一个中国式的判定,但去年修订时取消了这一罪名,新《刑法》没有对性骚扰作出任何条文规定,这个遗漏使许多骚扰者逍遥法外,她希望有关法律能尽早制订和实施。
尽管每个人都指出性骚扰已经“相当普遍”、“相当严重”了。但至今仍没有一个相应的统计数字浮出水面。据北京市妇女研究所王行娟所长介绍,北京妇女热线自1992年开通以来,每年接到的有关性骚扰的咨询约只占全年咨询电话总数的1%。而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登记的所有律师事务所的统计资料中,找不到任何一例此类案件。“这说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妇女对性骚扰仍讳莫如深,”中国妇女研究所妇女权益研究室主任刘伯红说,由于性骚扰往往并没有造成被强奸的后果,“受害者们还都是心存侥幸地默默忍受”。
“自妇女离开家庭出来工作,性骚扰就成了工作场所的固定节目。”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讳忌和忽视,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性骚扰至今仍停留于“只知其名”,对其含义的认识和界定存在诸多误解、偏差。事实上,国际上对性骚扰的定义也是五花八门。美国联邦政府的平等就业委员会1980年所给出的解释最为拗口,也最为权威:
“在下列3种情况下,向对方作出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行为、要求,及其他语言举动,均会构成性骚扰:
1.迫使对方接受有关行为,作为受雇或就学等的明显或隐蔽的条件;
2.对方接受有关行为与否,将成为影响个人升迁或学业、健康的先决条件;
3.有关行为可导致不良后果。”
一些学者则更为简短地把性骚扰表述为“通过语言、身体接触及暴露性器官等性行为滥用权力,在工作场所、学校、法院和其他公共领域欺凌、威胁、恐吓、控制或腐蚀其他人。”“不管怎么定义,性骚扰都与我们平常说的耍流氓有很大出入。”刘伯红说,“性骚扰更多是指领导、老板对下属、雇员等弱势个体的性要挟和性侵犯。”而几乎就在陈癸尊提出性骚扰立法的同时,美国最高法院又作出裁决,判定性骚扰是“根据上司所做出的丑恶行为”,雇员不必证明因为拒绝骚扰而受到在加薪、任命和提升上的惩罚报复。
尽管性骚扰的事实在古今中外都屡见不鲜,但直到1980年,美国才进行首次大规模社会调查,结论是42%的职业妇女自述受到过各种形式的性骚扰。“自妇女离开家庭出来工作,性骚扰就成了工作场所的固定节目。”著名女权主义者、法律教授麦金农愤怒地控诉道。
麦金农教授是率先向这股泛滥的社会潜流挑战的学者。1977年,在审理一起女职员为保住工作而不得不屈服于上司无理要求的案件时,麦金农成功地说服哥伦比亚上诉法庭作出“性骚扰就是犯罪”的判决。1986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性骚扰触犯了1964年民权法案。随后几年,许多国家起而效仿。
这个迟到的判决得益于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和运动中诞生的一个著名的口号:个人的也是政治的。当妇女的平等就业权利得到法律保护后,威胁到妇女尊严、生理、心理和职业机会的性骚扰问题就凸现出来,从个人麻烦提升为一种社会公共问题。女权主义者们坚决反对男权社会中性骚扰是因为男人控制不住自己性欲的说法,她们认为,这种行为同从经济和就业上的打击一样,传递给妇女的信息是,要服从老板、顾客、男性同事等等的个人幻想。美国社会学家伊恩·罗伯逊在《社会学》一书中也进一步解释说,性骚扰本质上是垄断着权力的男人们利用优势放纵他们的自我,“并重申他们认为女人的作用就是使男人满足的观点”。
应该说,被界定为性别歧视和侵犯人权的性骚扰在美国这个看重个人权利的国度里还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许多大公司规定,在办公室里放置裸体照片或黄色书籍,在公共场合说脏话,开带“色”的玩笑,老板亲热地拍打抚摸异性、同性属下的脊背或长时间握手都可能被视为性骚扰而遭到指控。安托荷学院(Antioch College)干脆这样教导每个行将毕业的男学生:“由于任何勇敢和主动均可能造成误解和麻烦,因此在进行每一步前,你都必须征求她的意见……如果你想抓住她的手,你必须先征求她的意见。如果你想脱掉她的上衣,你必须征求她的意见。如果你想触摸她的乳房,你必须问她同意不同意……”校方认为,这样一种制度虽然减少了性接触中的嬉戏和自发乐趣,但毕竟使得双方对性活动的责任更加平等,在这样一种制度下,“没有一个女人能说她是被迫的,她的意愿被忽视了”。
但是,法律的公正并没有带来事实的公正。美国心理学家路易斯·F·菲茨拉德最近对职业妇女的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妇女在工作中遭到过性骚扰,这个比例比1980年还略有提高。过去5年来,美国性骚扰案的数量翻了一番,但审结率却停滞不前。由于性骚扰很难找到旁证,对骚扰和示爱的界定也十分困难,大公司平均要花费670万美元用于性骚扰案投诉的调查、辩护或诉讼费,被骚扰者的律师代理费平均高达15万美元,以至于大多数受害者最后不得不撤诉了事。菲茨拉德颇为无奈地指出:“目前公正都无法保障,更不要想真正的平等了。”
“男权社会里没有避难所”
反性骚扰在其“原产地”的尴尬境地也在中国人的心中画上了一个大问号,以至于许多人认为,中国早已实现了同工同酬、男女平等,妇女状况要比每6分钟发生一次强奸案的美国强多了,因此立法惩罚性骚扰“时机并不成熟”,显得有些小题大做。中国政法大学巫昌祯教授就明确对立法持否定态度。她认为,目前大量的拐卖妇女、强奸、家庭暴力等显层犯罪行为尚得不到有效遏制,性骚扰这样一个“仅限于精神损害而没有任何实质性伤害”的问题,还不到立法的阶段。
很难说有多少人同意这种观点,但他们显然高估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中国从封建社会以来恐怕就算得上是世界上妇女状况最为低下的国家了。”中国妇女研究所刘伯红女士指出,尽管建国以来性别秩序有了较大改善,在全部就业人口中女性占到44.96%,甚至超过了美国,但绝大多数处于低职业结构,全国八大职业类别中,服务行业是唯一女性超过男人的领域。“更严重的是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刚有提升的妇女社会地位面临又一次失落,”刘伯红认为,随着大量女工下岗,面临性别歧视和阶层歧视双重压力,性骚扰必呈甚嚣尘上之势。更深刻的是,许多中国女性已习惯了男性权力中心,习惯了男性对女性的不尊重,并不意识到周围男性的某些行为实际已对她形成了性骚扰。
中国的性骚扰现象实质非常严重,率先研究性骚扰的中国社科院唐灿女士对此也有同感。1994年唐灿曾到广东进行问卷调查,她发现,36.8%的打工妹承认遭遇过性骚扰,对这些被损害者来说,性骚扰与性别歧视和身份歧视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近几年席卷全国的下岗浪潮中,女性占到下岗职工的2/3,而据全国总工会对660多家企业负责人调查,只有5.3%的人愿招女工。从女性在黑暗中以出卖肉体做交换,到流行在外企白领中“如何博着上司欢心”的“办公室秘籍”,再到美女充斥的各类广告,唐灿认为,性骚扰只是中国女性问题中露出水面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商业竞争时代,“妇女作为弱势群体正被推向边缘化和不平等地位。”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当着女性的面说几句黄色笑话实在是无伤大雅,这说明诱发性骚扰的性别歧视还深深扎根在人们心中。尤其在男权社会里,男女平等从思想和观念上的实现都仍然遥遥无期。当妇女越来越被物化为商品的今天,恐怕很难找到真正理想的避难所。 陈癸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