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能否点石成金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任波)
点石成金
前不久,英特尔集团总裁安迪·葛洛夫来到中国。《财富》杂志派出的随行记者记录了他在中国5天受到的种种礼遇,“在上海,英特尔的员工简直把他当作了一位摇滚明星”,8月17日的《财富》在封面故事里这样写道。
英特尔集团在《财富》杂志八月公布的1998年全球500家大企业中利润收益名列第四,1997年达69.4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7%,是大企业中的佼佼者。葛洛夫在中国受到的礼遇无疑显示了迅速崛起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深远影响,这正是知识经济时代的象征。
目前,世界各地过去最平静的大学校园,都在加速与商业化接轨。据估计,以剑桥大学为中心的英国剑桥地区已有1200个高新技术企业,涉及的领域集中在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大批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从校园走向公司,许多教师身兼数职。这与美国硅谷的风气一脉相承。在中国,我们也不难发现同样的苗头——校办企业正越来越红火。北京的北大方正、清华同方,天津的天大天财都创下了骄人的业绩。在依傍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中关村地区,地价一涨再涨。这些企业的经营之道,都在于“靠知识发财”,这些新兴的企业正呈现出与传统企业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以电脑业为例,它仅用了二三十年的短暂时间,就一跃成为美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1997年全美整个行业的生产总值高达7000亿美元。
知识资本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物质资本的投入。与制造业不同,新兴的大大小小的企业以更少的资源消耗,换取更多的产品附加值。与标志着工业经济的大规模的工人劳动不同,现在的许多企业白领比例已高于蓝领工人。“一个好的科研人员抵得上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普通工人”,一位企业的总裁表示。除此之外,科技创新还优化了生产过程中各项资源的配置,提高了生产效率。不同于以往,一个企业形成规模所必须的资本积累现在不再起决定性作用。大量风险资本更倾向于与知识资本结合。一些投资者说:“不怕没钱,就怕没有好项目。”
制造业的老牌富翁们与工业经济紧密相连,他们往往让人们联想起几代人薪火相传的家族式经营,而新一代的富翁只拥有短暂的发家史。如果说前者的聚敛生涯像一种滚雪球的游戏,那么关于后者,新兴产业的迅速扩张,仿佛用了一种点石成金的法术。
黑箱中的秘密
1998年7月20日,《北京青年报》报道,由国家国资局授权的湖南四达资产评估事务所正式认定,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袁隆平”品牌价值为1008.9亿元人民币。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无形资产评估价值额最大的一宗项目,“袁隆平”成为中国第一品牌。
袁隆平是世界级的科学家,他对世界粮食生产作出的贡献值得载入历史,但他长期以来几乎是默默无闻。此次“袁隆平”品牌未经媒体包装、广告宣传而以1000亿元高价脱颖而出,这典型地传递出知识经济到来的信息,而同时也不免令人生出疑问,这1000亿作为无形资产有没有实际意义?
当然有。
自从1984年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颁布,我国就已开始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定义无形资产的财产地位。之后,立法部门对商标和著作权也在这方面制定了明确的法律规范。知识无形,却有产权。
顾名思义,有形资产有获取成本,在账目上有相应的记录;然而无形资产,在未发生产权变动的情况下,其实际价值在账面上无法表现。以立法方式承认知识产权,是因为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一样,都能创造价值。

袁隆平(左)被称为中国的“水稻之父”(新华社)
在美国,目前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的无形资产比例已高达50%~60%,知识作为资本投入企业创造了新的财富生长点,而知识资本的特殊性又成为新增财富得以迅速膨胀的源泉。
1997年,美国的“探路者”号登上火星,给人们带回了5倍于21年前发射的“海盗”号的信息,而全部成本却只花了1.8亿美元,小于“海盗号”10亿美元总成本的1/5。消耗减少,效益增加,科技知识的新投入,直接对应于大笔钞票。在生产领域,无形资产最终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把创造价值的生产过程置于“黑箱”,黑箱甲代表常规生产过程,在黑箱乙中向常规生产过程追加知识资本,那么,当同样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要素通过,在乙的出口将会涌流出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大大超过甲的产品,而所用的时间却缩短了。
黑箱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说是知识资本所具有的价值源源不断地附着到了产品之上,那么,探究知识资本的真实价值就作为一个难题摆在了人们面前。在具体操作中,不同类别的无形资产价值的生成方式有很大区别,但知识资本的价值,在动态环境中,常常以它带来的收益来度量。这可用以下公式来表述:某知识资本价值=企业价值-全部固定资产价值-全部流动资产价值-全部流动资产价值-其他无形资产价值。其中企业价值等于企业的长期债务与股票价值之和。当然,实际的评估远不止于此。
对于知识资本作用的方式,一些经济学家的解释是,把知识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对于在大规模生产中,适用于所有常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金和劳力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相对成本递增规律,它具有一种抵销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节约投入,使成本递减;一方面,它能够增加产出,使收益递增。
从哈罗德开始,西方经济学家们纷纷以自己的方式列出生产函数,试图以经济模型,把科学技术通过企业这架物化机器对生产力的提高作用用更为理性的数学关系表述出来。结合我国的国情,国内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知识就是金钱”说起来容易,然而要真正看透这个点石成金的法术绝非易事。也许,把黑箱中神秘的运行机理以科学的方式彻底揭晓仍有待时日。不过,即使是在无数的身边小事中,人们也能真切地感受到知识的力量,与土地、资金及劳力相比,它的确大不相同。
没有泡沫就没有啤酒
然而,实际情况更为复杂。
1994年,网景公司上市,在一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间里收进20亿美元,一跃跻身大公司的行列。
1998年,网景公司在与微软公司的浏览器之争中失利,股价一落千丈。
对于捉摸不定的股票市场而言,这只不过是件寻常事,但对关注信息行业的人而言,这无疑是件大事。在新兴产业在股市上告捷之声频频传来之际,人们也会思忖,作为经营状况的晴雨表,股价的升贬与公司业绩是否对称呢?
事实上,股票的市价除了取决于企业当前的盈利值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人们对企业未来盈利的预期值。假设贴现率为10%,有一种发行面值为1元的股票,第二年每股盈利为0.80元,那么它的面值盈利率就是80%,除掉每股分配现金股息0.1元,余下的0.7元全部充作公积金和保留利润,代入公式:股票的价格=每股面值×面值盈利率/贴现率,于是下一年的股票价格应为(1+0.7)×80%/10%=13.6元。然而如果保持80%资金盈利率的预期时间为5年,那么股价就不会停止在13.6元这一价位,而是升至(1+0.7)5×80%/10%=113.59元了。当人们对企业盈利状况作悲观的预期时,结果就正好与此相反。对市场的心理预期有如浮在啤酒上的泡沫,它对股价涨跌的倍增作用模糊了企业的真实价值。
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在以市场收益作为确定无形资产价值的根据时,人们必然地需要对收益量和获利期等关键因素进行预测,而市场动态瞬息万变,未来的不确定性总是预示着种种风险。一旦价值部分掺入预期的因素,泡沫也随之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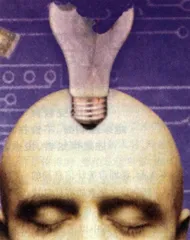
对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价值的预期值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人们对整个企业经营前途乃至整个市场景气程度的预期值,泡沫有可能交替出现。
“没有泡沫就没有啤酒”,国内一位知名学者在谈及亚洲的金融危机时指出,“既定的市场体系决定经济泡沫必然存在,但泡沫只有在堆积到一定程度时才对经济产生危害。”
在美国,自1982年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累计实际收益已达825%,超过2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730%还要多。而最近的购并狂潮和资产市场也纷纷显露出“起泡”的迹象。
关注股市,高科技股票成为股市连续三年攀升的驱动力,即使在去年10月27日的股市风潮之后,德尔、康柏和朗讯的年增长率依然分别达到214%、112%和78%。这让人振奋。但实际上,去年10月底以来,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中的软件类指标股的市盈率下跌了26.5%,而电信设备类指标股的市盈率则跌去近一半。
然而人们在牛市疯狂买入,在熊市疯狂卖出的那股不变的劲头似乎总能成为一种极易蔓延的力量。没有泡沫,啤酒就不好喝,可是任凭泡沫堆积,会不会喝不到啤酒?在新兴产业陆续登场之际,人们所要做的,除了紧盯银行利率、货币汇率、公司收益、政策倾向、投资者的行动这些关键变量之外,也许还有些别的。 袁隆平股票知识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