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走向新世纪始终不能忘记农村的发展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罗峪平 摄影 符建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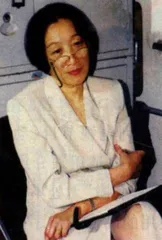
罗:20年前,中国改革从农村发端。现在农村情况如何?有人担心剩余劳动力和经济增长较慢会使农民对现状产生不满。
卢: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往往是被遗忘的角落,或者是被侵害的部分。只有改革开放的近20年中,农村才真正开始现代化。应该说,农村目前情况是建国以来,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
农村现代化至少需要两个条件:市场经济体制和外部经济增长的大环境。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几百年前,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开始发展,但它始终没有给农村带来现代化。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它给农村带来的只是不计劳动成本的过度竞争。从清朝后期的洋务运动,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到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国农村不仅得到的利益很小,原有的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结合的状态也受到破坏。建国以来,政府是有计划、有系统地从农村提取生产剩余。
罗:最近《百年潮》杂志上刊登的万里同志回忆农村改革的文章,也提到建国以后政府对农村实行的政策,“甚至是对农民的一种剥夺”。这种做法是大多数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的必经阶段,还是计划经济国家的特征?
卢:恐怕是后者。尤其中国这样历史上的农业国家,要工业化,除了从农村,还能从哪里找经济积累呢?当然,体制有很大问题。当时农民是交了公粮还得卖余粮,政府以很低的价格收购,把农民生存线以上的东西全拿走了。我们是社会主义,人人有生存权,所以,赖以生存的口粮在生产队是平均分配的。有多少个孩子,有多少人头,就有多少口粮。没有钱可以赊欠,时间长了可以不还。这样,形成破坏劳动积极性的机制。干活的人吃亏,谁还会有积极性?
如果说改革之初,农村经济的恢复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在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国民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对农村的作用更加重要。农产品有人要,剩余劳动力有地方去,乡镇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大背景,使中国农民第一次分享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好处。
外部经济增长的大环境,必须有农业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市场体制与其相适应。原来华国锋对搞家庭承包制的担心主要是农业机械没法使用。但20年后,我们看到市场经济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年麦收期间,机械收麦队没用政府补贴,就到处开花。收割机的机务市场使得小规模分散的农户经营和大型农机作业协调起来。在市场化条件下,过去认为只有政府和集体能办的事,例如水利设施,现在交由农民个人去办,他们能够办得很好。由于在市场上可以交换,产生利润,农民有很大积极性增加投资。川东地区把水塘承包给农户,他们不仅把过去十几年中过度使用和损毁的窟窿补回来,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也比原来有效和节省。
总结过去20年的经验,我们必须坚持农村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目前需要特别留意电力、交通、电信等公共部门和垄断性的商业组织,由于改革的滞后,它们正在妨碍农村经济与整个国民经济的连结,并阻碍农村经济增长。
罗: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到今天是加快还是放慢了?改革将如何深入发展?西方人对我国农村进行的民主选举非常注意,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卢: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尤其现在国有企业要进行改造,这种大环境会对农村产生影响。以前的改革是增量改革,特点是非国有部门的增长不断鼓励改革,改革又促进了这些部门的增长。从1994年开始的宏观改革到今年国有企业、银行、住房、社会保障的改革是存量改革,它带来的不同后果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可能不仅没有增长,还会有负面效应。老百姓不得不多存钱来保护自己在未来生活中的基本需要和安全。乡镇企业改成股份制也好,股份合作制也好。改制后的企业家们的主要兴趣会集中在降低成本,增加盈利。为了要挣出购买企业的钱,他们短期内不会扩大生产规模,像前几年一样去努力争夺市场份额。
1978~1985年城乡收入的差距是缩小的,从1985年起扩大。1989年到1991年农民收入增长基本停滞,城乡收入差距又回复到1978年以前的情况。1993年以来农村收入的增长较快,是由于国家提高粮食价格,乡镇企业增长快,外出人口打工收入增长等原因。现在,这种情况可能会有转折。1997年,农村外出打工人数不再增长。今年城市下岗职工的人数可能会达到2000万。城市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矛盾会进一步扩大。现在大连等城市提出下岗职工不挑不捡三天保证上岗,实际上就是把农村的人赶回去。
乡镇企业发展环境会比原来严峻得多。国有银行现在要承担信贷责任,但评估能力又不足。为避免风险,减少呆、坏账,银行宁肯少贷款。乡镇企业转制以后,如果没有一个较好的资金市场支持,发展起来就有困难。更不要说现在整个市场过剩,许多商品都难以出售。
农产品销售渠道不畅也是大问题。粮食系统改革可能会造成短期内粮食价格下降。因为虽然中央政府要求敞开收粮,但地方政府,尤其是产粮区的政府不会去大量补贴粮食收购,他们现在工资都发不出来,不会积极无偿为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的居民收粮存粮。所以,农民的收入从各个方面看都有下降的可能。
长期目标和短期后果的矛盾造成一些非常麻烦的事情,但这些麻烦如不尽早解决,将来麻烦会更大。用旧手段,还会造成旧的问题重新出现。比如说为了达到8%的增长速度,增加许多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投资是否已经过度?高速路上到底有多少车在跑?再多的钱投下去,生产不增加,回报率很低,整个经济状况要恶化。所以政府要经济增长,就要解决许多和农村长期发展有关系的问题。要做麻烦事。
第一要解决根本制度问题,如土地制度。我们现在说30年不变。农民希望土地承包期稳定,但他们又希望人人有饭吃。30年之内新增人口是没有土地了,他们或者进城,或者在二级市场上去租赁土地。许多地方为了对付人口增长预先留出了机动田,对其采取招标承包的办法。对此,中央政府非常愤怒,朱镕基也批评农村干部把粮食价格上调的好处装进了自己口袋。农业部急急忙忙发文章说两田制不能搞。农业人口能够外出打工当然好,但如果不能怎么办?靠什么替代?我们至今没有在社会公平稳定和经济效率之间找到较好的解决办法。所以我说土地制度的问题并没有完。还有山林所有权,承包时按人头分下去,以后有人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兴趣经营。各地实行不同的转包措施,留下了不少隐患。此外乡镇企业改制问题,现在比强调防止集体财产流失,更重要的问题是强调合法产权,包括私有产权受到保护。变成股份制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不公正,但是一旦产权确定,其所有权和收益权就应该受到保护,这样才能有投资的积极性。
还有政策问题,如税收政策。1983年搞农林特产税,是为了平衡经济作物和粮食之间的收益差异,保证粮食生产。这个税由地方政府征收,所以被抓得很紧。像茶叶等产品现在看来税都太重。再比如林产品,生产环节中有8%的税,流通中还有8%,乡镇政府有提留,还有育林基金等等。林业部曾经做过个案调查,一棵树砍下来,经营者只能得到一至四成的收入,其他六至八成都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了,我们还坚持以粮为纲,希望在农业部门内部进行这种调整,以保证粮食生产,而没有看到大的格局——就是城乡收入差别还很大,想农民提高收入已经不能只靠粮食了。中国有限的耕地价值本身就很高,要使这些耕地运转得好,就要种植高附加值产品。耕地少,但荒山多,中国适宜育林的荒山荒坡有十四五亿亩。在国家不能用大笔钱鼓励向高附加值农产品和林产品投资的情况下,应该坚决把税砍下来。我们最近在做外商投资农业的调查,台湾投资者一般不是商人,是自耕农。他们异口同声地抱怨政府对农业没有帮助,抱怨他们不能得到贷款,抱怨税太重。这是因为他们在台湾地区是可以得到各种帮助和扶植的。
农村公共管理工作是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现在有了很好的开端,就是你说的村民直接选举。有领导人说,选举我们早就有,不是现在才搞,而西方有人认为是他们民主制度传播的结果,我觉得这两个说法都不对。农民的民主要求是经济发展本身带来的。我们在农村调查中看到他们公共管理的职能非常全面,有:管理集体财产,帮助提供发展机会,调解纠纷,维护治安,改善基础设施,维护道德标准,计划生育,以及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等等。现在土地价值上升,一亩地的价值可以到好几万。这种数量级的公共财产如何管理?以前村里的道路好不好,对农民来说是雨天路烂多换一双胶鞋,现在是自己的小卡车能不能开到家门口的问题。村民的矛盾和纠纷也会随着各种经济活动复杂和多样起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靠民主选举出来的,有合法性的村民委员会。
历届政府在农村的目标都是两重,一是促进农村发展,二是期望从农村获得一定税收。问题是真正实行起来,往往一边倒。当年国民党政府为了还美国人的债,为了打内战,在农村横征暴敛,抓丁拉夫,最后和农民的矛盾弄得非常尖锐,还不说基本制度,就说苛捐杂税,弄得农村任何现代化工作都无法进行,他们在农村最后只能用痞子和坏蛋来维持统治。村一级的保甲制度很黑暗。解放后,社会主义给农村带来重要变化,比如卫生院、小学校、合作医疗制度等等。但是我们在完成两重任务的时候,也出现过一边倒的情况,要钱、要人、要粮。政府强制性任务一多,下面干部为非作歹的事就多,好多坏事都是这么出来的。干部打死了农民,扒了农民的房子,大都是借口执行上级任务。所以,农村真正的民主自治制度要发展,必须大幅度减少政府的强制命令。
农村经济发展是有潜力的。问题是我们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尤其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始终不能忘记农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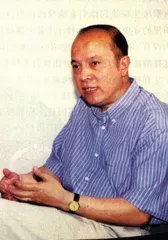
卢迈简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1982年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199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发表论文、研究报告等四十多篇。 经济三农农民农村改革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