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67)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许多 施武 唐波 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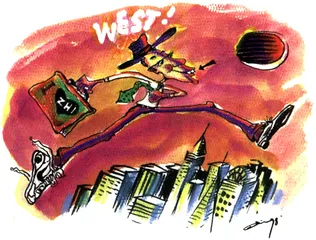
生活圆桌
我是小资
文 许多 图 王焱
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和一个女孩聊天,她装得有点玩世的样子,和我大谈最新的电影音乐还有畅销书,然后在话语里时不时加一两个英文单词。最神的是她常常自我嘲解道:我就是一个“雅皮”。我对“雅皮”这个词还不是太适应,因为,我习惯听“嬉皮”这种说法,就是那种特别随便和反抗一切世俗规范的人。她看我有点迟疑,就忙说,就是特别小资的那种人。我明白了,我开始感慨这世界变化快。我记得以前高中学课文的时候讲某某是个小资产阶级,就是讲他的思想觉悟不高,没有达到无产阶级的彻底的高度。分析课文的时候,我一听到哪个作者是小资产阶级作家,我就对他心存芥蒂,觉得他不够先进。
后来我就经常听到自我标榜有品位的青年男女对我说:我是个特别小资情调的人。满脸的洋洋得意,那自豪感就如60年代说自己是贫农、80年代说自己是个体户。他们说的小资情调就是追求生活品质的同时要关注文化,对,一定要显得有文化。比如,他们可以经常谈一谈最新的话剧或者画展,还有偶尔可以冒出一句特别后现代的诗,说这些话的同时一定还要在语调里掺杂一种嘲弄的意味,弄得自己特有文化鉴赏能力的样子。还有浪漫,小资的人最最喜欢标榜自己的浪漫,是那种都市化和形式化的浪漫,比如说“一起慢慢变老啊”,“隐居山林啊”,“出海漂泊啊”,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这样,所以就可以特别随便地说出来,说的时候满脸陶醉状……这时候最好还配有一点音乐,比如小资们最喜欢的肯·尼基的萨克斯风,然后他就可以说,这是他(或她)最喜欢的音乐了,因为特别有味道。
我发现面对小资的生活,我已经产生了无法抑制的亲和力,我想我肯定是马 上就抛弃了高中课文的观念,我觉得像我第二段里描写的生活方式真的很不错,但是小资的名字多少有点和我的传统习惯不同,所以一直也就没标榜自己活得小资。
有一天,我把高中的语文课本翻出来,猛地发现我喜欢的作家几乎都被定义为小资产阶级作家,而且我最景仰的卢梭竟然也是这号人物。我一下子就心理平衡了,小资原来是有文化有思想的表示,而且罗曼·罗兰说卢梭是个多情,好色,软弱,敏感,脆弱之类的角色,好像特别符合小资的要求,似乎和我性格有诸多相同之处。我终于心安理得地称自己是小资了。
偶像如太阳
施武
我崇拜维特根斯坦,不知是因为他的哲学,还是他的故事。多年前我从图书馆借到一本由他的学生写的小传记,那里记录了维特根斯坦的奇特人格,至今我记忆在心,许多琐事常使我试图引以为榜样,但是我不奇特,所以我做不到。比如他的房间之简陋,可能比现在的下岗工人还不如,只有一张行军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比下岗工人多的是一个存放手稿的保险柜。所有来访的学者或学生只能席地而坐。不是他没钱,他把钱都给人了。并且他不是出于慷慨,而是拿着钱他没用。这些我都做不到,摆在商店里的我的“生活必备”太多了,拼命工作后买回家的“生活必备”填满了房间的所有角落。而维特根斯坦死前能骄傲地说他过了幸福的一生,不知我能不能。
我太崇拜他了,就给图书馆赔了双倍的钱,把书留在了我的书架上。
我还崇拜Beatles,在大致了解了这个乐队的来龙去脉之后,就四处搜集有关的细枝末节。现在我知道他们各自的性格,尤其是列农的故事,从他妈到他老婆儿子查了个透。
我崇拜他们可以罗列出100个正儿八经的具有人文色彩的理由,因为有了这一重色彩我的崇拜就不俗。同时我也就有了100个理由不买明星传记来读,还因此瞧不起在地摊上买明星传记的人。就这样,我慢慢地读着大师们的传记,慢慢地发现不少人在读着不同的大师们的传记,甚至学者的日记。
当我读到一本学者的日记时,我觉得味道不对了。日记,自然记什么都可以,世事流变、一日三餐、朋党友人无不可记。可这些事跟我有什么相干?话说开来,维特根斯坦有几把椅子?为什么被任教的小学校赶走?列农怎么在印度修炼?这些又跟我有什么相干?所有传记、日记除了与他们的职业功绩相关的事,大部分是圈子内的私事或干脆就是个人私事(《顾准日记》除外,这里有不少历史资料性的文字)。圈内的事只与圈内人有关,再就是和崇拜者有关。如果我既不是圈内人又不崇拜他,读着就没意思。
天堂的玫瑰花是否有刺跟我无关,但是跟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有关,要让我参加讨论,我只好说爱有没有。文化人看着姑娘、小伙眼泪汪汪地追着某明星极为不屑,可也有人指出下了几年干校就资格倍增地写点受苦的事,而那点苦与广大底层的苦一比算个什么。那也挡不住崇拜者对他们那点苦津津乐道。
至于为什么一个人就崇拜了另一个人,100个理由之外,肯定与人私藏不露的内心弱点有点关系。前几天,《中国演员报》上登载了巩俐横卧床榻的大照片,一位研究神学的学者拿着这张报纸看了又看,最后发誓般说,如若能做巩俐的情人,他愿给她当牛做马,而他一向是爱默生的忠实崇拜者。这里没有点问题吗?其实没有,至少我没看出他虚伪或精神分裂。
无论是学者日记,还是明星轶闻,或我崇拜的维氏小传,走俏的理由都是因为崇拜者各取所需。偶像如太阳落下,明天会有新的太阳升起。
(本栏编辑:苗炜)
25岁以后的情趣
唐波
十七八岁吧——我年轻的时候(每次这么说总会招来嘘声一片,含意不详),高中毕业在一家旅游学校念书。或许是刚开放的缘故,特别喜欢奇装异服:红色的套头衫配紫色的条绒裤(裤子要特别宽大,迎风一吹活像战旗),脚蹬棕色高帮的圆头靴,原配的鞋带不要,找来粗细适中的麻绳把脚绑个结实。还有各式各样的藏饰(那时还没有仿制品,都是托人从拉萨八角街购回),琳琅满目地挂了一身,脚踝也不放过,系了一圈小铃铛,走路时叮当作响,我妈说还以为是哪家的狗回来了呢。
衣服都是自然面料的,全棉、全麻,有的连纽扣都没有,用些像是刚从牛身上割下来的细皮条、粗麻绳十字交叉地缝起来。走在街上回头率挺高,人家觉得古怪吧,我却很得意,处在一个希望引人注目的年纪。
那时没有扮COOL的说法,那时叫找感觉。
这感觉什么时候找不着了我没有确切的记忆,反正25岁那年,我发现好像在一夜之间柜子里全是套装、长大衣和高跟鞋。年轻时穿的衣服有的送人了,有的捐助灾区了,但大部分不翼而飞了。
如今是些什么衣服啊!化纤,尼龙,聚酯纤维,我已经“堕落”到离自然要多远有多远的地步。一条Espirit的裙子花了898块人民币(瞧这价格定得玄的,900就900,还要玩个两块钱花招),小商标上赫然标着“黏液纤维”。什么叫黏液纤维?我妈一脸坏笑,说黏液嘛,大概就是鼻涕,把鼻涕拉长纺成布再做成衣服估计工程也够大的,难怪要这么贵啊。
现在就更加从俗如流,我成了名牌的追随者。走在路上,只要看见有人背着L&V 的包,我立刻奋不顾身凑过去猛看质地、工艺,特别是边角的缝线,然后直起身,满脸不屑地从鼻子里“呲”出一声:假的!
我穿着2000块钱以下的Ports,执著追求L&V的真品,心里念念要买BMW,坐在男友的Santana2000里敲打他赶快挣钱。和年轻时代的自己相比,现在的我没有主见,没有创意,没有想象力,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口口声声地嚷着后现代的用语,有条不紊地阐述POWER的意义和历史的可颠覆性,内心却狂热拥戴权威,一副企图融入主流物质社会的奴颜媚骨。
不就是外语吗?
劳乐
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曾经这样教训他:“不要以为会背几篇演讲稿、招待几个外国鬼子就是学好外语了。真正的本事是看你能不能用外语和外国人吵架——吵上一个小时损人的词不带重复。”他的爸爸绝对有资格这么说——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援柬部队的副大队长兼翻译官,他为给中国军队营地争取来一台冰箱和一个死硬的美国老头对吵了一个小时,最后他赢了。
我们的英语老师可能也意识到“争吵”是学习英语的一种不错的方式,所以在口语课中安排了辩论。不过,“学习方法”中的另外一个精髓却不大可能在课堂教学中应用。在我周围有学各种外语的同学。无论是哪国语言,一般我们记住的第一句话都是“我爱你”,然后就该是骂人的话了。德语可能是个例外,我们记住的第二句话是“Trinken Sie Bier?”(“您喝啤酒吗?”)
骂人的话有时也会有些正经的用处。开始学德语后,不久我们生造了这么一句话:“Ich m?chte auf dich sheiβen.”这是一句很粗俗的话,但我们记得烂熟,而且从此清楚无误地记住了第一人称第一格、第二人称第四格、介词搭配和情态动词直陈式现在时。由中文记外文的例子就更多。我很小就知道“我掐死你发发气”是俄语中的“参加”。
不过,我们并不想把我们的所有恶作剧都赋予“学习”的意义。下面这些“英语”就纯粹是“为无聊而无聊”:“Let me see see.”是“让我看看”,“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是“人山人海”、“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至于说这些无聊玩意儿是谁编出来的,那是“You ask me,me ask who”(“你问我,我问谁。”)。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敢像我们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大言不惭地说这些自造的“洋泾浜”。也许是学腻了外语的缘故,“说外语”在我们看来既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也没有什么可忌讳的。我们只是想拿这些字母和句式寻开心。如果真有人会因此而小瞧我们,我们会“give you a colour to see see”——不就是外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