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67)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林河 高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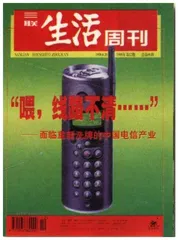
电信业竞争前景是整个中国产业发展前景的缩影。改革开放不是简单的“引狼入室”,电信业的国际竞争也不是简单的“与狼共舞”,贵刊是否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供更新的思路。
南京 林河
有关“改造北京”的一些回忆
北京 高汉
长兄陈干生前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的总建筑师和市政府的专业顾问,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城市规划专家。1950年,参与整修天安门的规划设计工作告一段落后,陈干调任都市计划委员会资料组长。当时,有关首都行政中心的争论非常激烈,陈干在这场争论中还起不了多大作用,只是回到家里跟我说起来时才显得有些激动,激动的原因是不同意离开旧城另建新都。我至今还记得他在当时和以后讲过的一些道理。
他认为,把旧北京城封存起来当建筑艺术陈列馆,听起来的确动听,但做起来却寸步难行。不说别的,光说垃圾这一项,当陈列馆的设想就是空中楼阁。无论是紫禁城的内外,还是北京的街头巷尾,到处是煤渣、脏土、粪便;城根关厢一带,还分布着1148处粪场,对这座古城形成了四面包抄之势,臭气熏天自不待言。据事后统计,清理掉的垃圾总量超过60万吨。试想一想,如果按梁公的方案,集中精力去开辟新区,把旧城封存作艺术陈列馆向世人开放,古建筑固然精美,但在垃圾堆和污泥浊水上欣赏,于中国人的脸面又能有多少光彩?
陈干此后常讲的理论是:保存必须和使用相结合,发展必然和改造相结合;对物如此,对城市也如此。他从搞了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整修规划之后,就确信整个首都的城市规划,只能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以中轴线和东西长安街为坐标来进行,坚决反对任何割断历史、弃旧图新的做法,也反对把旧城奉若圣物,连碰都不许碰的态度。
首都规划是陈干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我尤其难忘他辞世那天所表现出来的一片鞠躬尽瘁的情怀。我告诉他《城市季风》一书中把梁思成比作马寅初、把“梁陈方案”比作计划生育理论的观点。他笑道,历史是什么?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实践证明,反对马寅初的计划生育理论是愚蠢的、错误的,历史纠正了这种错误。但是保存北京旧城、另建新都的规划方案,在当时就行不通,后来更行不通,谁能想象现在或未来的哪一天,忽然从故纸堆里翻出这个规划来,又照着搞下去。我们已经根据自己的城市建设实践,总结出“分散集团式”布局模式,又开辟出了发展卫星城镇的道路,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城市规划理论。这就是实践,也就是历史,它彻底否定了那种出于某种偏爱的空想方案。不是说要尊重历史吗?那就应该尊重这一历史事实。
他感叹道,著书人应该说保护历史文物,而不应该说保护历史。因为历史是任何人都保护不了的。只要城里要住人,也要让人来参观故宫,新的生活方式就会跟人一起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来。拆毁皇城,打通东西通道始于北洋政府年代,这也是出于人民的要求。从那时到现在,时代发生了更巨大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演进一日 千里,对旧北京的改造一日也没有停止。至今仍然抱着原样保存旧北京城不动的方案,隐隐中埋怨当初人们不懂得“保护历史”的重大意义,因此要求为“保护历史”者大书一笔,这样说话的人实在有点春梦未醒的样子。
看着病榻上的陈干有些激动,我便接过话茬,由我来说,让他听着。我说至今仍有人怀念梁公的建都方案,重要原因之一是怀念旧的北京城墙。我自己对它也很迷恋,但当北京的建设事业蓬勃展开以后,这种梦幻般的感觉就慢慢地被理性代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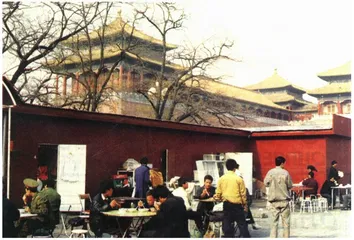
他觉得我的转变很有意思,要我继续讲下去。我说,就北京这一个地区而言,城墙已经够多了:方的有紫禁城,圆的有团城,长的有万里长城,断断续续的有元大都城;就是那座已经拆了的原北京内外城,至今仍然保留了若干城楼、箭楼和个别段落。把城墙作为文物观赏,或者把它作为古代军事防御工事来研究,这已经够丰富了。原来的内外城城墙迟早要被拆除却是势所必然的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那些城砖表面被风雨剥蚀的现象已很严重,钢铁也经不住风雨的消蚀,何况是城砖。这种情形怎么办?是投资重修,还是任其自然发展,慢慢地由破损而走向消亡?
生活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就像滔天的巨浪,荡涤着一切已经丧失根基的旧物。许多我们非常熟悉的东西都被这巨浪席卷而去,而大量新生事物又随着这巨浪排山倒海而来。当我们还来不及弄清究竟时,大地已经换了容颜。北京的城墙就在这样的变迁中从地平线上消失了!这就是历史。瓜皮帽、长袍马褂似乎在一夜之间都消失了,满街都成了列宁服、中山服、干部帽;而现在,这一切又都像被大风刮走了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哪儿哪儿都是西服、牛仔裤、超短裙、高跟鞋……服饰如此,建筑为什么就只能永远岿然不动呢?北京的天际线跟着发生了变化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总不能只许自己服装的轮廓线弃旧图新,而不许天际线更新换代。人不能只在历史的巨流面前叹时代之无情,哀旧物之须臾。事实上只有在确认这种进步的前提下,才能更加重视历史文物的保护。我同意他提到过的“只有继往才能开来”的观点。历史文物也只有在不断创新的历史前提下才更加显示其自身的价值。因为继往为了开来,也只有在不断地开来的过程中才更加懂得继往的意义。
他从床上坐起来,显得有些兴奋:的确如此!新陈代谢是宇宙万物共同的规律。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它所起的作用。对旧物的继承和维护有积极的和消极之分,分界点就在于是否按新陈代谢的规律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办事。
他说,只要举出两点就可以说明这种区别:一是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如果当初按梁公方案办,天安门广场只不过是一个狭长的、封闭的、T字型的皇家大院;而现在,古老的天安门城楼如同一块祖传的无价璧玉,被镶嵌在一个无与伦比的现代广场上。再比如大片危旧房的改造,百姓住房经过较长时间的磨损,寿命往往只有几十年,这是常识,危旧房改造因此成为一个城市的生命得以延续的重要方面。要把旧北京城封作艺术陈列馆永远保存是违背新陈代谢规律的。这个问题不决定于专家个人的偏爱,而决定于千千万万城市居民的意愿。众口一词的答复是“住楼”。道理很简单:他们不要煤球炉,而要用管道煤气;不要靠煤炉和烟筒取暖,而要靠暖气;不要靠别人送水或用抽水机压水,而要用自来水;不要靠掏粪工掏粪的厕所,更不愿到大街公厕大小便,而要有自家的抽水马桶……总之要“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生活方式。
陈干把这种居住条件现代化的现象生动地概括为:“把胡同竖起来。”他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城市地价随着人口的增长、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而增长,现代生活方式要求居住密集化,走集中供暖、供气、供水、供电的道路,这都是任何人无法阻挡的历史趋势。就北京这个具体城市而言,在特定区域内限制高楼是必要的,但不能一概地反对高楼。所谓把胡同竖起来,指的就是盖高楼。胡同横着行,竖着为什么就不行呢?在寸土寸金的北京,要搞现代化,胡同不能不竖起来。“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只是诗人的幻想。现在不同了。想竖就竖起来了。这就是历史,就是新陈代谢,是反对不得的。
陈干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激动。为了让他好好休息,我不得不起身告辞。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成了永别。
——摘自陈干文集:《京华待思录·云淡碧天如洗——回忆长兄陈干的若干片段》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