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64)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鸿飞 方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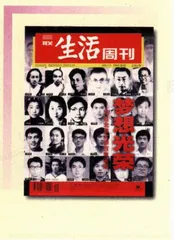
对北大在未来100年中的地位的思考,可能才是最好的纪念
北京 沈鸿飞
改造北京?还是毁掉北京?
当我读完《三联生活周刊》第8期的封面故事《改造北京:一条街道和一座城市》(以下简称《改造》),非常难过与气愤。有些人竟然用“革命”、“解放”和“改造”等词来形容旧城内的房地产开发,何其熟悉?再看看封面上那位抡大锤砸旧房的工人,如果给他带上红卫兵的袖章,恐怕没有人会觉得不妥。只是当年让人们愚昧疯狂的是信仰,多少还比较壮烈,而今天又是什么呢?
国务院颁布的三批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对旧城保护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其中,从个体建筑保护到整个历史环境的保护分为三个层次,即:文物单位的保护、历史文化区的保护和旧城整体形态的保护。互为依托,缺一不可。
这里重点想要探讨的是在宏观层面上怎样处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由此不能不提到著名的“梁、陈方案”。
但是,《改造》一文中的高君却仍然拿天安门广场改造的成功来否定梁先生的主张。其实,人们说天安门广场改造取得成功指的是广场周围的新建筑在规划设计上的成功,这是一个“战术”上的评价(它本身也不意味着保留原来天安门前的千步廊等就不成功),而“梁、陈方案”是对城市发展的一种“战略”思考,两者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
高君又描述说,当时郊外都是荒地,政府根本没有力量在旧城外建新的中心。且不说他对历史的无知,日伪和民国时期西郊一带已有一定的建设。从50年代到现在,今天的北京市区面积已经是旧城的六七倍,等于又建了好几个北京旧城。如果能够有计划地集中建设,新的中心早就形成了,怎能说没有力量建新中心呢?
事实上,“梁、陈方案”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因为北京仍然面临这个问题:是继续“以旧城为中心”发展,继续向旧城拥挤,还是努力向更大的发展空间进行积极的“疏解”?
50~70年代涌入旧城的只是大量的行政单位,今天则是更大量的商业和办公建筑,而后者对旧城所造成的影响也更加厉害。例如:西城区在二环路内建设“金融街”,占地103公顷,商业办公面积高达300多万平方米(面积相当于300个1万平方米的大商场)。在“金融街”之后,“东方广场”(东城区,总建筑面积100多万平方米)、“国际金融中心”(宣武区,总建筑面积170多万平方米)等一批大型商业办公建筑相继在旧城内涌现。北京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形成一个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商务中心(CBD,或叫金融中心、商务办公中心等,是国际大都市必须具备的城市功能)。新出现的CBD和商业中心又都叠加在旧城里,必然将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一切矛盾,都“聚焦”在北京旧城,这是导致旧城交通拥堵和平安大街不得不改造的根本原因。
80年代以来,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多次指出,北京旧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过分拥挤”,北京应研究建立多中心的城市发展战略,尽快停止旧城内的大规模建设,集中力量在旧城外建设CBD,例如在朝外地区,那里临近使馆区并且已有多个高档写字楼。但是北京市仍然不断加大旧城改造的规模,继续吸引投资涌入旧城。由于中央的行政中心(首都功能)在旧城内,考虑到日本东京由于城市过度拥挤而不得不准备迁都的事实,若北京旧城过分拥挤的局面不可收拾(百米宽的长安街目前已经经常堵车),北京被迫“迁都”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有些人认为,向旧城外疏解的做法是对旧城土地资源的浪费。因为按照一般的城市规划理论,城市中心区的土地利用率应当是最高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两个重要的事实。其一,紫禁城位居北京的几何中心,它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早已限制了北京旧城不可能达到一般城市中心区应当达到的土地利用率。其二,城市的中心与城市的几何中心是两个概念,而且城市中心也并非永恒不变。巴黎、东京、洛杉矶、波士顿等都出现了多个城市中心的格局;甚至出现了在区域内进行功能分工和协调的城市群,如:华盛顿一波士顿城市群、伦敦一伯明翰一利物浦一曼彻斯特城市连绵带等。北京距天津只有1小时的车程,北京城市发展向渤海湾靠拢,城市形态向东转移完全是可行的。由于新中心的形成需要花费时间,北京更应当“未雨绸缪”。
需要指出的是,建设新的城市中心仍对北大在未来100年中的地位的思考,可能才是最好的纪念。
北京沈鸿飞然是对土地的集约化使用,与国外50~60年代出现的“逆城市化”带来的郊区蔓延扩大、占用大量耕地是两回事。相反,由于出现多中心,北京可以有效地控制住目前这种低效益的“摊大饼”现象,减少占用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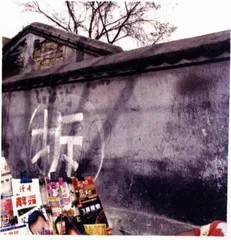
其实,改革开放以后,北京也有过向外进行有机疏散的成功例子,例如亚运村。当年曾经一度要将亚运村和几个亚运场馆放在城区内,后来经过研究安排在北四环外建设。结果带动了北四环的发展,亚运村一带成为目前城市外围较有吸引力的现代化地区。
想在旧城内搞大规模房地产开发的人,现在又举起一块美丽诱人的牌子,叫:“安居解危”。然而,在付出了“破坏历史文化环境”这个惨痛代价之后,单纯依靠旧城内的大规模房地产开发是否就能够解决旧城居民的住房问题?
北京旧城的住房问题是过去错误的发展政策的结果。根据文献资料,建国初期,危房只有80多万平方米,只占房屋总量约5%左右。50年代以后,在急于改造旧城思想支配下,忽视了对原有旧四合院的维修与保养,认为这些房屋将很快得以改造,不必下大力维护,导致旧城房屋失修失养,危房数量大幅度增加。加之60 -70年代人口急剧膨胀,带来非常严重的乱搭乱建,大部分四合院成了大杂院。80年代初期,旧城住房问题一度非常严重。
1990年4月,北京市政府召开了第八次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门研究危旧房改造问题,提出“加快危旧房改造,尽快解决人民群众住房问题”,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大规模的危旧房改造。
1994年6月,北京市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城市危旧房改造若干问题的通知》,将危改审批权下放到区政府,进一步推动了危旧房改造向商业性房地产开发的转变。许多危改工程如金融街、东方广场、报国寺等都以开发商业性的写字楼和商场为主要内容,居民也不再回迁。
远郊新区的主要问题是目前交通不便,生活设施很不齐全,而安置房又往往是新区中最差的住房。外迁居民原有的社会关系又都在城里,因此在上班、就医、购物、孩子上学等方面有诸多不便。
这里就需要了解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旧城居民对住房的实际需求到底是什么?另一个就是在历史文化保护地区如何满足居民的住房需要?
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师生进行的问卷调查,目前旧城居民对住房的主要需求依次是住房位置、面积、厨房卫生间等现代化设施、通双气等。由此可见,住房地点是居民们最重要的一项要求。但这一点却正是开发商不可能答应的,因为他的着眼点是盖商厦、盖写字楼赚大钱,而不是为原来的居民盖住房。
兴许有人又会说,旧城的土地这么值钱,为什么要建低造价住房?换句话说,旧城现在的贫穷居民应当住到郊外去。
旧城居民的确比较贫穷,但正因为穷,他们才更依赖城市。他们大都在市区所属的单位上班,单位里没有国家部委所属各单位那样充足的住房预算。因此,危旧房改造牵涉到社会公正与社会稳定。从这个角度来说,危旧房改造中仍然需要有政府行为,而不能开发商说了算。
这次平安大街改造需要耗资20个亿。但政府没有这些钱,怎么办?开发商出。赞扬这么干的人只看到了一条街道的开通,却没有去深入思考:开发商的拆迁范围为什么到了离平安大街160米远的地方?
不愿搬走的赵景心老人说:“我们不是‘钉子户’,如果是公共事业,开路建桥,我们肯定搬,但这里离平安大街有160米远啊。”老人的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事实上,即使“附赠”土地也不应当在旧城内解决。北京旧城只有62.5平方公里(其中故宫等文物以及河湖水面约占1/3),而旧城外的北京市区有300多万平方公里,其中朝外一带已经有多个高档写字楼,交通便利,环境也很好,为什么不把“附赠”的土地集中安排在那里,将来建成北京的CBD呢?
平安大街改造已经不是个简单的交通问题,它关系到整个旧城的命运。我们不能“吃祖宗的饭,造子孙的孽”。
因为北京旧城只有一个,全世界只有这一个。
清华大学方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