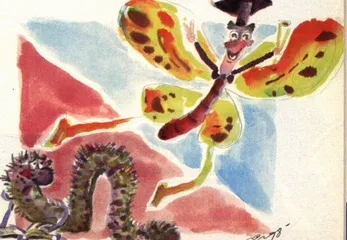生活圆桌(64)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刘应明 洪晃 吴宏 李甲)
算盘
文 刘应明 图 王焱
小女的算术课上到珠算了,这对她是件颇隆重的事。正如以前和今后她每要学点新玩意儿时一样,全家也照例跟着忙乎。又是买算盘、又是找录有珠算口诀的磁带,还得将业已生疏的指法在久违的算盘上温习一番。
珠算的文化内涵和实际用途恐已寥寥。当然,教育专家是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的。他们会抚今追昔,论述珠算如何是国粹、算盘如何有文化底蕴、甚至多用算盘如何有利于锻炼手指的灵巧性等等。
记忆中倒确实有两个深深得益于算盘的例子。其一是:某君年过半百而无所作为,穷极无聊之余也觉悟到要做点事情以无愧一生。但实在文不能舞墨武不能弄枪,无以惊人。最后想到了收藏。然环顾四周,大到钟表、钱币、邮票,小到脸谱、火花、烟壳似乎都有人收而藏之。忽一日,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想何不收藏算盘呢?虽然听起来不大正宗,但不也有人收藏石砚、门锁,甚至筷子的吗?于是,竟不问结果地埋头干了起来。您还别说,一来兴许是他真能寻觅,二则也是收藏该物件的人本来就无几,反正经年累月后也小有成就,自成专家。当然,此时的算盘已然不是用来辅助计算的了,而完完全全成了一件玩物。看到这位真人在一堆大大小小的算盘间神侃算盘的历史与文化啦、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啦,不知何故,我反正足横竖体会不出来。
第二个例子是从一本书上看来的,讲的是一个洋骗子的事。大意是某日洋骗子到一群富人堆里,大肆吹嘘自己正在着手开始一个重大的实业项目,生产一种新颖实用、简单易学、无需电源的计算工具,名为Sucaba。该新产品如何绿色、如何低耗、如何傻瓜、如何高效,富翁们听了大起兴趣,纷纷解囊投资这个前途远大的项目。洋骗子也真不含糊,未过多久就送来了样机。阔老们迫不及待地撕开外面的层层包装,正如您能猜到的,里面只是一架算盘。不免全体大眼瞪小眼,惊呼“What’sthis?”好在有钱人中也不乏稍有头脑的:“这是中国的算盘!”这下阔老们软瘫在椅子中。他们记起来,洋骗子并没有说谎。这确乎是个“新颖实用、简单易学、无需电源的计算工具”。而且他实际上早已透露了谜底:所谓的Suca-ba只是将英文算盘一词Abacus的字母顺序颠倒了一下而已。我读到这里,为我们的国粹充当了一回骗子的道具而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的感觉。
(本栏编辑:苗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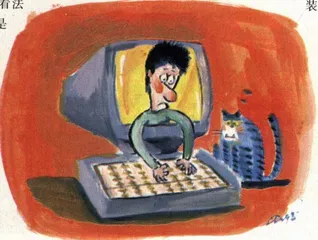
科学幻想
洪晃
Christine说,“我看过的中国电影都是讲以前的事,I mean,我们美国就喜欢拍科学幻想片,就像<黑超特警组>(MenIn Black)和《第五元素》(The Fifth Ele-ment)什么的,中国就没有,You know,科学幻想类的东西。”
“有吧?”我虽然觉得这个黄毛丫头说得挺对的,虽然她从来没去过中国珠江以北的任何地方,但我还是要“扛”一下:“我看过一部香港电影,好像有点像未来的事,有机器人什么的。”
“那不算,”Christine反驳道:“你说的那种电影就像《ET》那类,只是幻想,不是科学幻想。”
“那什么才算科学幻想?”我问。
“科学幻想必须把未来世界想出来,包括未来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都必须和今天不一样。如果只是一个未来的东西到今天的社会来了,就不算。《ET》就不算,《星球大战>就算。”
我有个毛病,每当说不过人家的时候就换个话题。“你说,也怪了,就算我们没幻想能力吧,可我们做的事比幻想还幻想,比如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快得出乎任何人的幻想能力,我小时候从来想不到中国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再说,你想一想三峡工程,如果没有想象力怎么可能有这种工程?”
“三峡是什么?”
她真无知。我很得意地花了喝三碗牛奶咖啡的工夫向她介绍了三峡历史之悠久,工程之庞大,未来之明亮。
“你们这么缺电啊?”这是她对我一番辛苦口舌的唯一评论。“But,”我最怕她说But,“三峡工程是从实际出发的,不能算幻想。”Christine说,“我教你什么叫科学幻想。这么说吧,如果叫你拍一个三峡的电影,你拍什么?”
“故事片?”我问。
“故事片。”她肯定地说。我脑子里只有什么大禹、都江堰的故事来回晃悠。这些都不能说,都是历史,说了正中她下怀。“你先说吧。”我反问她。
“那太多了,都是科学幻想。三峡里可以出个妖怪,就像苏格兰的尼斯湖(Loch Ness)妖怪,这是一个题材;三峡移民这么多,可以拍一个中国版的《开路先锋》(Mad Max),或者《水上世界》,这又是一个题材;但最精彩的是拍一个像《华氏450度》那样的片子。”“你是说杜鲁福(Truffaut)拍的未来世界里消防队烧书的片子?”“没错儿,”Christine开始进入角色了。“试想三峡工程成功了,但有一个问题,供电过多,如果不消耗80%,电站就有爆炸的危险,所以在消防队的监督下,家家户户必须昼夜点灯,永远生活在光明中,这是什么感觉?多棒的一部科学幻想片!”
“异想天开。”我用汉语说。
继续上课
吴宏
这几年,自学考试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教我们<法语>的是一位40岁左右的女教师。有一次,讲一篇介绍巴黎的文章。课文中有一些巴黎的名胜古迹的名字,有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卢浮官,先贤祠等等。对于一些大家较为熟悉的地方,老师没多作介绍,而对于比较陌生的,老师稍微介绍的详细一点。“红磨坊”(Moulin Rouge)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我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说实话,一本中国人编的,大学生用的教材中把这个地方作为旅游景点介绍,已经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老师说这里是人们唱歌、跳舞的地方。正好我坐在第一排,老师介绍完之后,我以探讨的语气补充了一句:“是妓院吧!”这时我身后传来一阵笑声。老师还没说话,与我隔着两个座位的一位女同学义正辞严而又莫名其妙地冒出几个字:“根本不是!很有名的!”如果此时我沉默了,那会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我从容地回答了一句:“我看过一本书,说这个地方就是妓院。”这时老师说话了:“可能是有这个成分。”她说话的口气显得有点勉强,显然她是被迫作出这个解释的。
第二次上课,我带了一些关于红磨坊的资料给老师看。一篇是一本旧杂志上的文章《“红磨坊”春秋》,文章详细地介绍了红磨坊的历史。还有一篇是余光中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余光中批评台湾的一些恶俗的翻译时,举了一个例子,一部电影名直译《红磨坊》而译者非要译为《青楼情孽》。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想告诉那位与我隔着两个座位的女同学:有知的庸俗胜过无知的高雅。
教我们《高级英语》的是一位40岁左右的男老师。有一次在讲课时,他向我们发了一番感慨。他说:“我是很喜欢给你们成人上课的。我在大学里给学生上课,有些东西不能讲。而你们都是成年人,都已走上社会了,所以给你们讲课,我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觉得比较自由。”原来他晚上出来讲课,并不只为了赚外快,还为了寻找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地方。接着,他给我们讲了一件事:有一次,他给一个“自考”补习班上课。讲的课文是一篇由中文小说翻译成英语的。由于同一个动物名词在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含义,他觉得这篇文章中的一个动物名词的翻译择词是极为不妥的。由于考虑到学生们都是成人,他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在中文中,这个词并没什么,而在英文中,这个词还有人体器官的意思。如果让美国人看到这种句子是要闹笑话的。过了几天,他收到一个电话,是一位学生家长打来的。在电话中,他的过度诠释被指责为毒害学生的流氓行为。
听老师讲完这件事后,我们都笑了,老师也笑了。他无可奈何地说道:“有些事,真难办。我们还是继续上课吧!”
教育与虚伪
文 李甲 图 王焱
在我生活中的头20多年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落后分子”,我上到小学五年级时还没被批准入少先队,上到高中三年级时还没加入共青团,上到大学四年级,快毕业了,才知道按综合素质排下座次,好工作轮不到我来挑。
我上初中时犯过一次错误,那是我求学生涯中所犯无数错误中之一次,具体是什么事,我忘了,但我记得那次老师要我写5000字的检查,说“没有长度就没有深度”,我就熬夜写下5000字的检查—那时候,我的理想是当一个鲁迅或巴金似的文豪,可以出全集,这样的话,全集第一卷中就会收录我写过的所有检查。
为什么我会犯错误写检查呢?大概是因为我老暴露“人性的弱点”,比如在参加集体劳动时犯懒,比如上课时总说两句闲话,比如到青春期时想跟个姑娘谈恋爱。对这些错误,我当年的认识是很深刻的,后来却觉得有些模糊—老师干嘛要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学生呢?或者干嘛要用阴暗的心理去揣测学生呢?
比如我当年“早恋”,老师定下来基调说我“勾引女同学”—“勾引”这个词儿非常刺耳,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勾引一般是个手段,下面还有目的,可当年的我没有目的—连勾勾手指头都没有。但老师们的逻辑很吓人—你如果不是个圣人,那么你就是个流氓。
于是我就写检查,但还不是要写怎样勾引女同学,而是要分析自己为什么不是圣人,这非常有难度,我年纪小,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但相信,那时的情况也是这么糟糕。总而言之,你要非常虚伪,你越虚伪越接近老师们的要求。
在我大学毕业时,我的一位标准的好同学找到了一份好 工作,我们都很羡慕,他说,这份工作是付出代价的。“我装孙子装这么多年不容易啊。”说来好笑的是,我这样的“落后分子”的工作是去当老师,去教育别人。
在这个岗位上我没干多长时间,但我发现,整个教育过程就是学生跟虚伪对抗和妥协的过程,我在我的学生身上看到了许多“人性的弱点”,——比如他们也愿意营造一种虚伪的风气,我也希望他们是圣人—至少做一个大体上是诚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