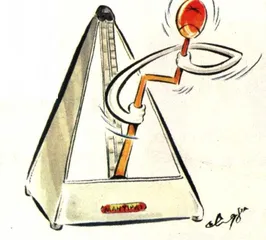生活圆桌(59)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王焱 舒木禄 曹云 孙海玉)
语言能力
文 杜比 图 王焱
我以往总能听到这样的批评,说那些说话时夹杂几个英文单词的人多么操蛋,那时我英语水平很低,听到这样的批评未免窃喜。
后来我渐渐发现,夹杂几个英文单词未必就是“假洋鬼子”,因为英文中的确有些东西是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词儿的。比如说“brain stonning”,你可以说“咱们来个碰头会”,但“碰头会”的说法很不准确,而且非常土。
近些年,“酷”字极流行,那么,凡是说“Rh”的人都等于在言谈中夹了英文。我从卫视中文台中跟Go West的主持人吴大维学了一句话叫“This is cool”,准备用它代替“是”或“Yes”,我已确信,说话中有一两个英文单词冒出来,能多一份体面。
生活得不够体面的人尤其愿意在这些小细节上下功夫,因此,改变自己在使用汉语时的毛病与学两个英文单词同等的重要。比如我有个毛病,每次坐出租车,司机问我是不是该走某条路,我总回答说:“对对对”或“行行行”,再比如某人求我办件事,我也总说:“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据说早年间的国语电影,演员念台词时就喜欢重复,情感充沛地说:“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相比之下,我竟然能把一个词重复至三遍,这就显得很不沉稳很不优雅。更好的回答应该是这样,司机问我能否走某条路,我只说“对”或“行”,别人让我帮忙,我也只说“可以”,如此才能显出从容的、成熟男人的韵味,忙不迭地说“对对对”,感觉就像“小碎催”。
早几年,我读《光荣与梦想》,艾森豪威尔的副官说,艾森豪威尔不自称“我”,而是说“艾森豪威尔如何如何”,文中称,大凡用名字指称自己,就是自大狂开始发作了。
后来我留意观察,这一论断百分之百的正确。虽然用自己的名字代替“我”字的人并不都如艾森豪威尔那样当上将军和总统,但至少是我们社会的“成功人士”。
遗憾的是,我目前还不敢这样说话,能在言谈中夹上一个英文字,就让我自呜得意了。

松武拜佛
舒木禄
前些年老能听到有些活动的主持者说“重在参与”。这话的意思就是,你别管是否丢人现眼、是输是赢,甚至是否乐意,这一切都不重要,你参与了,无论怎么样,最后都有“重在参与”这句话挡着呢!
这句话其实对人很不负责任,它一棍子打消了你问为什么,干什么等等的念头。真照这话去行事,人对自己也会不负责任起来,幸亏它没有那样的蛊惑力。但它还是很坏。这种坏就像站在路边的算命“乞丐”,他告诉你,“信则灵”。这种东西有一种阴柔的腐蚀力。最开始它腐蚀一些正在想参与的人,最后把离它最远的人也卷进去了。这时候,不参与就有点犯虚。
10年前我认识的一位性情坚毅的广东人松武就是这样犯虚的。那时候我第一次去广东,见到无论大小公司,大商店小铺子都有一块拜佛的地盘。在一家餐厅里松武请我和几个朋友吃饭,这家餐厅不小,拜佛的地盘却不大,松武让我们仔细看看那里拜的哪一家佛,走近一看,才发现这家老板真周到,佛龛摆了一根硕大的蜡烛,上方有一排小小的木牌,上面排列如来佛、菩萨、基督、上帝、真主、关羽、孔子、财神爷、灶王爷、毛主席等等。一根蜡烛把他能想到的人一并都拜到了。松武说,这老板最初只拜如来佛,后来看到有人信基督教,他又把基督的名字写上,最后就越添越多。今年我又去广东,如我所猜,他又添上了邓小平的名字。如此互相矛盾的人名都聚在一起,其实不能责怪这老板没文化或没信仰,他实在是被腐蚀了。
松武也没坚毅到哪儿去,10年前他做生意,做得顺利,在广东他不拜任何佛,显得很特殊。5年前我见到他时,他还是没拜佛,并且说某某人不信任何神鬼也活得挺好,这时我没有觉察他的变化,现在想想,找出个成功人士做证据,是不是有点心虚了。今年春节,松武搬了新家,我去看他的新房子,房子可以说明他的生意依然顺利,人也依然精神十足。因为在这之前,我看到有的人家里也设了佛龛,所以就玩笑地问松武是否拜佛。松武哈哈大笑,然后让我低头看我身后的沙发脚。沙发脚旁边放着一个易拉罐,上面插着一根香炷,易拉罐上已经盖了一层香灰。松武说:“都拜,那就拜吧!”此中的无奈全堆在那一炷香火委屈的角落。
重在参与吗?反过来说应该是:“不参与很严重。”这就像看电视对于我的重要,最开始是不看电视,去上班时人人都在说电视里的事,我听着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后来也看看电视,后来我上班时不像傻子了,每天晚上坐在电视前都成了傻子。反正,只要一跟“参与”这词缠上,就怎么着都像傻子。(本栏编辑:苗炜)
宴会与礼仪
曹云
我妈说凡喜欢摇滚的人都是粗人,有点“野”,而我似乎也可以归入此类,至少有一点可资证明:在我那只并不太大的衣柜里,各式各样的牛仔裤、T恤衫充斥其间,要从中发现一条西裤一根领带什么的,那简直比大海捞针还难。所以,像我这样的人讨厌各种宴会应该是很自然的,而我对那些所谓的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作派也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好感,总觉得那就是繁文缛节的代名词—说这些,当然并没有要表示自己有点反主流的意思。
不喜欢什么并不是说我就可以不去干什么,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一个人不能因为讨厌工作就可以成天在街上东游西荡。
那天朋友约然要我和她一起去出席宴会,出于开开眼界的动机,我答应了。约然是那种典型的白领阶层,我当然知道与她赴宴绝无穿牛仔裤的可能,即使是华伦天奴牌的休闲服也不成,但其他的我真的一无所知。所以免不了要问约然有关的问题,包括我可以做什么和可以不做什么。
约然首先告诉我怎么吃饭(在她嘴里叫“进餐”):入席后不要用双脚拥抱椅子腿,不要摸这摸那,也不可以用手支起下巴做“思想者”状,正式用餐时不要让餐具碰撞发出声响,用刀叉切肉时也不要像在厨房里剁排骨似的—听完这些,我对自己会不会吃饭就真的有点将信将疑起来。
当时想起在电视上曾见过每个人拿着一个酒杯走来走去,我就问她要碰到这种场合而我又找不到谈话伙伴该怎么办。约然说那天不是鸡尾酒会,但她还是告诉我在那种情况下,不必去找别人,别人会来找我,最根本的一点是另外两个人正在交谈时,不要给人感觉你像个便衣或侦探一样在一旁窃听—约然知道以前我在厦门大学外语角时常这样。
但那天的宴会安排了舞会,“当你邀请女宾跳舞时”,约然告诉我,“应先向同她在一起的男伴点头致意。”“要不要和他攀谈两句?”我问。“如果你只想和他聊天不想和她跳舞,这当然再好不过了。”约然接着说,“当跳完一曲后,应对舞伴表示感谢并伴她离开舞池,绝不可以舞曲一终,撒手就跑。”听到这里,我就有点不想去了。因为通过约然的一席教导,我已经想象出宴会的情形:就跟中世纪封建贵族的宫庭舞会一样。
在这种宴会上应邀致辞的机会很多。约然的这话还没说完,我终于大声对她说,我不想去了。但约然马上又告诉我,致辞或许会令你感到为难与紧张,事实上并非如你所想象的那么难,也不必使用优美华丽的词藻,只要把握住扣人心弦的原则就行。可在我看来,把握住扣人心弦的原则,其难度系数比使用优美华丽的词藻一点也不小。
条条框框太多了,我对约然说坚决不去了。但约然说,条条框框是条条框框,并不妨碍你在宴会上从容自如,就正如成千上万条法律也丝毫没有干扰你的正常生活一样。自然是至高的法则。
一想也对,所以后来我还是去了,结果得意地发现自己居然能俗也能雅,事情远没有先前想象的那么糟,除了一点小意外,甚至可以说我还相当绅士。当时我正泰然自若地用那把没有刀刃的刀切那块半生不熟的牛肉,一不小心,肉从盘子里滑出来,正落在自己的西裤上。来之前约然并没有告诉我,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正在我吃惊不已而又手足无措的时候,小姐飞快地过来帮我弄走了那块肉并换上一块崭新的餐巾。我惊魂甫定地抬起头,看见坐在对面的约然朝我嫣然一笑,好像是在鼓励我,又像是在宽慰我。我就想应该再自然一些。
慢一拍
文 孙海玉
图 王焱
有一段时间,我患上了严重的阅读恐慌症,或者叫信息恐慌症、我狂热地翻看报纸,以了解全世界各地的大事小情;我的书桌上堆满了花花绿绿的杂志,它们都严肃或戏谑地预言着即将到来的下个世纪;朋友、作者们不断寄来新著,印刷得美仑美奂,让人舍不得不翻一下就扔在屋角;最可怕的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畅销书排行榜或名家荐书,若赶上个不负责任的,拿个棒子一点,够我折腾小半个月,然后一头雾水地从那些所谓畅销书里溃败出来。
病成这样没别的原因,就是怕自己没知识,怕赶不上新时代!报纸上说了,在西方发达国家,文盲的概念已经泛指所有不具备现代知识与技能的人。对现代化步伐迅速的中国,过不了几年,新旧文盲大概便为浩浩大军了。
广泛而忙碌的阅读真让我感到“充实”。我找到了走在时代发展前沿的美好感觉。
但是,这种感觉没维持多久,其后遗症却显露出来。我睡眠严重不足,整天哈欠连天,对身边鲜活的人与事毫无兴趣;我对事物的理解已经“信息化”,浅尝辄止,说上二百字便哑口无言。
后来我就采取观望政策,看看大事小情有多少与中国人有关;看看畅销书能在榜上停留几周;看看那些预言有多少现实意义。这样一看,原来有一大半都是“伪信息”,与我几辈子也不沾边儿啊!再往后就明白了,尽管科技、信息、电脑使我们头脑中的盲区越来越多,但是属于人类的永恒命题仍然就那么几个。这就像地基与摩天大楼,楼盖得多惹眼,地基就那么一块儿。
病一好,赶紧将这方法告诉周围的人们,我这才发现周围有不少同属病中人,他们总妄图赶在什么前面,其实根本就是与巨大的媒体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信息的繁衍能力增强了,人们的创造力也增强了,但两者之间断不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