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明信片:大片及其他
作者:娜斯(文 / 娜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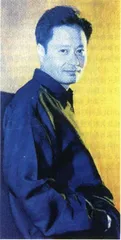
会拍西片的李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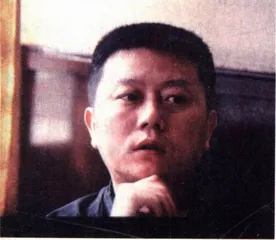
王朔当年挺“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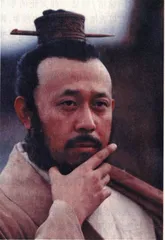
《秦颂》中姜文饰演秦始皇
记得还在大学校园里做学生时,看到姜文演的溥仪,吓了一跳,说哪跑出这么个演员,这么会演戏。尤其是那电影并不怎样,所以更显得难能可贵。过了一阵,又见姜文演秦书田,又把我们吓了一跳,不但跟我们记忆中的溥仪搭不上边,才气也罢了。那时候,中国男演员在银幕上特会演戏的不多,让女人觉得有吸引力的更少,不是特木就是特奶油或者往胸口上贴假胸毛。
后来是《本命年》。要不是有姜文,还真想象不出这片子怎么看。那时改编王朔一窝蜂,可是男主角全不对路。王朔那时挺酷,可是人们还不懂得说“酷”这个词。把王朔称为痞。弄得好象他自己也糊涂了,后来还真俗了。那时的王朔迷苦思冥想谁能演王朔的男主角,想来想去想不出。后来王朔小说改电影终于成功的是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遗憾,到现在我还没能看到。但是各种迹象看起来,不管你怎么看它的意识形态,它似乎拍出了“酷”,而不是“俗”。
后来没有看到姜文最好的东西,我只是断续看过《北京人在纽约》,最近又看到《秦颂》,老实说,不但当年吓一跳的感觉没有了,而且觉得不对路了。“北京人”且不提,因为那是电视剧,《秦颂》让我有点张口结舌。不知这是不是就是那种“与世界接轨的大片”,架子摆得特别大。我不敢妄加横批,并不是姜文的演技坏,不过很替姜文遗憾。当年姜文演溥仪的那电影虽然也不见得怎么好,因为没那么大的企图心,所以那坏处倒也还没那么让人印象深刻,愤愤不平。现在姜文任是怎么聪明,这电影那么“端着”;换了哪个演员恐怕都难—葛优的高渐离,就更离谱了。所以,很高兴看到姜文谈电影的一番话(虽然那题目又显得特耸动,见1997年第20期三联生活周刊)。而且觉得,姜文不能演项羽,未必是件坏事。
我现在有点“怕”看艺术大片。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动作大片坏呢,也未必让人太在乎;小形态一点的电影坏呢,也容易让人容忍。怕的就是大卡斯,大制作,大构想,大企图,然后坏得让你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比如我刚刚看的马丁·西塞科斯(Marlin Scorcese)拍达赖的新片《Kundun》,就几乎是这么一种情形(除了没有大卡斯)。我这里无意谈它的意识形态,我失望的是这个“名导”的“大片”在艺术上如此平庸。它一点没有把西藏独特的东西表现出来,而且平庸得离谱。片子的节奏很忙,摇来摇去的,忙得让人不知所以,可是又讲不出什么东西来。
这里牵扯到的一个问题是,西方艺术家到异国文化去寻找灵感,尤其是拍东方文化,不管多大牌,几乎都不成功。西塞科斯拍西藏的佛教一塌糊涂,贝托鲁齐比西塞科斯应该更有文化感一些,拍的“小活佛”(Little Budda)也是捉襟见肘。这当然涉及了复杂的文化问题,无法一言以蔽之,但简要说来,东西文化权力走向的不平衡,使得西方的文化人对东方的了解一知半解,或神秘化,或浪漫化,或理想化,或野蛮化,总之都缺乏一个踏实做功课的过程。马丁·西塞科斯是纽约成长的艺术家,最熟悉的生活是纽约的街头混混“can·street”,小痞子,拳击手,出租车司机。他是不是就不可以拍别的题材?当然不是。但是以他这样一种文化背景,要拍西藏和佛教的东西,一定做足功课,现在是,哇,这个题材真有意思,然后三下五除二就给它拍出来。贝托鲁齐的东方,不管他搞没搞懂,仍然有一份他情感上的东西在那里,西塞科斯的东西则是彻底的没着边际。
当然,有人会说,你说西方导演拍不了东方题材,是否又是中国人文化上的自命不凡?李安还在好莱坞拍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冰风暴》呢,一个是西方名著,一个是70年代的中产阶级郊区生活,都是他不熟悉的,都在美国被接受,是不是显示了他们比我们宽容?我觉得这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话题。第一,李安本身是美国的电影系统教育出来的,在美国已生活了多年;第二,在文化的走向上,本来东方的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殖民”要比反过来多,我们有时可能了解—或推崇西方的经典要比自己的多的多;第三,他是在好莱坞的系统中拍电影,所有工作人员都是西方人,在文化背景的把握上还有编剧、摄影、美工、演员等一系列的主创人员在那里把关。西方人拍东方的电影,有哪种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在此倒还不是讨论西方导演拍东方这个话题,其实先不管别人,先说说自己的事。如果我们批评西方导演对我们的文化不做足功课就敢乱玩,我们自己,在一个世纪来的文化动荡下,又敢说对自己的文化就有多少扎实的把握?我们的功课也未必就比人家需要的少。
我说我现在怕看大片,当然不是怕看好的艺术大片。纽约现代艺术馆刚刚举办了意大利导演维斯康蒂的影展,一部《路德维希二世》(Ludwigll)看得所有人如痴如醉,3个多小时一点不觉。维斯康蒂属于真正的“最后贵族”,他的欧洲,复杂,华美,颓废,正在消逝的文明,谜一样的皇帝,瓦格纳的音乐,庭台楼阁,锦衣贵妇。但是他拍得从容不迫,毫不堆砌。我恰好是看完此片再看西塞科斯的《Kundun》,后者尤显小儿科。
在杂志上看到作家阿城受邀当文学奖的评委,他上来先说,不知道为什么奖只有一名。他说:“科举有所谓状元、榜眼、探花之类,但诗无状元,虽然唐时科举中有诗一项,但状元诗留下几首?诗只有品。艺术只有品。”我衷心拥护这种见解。当然这里说的又是另一个话题了,但我在这里引用是想说,很多人急着拍大片,写巨著,好像就跟爱设奖的人是一种心理,觉得艺术也得有状元。比如诺贝尔就是个搞科学的,搞科学的人爱说“真理”,“对错”,“答案”,可是在艺术中,这些概念其实都是很要命的。所以由一个搞科学的创造出的文学奖,它的意义我一直很怀疑。电影也有电影的奖。国际上的电影奖好像比诺贝尔奖还人文一些,毕竟是搞电影的人自己设的,比如有大奖也有小奖,有老资格奖也有新人奖,同时也不忌讳买进卖出地忙着做交易。这个评奖的意义就比诺贝尔的强些,让大家知道各地方的人都在做什么东西,各种各样的放到一起瞧一瞧,而且评出来的东西,好像也不都非得是规模宏大,解决了什么终极真理了似的。起码我看过的一些电影大师的作品,得了这个奖那个奖的,很多都并不是“大片”。艺术有品,不是拿尺子量大小,拿称论斤两之类。然而不管怎么样,在艺术上不按“品”,而按“榜眼探花”之类的说事,“大片意识”恐怕就不会断绝。在这一点上,奥斯卡是最让人不耐烦的。我现在不但电影爱看小电影,连吃饭都要上小馆子,买衣服拒绝进百货商店,不喜欢听人说大话,看画专看小幅……追根溯源,或者都是奥斯卡的大片给害的,也未可知。
马丁·西塞科斯:美国导演,最出色作品是70年代的《愤怒的公牛》、《出租汽车司机》,写纽约下层小人物生活,震撼美国影坛。近年代表作是《Goodfella》、《Gape Fear》。90年代改编女作家伊迪比华顿写美国早期上流社会的小说《纯真年代》,在题材和风格上作新的尝试,反应不算成功。《Kundun》是其最新作品,正在美国公映。
鲁西诺·维斯康蒂:意大利战后一代名导演,现已去世。他出身意大利欧洲最古老的贵族世家,本人思想左倾。代表作品既有早期写平民生活的新现实主义名作“罗河和他的兄弟们”(1960),也有场面辉煌胡贵族文明的杰出写照“豹”(1967)“路德维希二世”(1972)。 姜文电影秦颂王朔中国电影战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