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55)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施武 布丁 曹云 杜比)
注定要输也得赌
施武
维特根斯坦有一次在讲到如何教给幼儿语词的用法时说,大人总是以为小孩笨,总是不能正确理解大人的话,比如,一个母亲指着一个红皮球对小孩子说:“这是红的。”以后,这个小孩见到圆的东西,就说:“这是红的。”维特根斯坦说,这难道是小孩的错吗?这是大人愚蠢。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在大人向小孩讲述知识和道理时,不能仅仅给出一个教条,得给出一个系统。
自从我成了大人并面对自己的女儿以后,我时刻注意着不能给小孩强加一些教条,不是教条不好,而是教条导致误解,结果就会是很槽,我就不仅会成为一个完全愚蠢的大人,还将是一个失望的母亲。我在一篇讲教育的文章里读到过一个母亲的失望,她说:“我儿子出生时,我曾希望他以后成为总统,现在我为他没有成为公理的谋杀者而感到宽慰。”教育的初衷与结果之间有如此大的距离,让人觉得此事全无可为。所以,我明确地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希望她成为任何“总”什么。
但是,教育自己的小孩好像是一种冲动,不管自己配不配。在这种冲动下,我还是不可避免地较上了劲。我给她讲英雄的故事,英雄一律都是力大无比的,英雄一律都是最终的胜利者,英雄一律都是好人。她很想当英雄。我给她讲懒猪的故事,懒猪一律都吃的多,一律都是胖胖的,所以是饭桶。我还在她的提问下告诉她小孩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我还引诱她自己动脑筋,不要什么事都问别人。这些都没什么错吧?有一天,在我软硬兼施地让她多吃饭时,我说,“吃得多,才能长胖。你知道像后羿那样的英雄为什么那么有力气吗?”她说:“因为他们吃得多。”“对!”她异常兴奋地说:“英雄就是饭桶。”我失望地扇了她一巴掌。前几天,我给她找来一本幼儿书,书名叫《人从哪里来》,讲的是从猿到人的进化。当我拿给她看时,她不看,我问为什么不看,她说:“我不看就知道,人从妈妈肚子里来。”
虽然我一直还没有冲动到忘记了维特根斯坦的提示,始终尝试着在一个系统中给出指导,而且标准很低,讲那么多英雄不过是为了激励她多吃点饭,还是免不了失败。我觉得教育好像是一场注定要输的赌博。难怪有一个研究教育的美国人一个劲地在论证教育的不可能。可是,这冲动又难以压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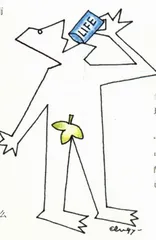
渔民和富翁
文 布丁 图 王焱
有个富翁,到海边旅游,见个渔民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他就劝渔民多干活儿多赚钱,渔民就问富翁赚了钱有什么用,富翁回答说,那就可以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渔民说,我现在不就躺在沙滩上晒着太阳吗?
以上这个故事,好多人都知道。其中心思想是劝人不要赚钱,而是尽可能多地晒太阳。
如果是富翁读了这故事,那的确有点儿好处:他可以停下日以继夜的工作,先放慢赚钱的脚步,去晒晒太阳。但如果是渔民或更多的像渔民那样不富裕的人读了这故事,就有被欺骗的可能:他们会以为富翁们赚完了钱,不过就是有了在海边晒晒太阳的机会。
很显然,这故事有个不合理的观点,认为富翁晒太阳和渔民晒太阳是一回事。当然,这故事还嘲笑富翁比较傻:他为什么要用“晒太阳”去刺激渔民赚钱呢?渔民天天晒太阳,想不晒都不行。
早几年,我初次读到这故事时,觉得那渔民很了不起,悠闲,自在,智慧,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个穷光蛋。今日再读这个故事,那渔民的形象在我心中变了个样:呆滞,愚昧,自以为是。
我还因此憎恨写这个故事的人,这故事好像是个外国作家编的,因流毒甚广反而像个民间故事。我想,这故事写作之时应该注明:专为富人阅读。
眼下,街面上流行一本书,叫作《生活简单就是幸福》,我想,这本书也该注明:专供年薪100万以上的人士阅读。或者说:专给生活得极复杂的人士阅读。
生活简单,该怎么理解呢?
比如一个人一月挣1000块钱,投资理财就比较简单,挣5000块钱,就复杂了一些,挣50万,就非常复杂了。这时候,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个人帮你投资理财,这样的简单比较幸福。
再比如一个人没有女朋友,生活就比较简单了,有了一个女朋友,就复杂了些,有了两个,就复杂了一倍,有了好几个,就极复杂。简单又幸福的办法当然是去粗取精。
《生活简单就是幸福》,主旨是把复杂的生活弄简单,这个过程幸福,而不是说只挣1000块钱、没有女朋友才幸福。
我是把这本书当作“反面教材”读的,比如书中讲该减少不必要的应酬,这样才简单,我一算自己一个月也赴不了一次晚宴,蹭不了儿顿饭,就知道我还不算复杂,就还得使劲儿棍。
男的女的
曹云
大可和我在同一个偌大的办公室,有一阵子,他特害怕接电话。这是因为好几次每当有人叫“大可,电话”时,他总要朗声地问上一句:男的女的?这肯定会有人明显地表示不齿,觉得这厮未免也忒“好色”了,而且还敢如此地明目张胆。
虽然大伙在心里都这么认为,但也不好意思直截了当地指斥他。当然大可从大伙那么惊诧的眼神中似乎也读出了一些什么,本来他就不鲁钝,由此做一些合理的想象也在情理之中。我猜想,他肯定以为大伙从他的这一举止中推知他思想作风不好或者道德品质败坏,在无形之中,大可将自己比作了霍桑小说《红字》当中的那位可怜的女主人公。
其实,大可并不是那位与年轻传教士偷情的女主人公,大伙更不是那帮有意无意地充任了道德法官的群众。大可接电话时总要问一声“男的女的”,这根本就不表示他特在乎打电话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熟人见了面总爱问人家“吃饭了没有”,也不是说人家如果没吃的话我们立马就会请他去饱餐一顿一样。据说在加拿大不时可以听到加拿大人抱怨这抱怨那,大至通货膨胀率太高、就业机会太少或者税收过高,小至公共厕所不干净、公路某处路面不平或者电视台音乐节目太少。有人甚至在报纸上撰文,说他有一次在一家餐馆用餐时,从盘子里挑出一只苍蝇,竟然就由此引发长篇大论,指责政府环保政策不当、力度也不够,文章中说,连餐馆也会有苍蝇,可见国内环境糟糕到了何种程度!
如此看来,加拿大在其公民的眼里整个就一无是处。其实非也。有一家民意测验机构就此做了一次民意调查,问加拿大人如果有机会移居国外,他们是否愿意到加拿大以外的国家去定居。调查结果令人大跌眼镜,说愿意的竟然只有1%!
加拿大人的逻辑和大可是一样的:在他们看来,抱怨归抱怨,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在加拿大幸福而安详地生活。同样,“男的或女的”也不是说如果是女的,大可就会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而如果是男的,大可极有可能两步当作三步甚至干脆就不去接。
无论怎么说,大可后来不再问“男的女的”,而改为“来了来了”,但很显然,他有点不大适应这种方式,所以就有些害怕接电话。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某一天,中国人见面不再问人家是否吃了饭而代之以热烈的拥抱亲脸,那肯定会感到特别扭。
这些我们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之后,在办公室接电话谁也不敢问“男的女的”。那天我到对面的打印室去打印两篇文章,其间有人叫我电话,我脱口而出:男的女的?—当然,这次我是真的很在乎是男是女,因为我妹妹那天下午要我去西站接她,她从未来过北京。没想到那边传来一阵哄堂大笑,还齐声高喊:男的。于是我没好气地嚷了一句:让他待会儿再打。可当我来到办公室时,大可却告诉我:电话是女的打过来的。
傍晚时分,听见妹妹.在下面叫我,下去一看计程表,的士司机和我都吓了一跳:85.90。
(本栏编辑:苗炜)
可怜的马
杜比
早些年,我在大学里听讲座,有位先生来讲电影,开头第一句话是:电影本是种很粗俗的东西,不过,幸好现在有了电视……
对这句话,我印象深刻,原因是我既喜欢看电影,又喜欢看电视。我相信,比起音乐或戏剧,电影、电视的确算不上多雅致,但更多的人还是喜欢电影电视。
至于说电视比电影还低级,这我也很理解。电视里常讲一些电影制作的技巧,为某部电影作宣传,反过来,电影却常常骂电视,比如有部片子叫《无线电视狂》,讲一个人酷爱电视,还极热情地帮别人安电视线路,这个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有精神病,而且是看电视看出来的。
还是早些年,一个聪明人告诉我说,让自己变傻,有4种方法,其中之一就是看电视。我连忙追问其余3种办法是什么,他说,你看你看,你已经变傻了。所谓4种方法,只是虚晃一枪的事。
这个人说的话,我就不大同意。因为就我的经验来看,经常看电视不仅不会变傻,反而会觉得越来越聪明,你看了太多的缺乏智慧和创造性的东西之后,就会为自己那点儿智慧和创造性而庆幸。看电影,有时也是这样。
前不久,我在电视里看到了一个专题片,讲贺岁片《甲方乙方》的拍摄过程,其中说,导演和演员们很努力,夏天里拍冬天的戏,要穿很厚的衣服,这是多么可贵的奉献。电视片还记录下拍这部电影的一些花絮,比如导演兼演员在拍最后一场戏时老找不着感觉,发了点儿脾气。
过了些日子,《甲方乙方》的导演兼演员不发脾气了,心平气和地坐到了电视台的演播室里,谈起其创作的想法就是想让影片好看,还说,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就非常好看。
又过了几天,我终于坐到电影院里看完了电影《甲方乙方》,如果你让我说这电影好看不好看,我想,要是我几年前看了这样的电影,肯定会说还算好看。不过现在,我又觉得自己聪明了一些。
我这里写文章,并不是要评价哪部电影好,哪部电影坏,也不是想说电影和电视的关系问题。这些话,我没资格说。我想说的只是自己的一点儿感受。
《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一部我爱看的电影,我还买了本《诞生》,想看看人家是怎么拍出来的,一看书,我明白了,导演用了好多好多胶片,然后再慢慢剪,不过,以最后的成品看,这样的浪费值得。
还有一部国产大片,其中有个镜头是一匹马活生生地摔下了悬崖,我看完这部电影,整天就为那匹被摔死的马难受,至于这部电影是不是好看,我倒没有什么印象。我老想:为这么个电影,还要摔死一匹马,太浪费了。 渔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