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节:拒绝明星
作者:李鸿谷(文 / 李鸿谷)

《丛林人》

《安居》

《门德尔》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先上演的是一道特别的风景。
在开幕式上,香港明星冯宝宝受到众多媒体的疯狂追捧。10天的电影节下来,再难觅这等景观。自称“在家里上班——照顾老公照顾孩子”的“下岗”明星冯宝宝竟能在国际电影节上复习当年的红火,这已经清楚暗示本届电影节的一种倾向:拒绝明星。
号称国际九大A级电影节之一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是否因这份“拒绝”而使自己显示出独特的个性?是一个待解之谜。
拒绝明星,能使观众更注意电影
戛纳使中国人认识了世界电影节的模样。当戛纳让我们重新发现并重视中国的电影人张艺谋、陈凯歌与巩俐后,它又让我们见识了电影节刻意形成的对明星的“聚焦”。——作为一种参照,戛纳对极欲与世界接轨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也许是值得玩味的样本。
今年戛纳电影节上演的第一道“明星大菜”是美国明星布鲁斯·威利斯与黛米·摩尔夫妇。通过电视观看他俩作为戛纳首映片《第五元素》的特邀嘉宾踏上红地毯时所引发的那阵喧哗与骚动,你很难判断电影节与明星的这种“合谋”谁更得利。
在距戛纳遥远的中国,今年对戛纳的重视恐怕也是空前的。中国的明星巩俐是这届戛纳的评委,而恰巧与她已经分手的张艺谋又欲将自己的新片《有话好好说》送往戛纳,这曾经有着浪漫过去的两位中国明星在美丽的戛纳相遇将会如何——这构成了人们注意力的非虚构的悬念。张艺谋的新片最终没能成行,我们无法得到他们相遇异国可能出现的种种结果。但戛纳不断捧出的“明星大菜”不是经常可以制造出这种十分巧合的意外吗?
明星们一次一次撞击你的记忆,你最终没法忘记这两个字:戛纳。一个国际电影节就在这种与明星的“合谋”中完成了它对世界视线的吸引。从另一角度而言,一种著名“品牌”也就因此而诞生了。
今年戛纳电影节两位法国前明星没有被邀请也成为了传媒广为传播的消息——阿兰德龙与德帕迪厄对戛纳组委会对他俩忽视的愤怒,其实让人更多地读出的是一种失意一分落魄。
法国阿兰德龙们在本国的国际电影节上被忽视现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没有被重演。在本次上海电影节上,我们可以发现孙道临、秦怡、王心刚……那些大约只有45岁以上的人才可能记全的面孔。
这些人是曾经的明星,况且尊老也是我们的传统,不过也就是上海的一份报纸明确地忽视了他们的存在而径直质问电影节“缘何当红明星少”。
接受采访时,上海电影节有关人士提供了两种版本的解释:
其一,准备邀请一些国际大明星来沪,除免费提供食宿行之外,还拟给予一些经济上的补偿,但国际明星来沪,显然不会单独成行,夫妇子女以及随行人等一并来沪,开支显得过大。国内的一些明星也拟邀请,但他们有“出场费”的要价,当然拒绝。对“出场费”的追问,得不到有关人士更进一步解释。
其二,上海电影节的目的是为了电影艺术,它追求让观众注意的应是电影,有明星想来只能是锦上添花,不能让他们喧宾夺主。
分析这两种版本的说法,电影节拒绝明星虽然有不得已的因素,但拒绝的姿态显然是明确的。有关人士对这一强硬姿态的解释回避了一种容易被忽视的疑问:拒绝电影吸引观众最重要的成分之一的明星,就真的能使观众的注意力投向电影吗?
传媒拒绝了电影节
拒绝明星而使观众更注意电影的说法首先在记者这里得到否定。
本届电影节参赛参展影片共269部,而大多数记者仅看过不足5部的电影。其中理由说来,你几乎无法指责。首先这些影片大多不会在中国上映,其次这些影片的导演、演员即使专业人士也不一定知晓,普通读者如何又能有兴趣?
一位记者代表一家传媒,当他们只看过这样为数甚微的电影时,你能相信他所供职的那家传媒的读者会对电影本身产生兴趣?
在电影节快结束时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传言称伊能静将来参加新闻发布会,这位二线明星尚未到场就已引发了一场争夺有利地形的骚动,记者的明星“饥渴”由此可见一斑。
张艺谋与姜文、李保田等人电影节期间携片《有话好好说》抵沪做宣传,记者采访之多使许多稿件标题竟冠为“张艺谋打败电影节”。与张艺谋抵沪宣传同一时间的电影节新闻发布会因此大大受到损害,仅区区不足10位记者到场。对比这两个新闻发布会人数的众寡,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令人痛惜的事实,这次新闻发布会的主角是英国影片《丛林人》的导演阿格兰德,这部影片两天后夺得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项大奖,而他却在电影节上受到传媒空前的冷淡,我不知道这位英国导演对中国记者的专业能力会如何评价。这一结果该是患明星“饥渴”症的记者悲哀,还是坚持拒绝明星的组委会悲哀呢?
张艺谋回答为什么不参加电影节时说:“我没有受到邀请。如果有邀请,那至少我没有看到。”张艺谋无意间引发传媒的热切关注,确实大大转移了记者对电影节的视线。张果真没有被邀请,按照电影节的逻辑显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比张艺谋更知趣的是葛优,他也在电影节期间抵沪参加就在电影节主会场——上海影城举行的中国导演年会,他悄悄进退,刻意拒绝吸引传媒关注。还有一位悄悄进退的明星是邬君梅,她与普通观众一样参加了电影节的闭幕式,仅有几位超级影迷注意到了她的存在。她只是因为回沪休息而碰巧碰上了这次电影节。
中国的明星们如果说有“要价”一说,那同样更存在另外一种心理倾向,那就是尽量不“喧宾夺主”。像戛纳电影节那样明星与电影节在相互的“合谋”中完成对世界视线的吸引,也许只是一幕我们只可以看一看的西洋景。同样是国际电影节,在我们这里则演变为电影节与明星争夺谁才是主角的对峙,在这一竞争中,我们观察到中国明星们已经自觉地悄然退席,至少我们没有听说那几位即使是国外大电影节也经常被邀请的中国明星,对没被上海电影节邀请而像阿兰德龙们一样表示愤怒的消息。
国际A级电影节的身份,使上海国际电影节仿佛被赋于了可以说“不”的资格,拒绝明星,实际上也就开始了对传媒的拒绝。传媒对明星天然的需求,被没有明星的电影节给釜底抽了薪。也许传媒自此“改邪归正”也拒绝明星,另外一种也许就是传媒拒绝电影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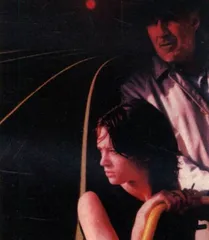
《旅伴》
拒绝需求链能否成为国际电影节
此次上海国际电影节几乎所有参赛的外国影人在回答“知道中国哪几位电影人”时,都只说出这三个名字:张艺谋、陈凯歌、巩俐。这一事实使中国的电影专业人士经常要面对外国同行与记者的追问:在哪里能找到这三位中国明星?中国合拍片公司总经理郑全刚叙述这一尴尬时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这一尴尬背后所隐藏的是这样一种事实,一方面上海国际电影节可以做出拒绝明星的姿态,另一方面电影节却又不得不忍受着被别人拒绝的处境。
此次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石方禹在回答“这些参赛影片是否可以代表这一时期世界电影较高水平”时,十分巧妙地绕开了是与否的答案。他说,这些影片可以代表参赛国的较高水准。
日本电影代表团团长高山宽平就日本电影界对上海电影节态度的描述可以让我们认清一种事实。去年东京国际电影节选出推荐的五部佳作,高山去征求他们是否乐意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时,四部电影制作者作了拒绝的回答,只有一部电影最后参加了这次电影节。
这种拒绝的现实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委员会官员们解释此次电影节参赛影片质量不高的最主要的原因。
最简单地说,国际制片人协会有一规定,一部电影只可以参加一次国际A级电影节的比赛。这一规定使各国许多高质量的电影在选择电影节时当然要作各方面考虑,毕竟有九大A级电影节。仅仅只举办了三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并没有显示出它吸引各国优秀影片参赛的特别的优势,它被拒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上海国际电影节被别国高质量电影拒绝却不是一件特别悲哀的事情,这只是成长中的烦恼。现在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正在成长的上海电影节所追求的一种个性:拒绝明星。这种自诩为抛弃一切包装只注重内在质量的品格塑造,从逻辑上说并非不是一种选择,但这种个性当真可以使它有别于其他八大国际A级电影节而显示特别吸引人之处并完成对内在质量的追求吗?这是巨大的疑问。
一年一度,有数亿人观看的奥斯卡狂欢之夜显示了电影的生存的需求链——明星、影片、金像奖、传媒、大众——在这种相互需求相互依靠的链环中,电影找到了在当代社会存在的理由,奥斯卡以及种种电影评奖也找到了存在的理由。你能够想象在这一需求链中谁能表示对其他链环的拒绝而独立生存吗?
当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始自觉地取消电影生存中的一个个链环时,它在一定程度上找不着北的迷失已然成为事实。 张艺谋艺术电影中国电影导演大导演上海电影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戛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