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51)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陈宝国 王学权 李平 刘国信 夏志琼 贾抒 徐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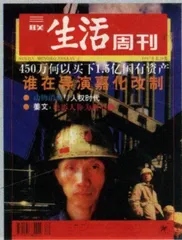
自己买下自己的工厂,从无产者变成资产者,这确实是一种命运抉择。值得讨论的是,这样的改制下,普通工人的命运发生了什么变化。会不会由国家包办变成“一切由钱来把握”?
北京陈宝国
意识形态问题
南京扬州路1号 王学权
好莱坞亦与成龙合作拍片,酬金多多,但成龙这厮倒也有趣,提出一个看似玩笑、实质上却包含意识形态问题的条件:他扮演的中国人必须是最后的胜利者,否则就“拜拜”。成龙宁愿放弃进军好莱坞的机会而偏要一厢情愿地为中国人争一个face,其实就是因为民族自尊心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成为自己的行为标准,那就是——他不能忍受中国人在美国人手下当狗熊,尽管只是演戏。
前几天我看了一张VCD,名叫《拳行天下》,美国人拍的。看到大半,我看不下去了,原因在于其中一个镜头极大地刺激了我——在擂台上,美国拳手把中国拳手的脖子扼住,摁在地上,举拳欲击,而中国拳手满眼哀怜,一副绝望之态。
看来,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也没有肚量容忍自己在影视作品中被别人打败,这并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观,而是意识形态使然。因为,演戏固然是虚的,但视听的灌输却是实的,角色本身固然是虚的,但感觉的刺激却是实的。
正如意识形态,“意识”固然是虚的,但“形态”却是实的。
只能捐钱吗?
北京将台乡 李平
政府号召大家捐钱捐物给一些温饱还没有解决的贫困人口,我们全家都一致响应。我爸把他那件1958年买的棉猴终于捐了出来,那是一件质量依然不错的冬衣;我妹则捐了前年买的一件皮夹克,那件过时的衣裳她一直不知如何处理;最令人感动的是我儿子,他把他一身“李宁”运动服也捐了出来,然后开口要我给他买一身“耐克”。我没什么可捐的,只好出力,抱着这些东西和其他一些杂物,沉甸甸的一大摞,走到居委会。没想到居委会门前贴了一张布告,说本小区要求居民自愿捐款,不接受捐物,理由是物不好处理,钱好处理。这肯定是一件违反政府精神的事,不知是从哪一级下的命令要求我们只能用钱来表示爱心。
科普文章“打架”,百姓如何生活
山西阳城畜牧局 刘国信
现在癌症患者比例较高。于是乎,各种媒体纷纷以其极具权威的面孔介绍一些形形色色的“抗癌物质”,如紫菜、海带、芦笋、白萝卜、土豆、大白菜、西红柿等多达几十种,似乎与我们生活相关的各种水果蔬菜都有抗癌作用。为此,许多人大惑不解:我们每天都吃的是抗癌食物,为什么癌症患者的比例仍然那么高呢?事实上这些结论并不确切,如有关紫菜抗癌的说法,其来源于日本一家研究机构,该机构医生通过一次一组动物实验,以一系列的数字“证实”了“紫菜含有抗癌成份”;但结论公布仅一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5名权威医学家就指出,这种说法很可能“依据不足”,随后他们通过同样的动物实验后,果然以一组相同的统计数字否定了前种结论;于是又有一家报纸称:紫菜只是日本人爱吃,至于能不能抗癌,其实并无特别功效,因为日本癌症患者一直有增无减……读了这些文章,真叫人亦真亦幻、哭笑不得。
还有一些报刊关于“中老年人不宜吃鸡蛋”的告诫性文章,文中说,因鸡蛋的蛋黄中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它是诱发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及脑中风病的元凶。看了此文,一些老年人和患病者不得不忍痛割爱,同鸡蛋“绝裂”。其实这也是在以偏概全,科学研究表明,鸡蛋中虽含有较高的胆固醇,但同时还含有大量的卵磷脂,卵磷脂有降低血脂的独特作用。因为卵磷脂被胃肠吸收后,能使血液中的胆固醇脂肪颗粒变小,悬浮于血液中而避免在血管壁上沉积,同时还能促进胆固醇透过血管壁而被吸收,所以使其失去了危害性。因此,专家们从更科学的角度忠告人们:可以放心地食用鸡蛋。
这里就存在着科研成果的权威性与普遍性问题。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科技领域不断有新观点、新发现的出现,这本是正常现象。这些新的观点、技术大多数无疑是科学的;但也有些尚属实验性的初步研究结论,并不具有普遍性,仅能在内部学术报刊上发表,而将该文不加任何引示地转载于新闻媒体,公开呈现在大众面前则有不妥与误导之嫌。
“克隆”文化
辽宁凤城农行 夏志琼
儿子喜欢读书,我给孩子购买图书时,认认真真地翻阅一下,发现图书中的“克隆”现象十分严重,如一篇《卖火柴的小姑娘》,孩子的图书中竟有8本中同时收录,《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有9本图书收录。自己一算计,为孩子购买的图书中,有20%多是重复的文章和内容,新书不是新知识。
“克隆”文化不只是儿童图书,中外历史名著更严重,如《红楼梦》、《水浒传》等都有多家出版社的多个版本,前几年出版界曾掀起一股散文热潮。诸如《名家经典散文》、《散文精选集》、《散文杰作珍藏本》、《散文精品大系》等等,令人眼花缭乱。这些出版物大多成套炮制,有些还不拆零销售,令读书人倍感困惑。一位读者为了得到贾平凹的《人病》,不得不花上几十元钱买下了整套的《中外永恒主题散文精品》。影视作品更是大碰撞,像《孙武》、《施耐庵》、《胡雪岩》等反映历史名人的电视剧都出现了多家同时拍摄,重复投入资金高达3000多万元。此外老剧新编,短剧拉长等现象也是文化“克隆”。
文化成为商品是好事,但是经过“克隆”出来的文化要找到市场,只有让“克隆”人手持“克隆”出来的钞票去买才行。但我们不能每天都过“克隆”出来的日子。
一年招生两次?
北京 贾抒
我不明白为什么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大学都一年只招一次学生(孩子)。在我看来,如果每年的春、秋季都招生,至少有以下好处:
1.每个孩子都能在满3周岁的半年内入幼儿园、满六周岁的半年内入小学,有利于早期教育,也可早些解决一些家长带孩子的困难。2.一个班级中孩子的年龄差别从最多差一岁缩小到最多差半岁,更便于教学和管理。3.孩子的智力发育有早有晚,每个年级都有春季班、秋季班以后,一些智力超常的孩子只要多学好半年的功课就可以跳半级;而一些智力发育较晚,或因探亲、生病等原因耽误了几个月功课的孩子只要降半级就行了,想赶上也比较容易。4.考试失常即使对一个天份很高的学生来说也在所难免,何况还有身体的、家庭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如果有春、秋两次招生的话,落榜学生只要补习、等待半年就可有下一次考试机会,大大节省了时间,也减轻了家长的负担。5.从学校管理的角度说,虽然增加了有限的工作量,但一次离校、入校的人数比较少,减轻了对学校管理工作的压力;能解决一些任课老师一年当中忙闲不均的问题等等。
我认为这种改革挺值得也很必要。
开会与“学习”
山东师范大学 徐斌
中国的会多,早已世界闻名。比如单位无论大小,机构无论轻重,每周一般都有一个例会(我此时使用的Windows3.2中文版的ABC输入法里面就有造好的“例会”一词,可见例会的思想不仅是深入人脑,而且也深入本土化的电脑了)。这样的例会常常遭到永远没有机会发言(也不想发),又自以为是的小字辈的讨厌,也常常令不请中华会文化的外籍人士不解。我们自己,也是反反复复检讨了多少遍,为了检讨会议多的危害,又不知道开了多少会,可结果会山更加巍巍高耸,让无数人穷其毕生精力也登不到峰顶。
我所在的这所大学,每周,这些被社会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需要正襟危坐,“学习学习”。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我们的黑色幽默?我们的智商实在是在人类中出类拔萃的——有谁还能想起这样卓绝的浪费众人生命的办法呢?一群有思想的,可称上是“知识分子”的人,定期地聚在一起,被“学习”一番,的确妙不可言。按照一些后现代的艺术标准,众多的中国人定期地开这种并无多少实际内容的会,可说是一次次反戏剧的集体大上演,而此事还要进行相当长的时间,虽然许多人早已看出了其中的可笑、可叹和可悲。也许终有一天,会有一个“不更事”而勇敢的小男孩,站在旁边大声说:“其实他们什么都没学呀!”然后开会的大人们先是试探,继而附和,再就异口同声地说:“是呀,其实我们他妈的什么也没学呀!”然后从各自的会场作鸟兽散,各忙各的去了。下棋的下棋,织毛活的织毛活,打球的打球,读书的读书,社会反而因此更活跃,个人也多一份轻松。但目前,我们只有拿出一个面孔/面具,继续端坐一方,手捧茶水,怀揣报纸/毛线活儿,身在会议厅,脑想窗外事,共同蓄谋屠杀自己的时间。我看够和受够了这样赤裸裸的被称作“学习”的无所事事。什么时候我们向我们自己,作一个永远的谢幕,不再上演这样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