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谈的话题:Techno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卞智洪)

世界上最大的Part——100万人涌进柏林参加第9届“爱的大游行”
世界上最大的party
今年7月的Loveparade(爱的大游行)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一个party。100万年轻人拥进了柏林,塞满了所有的公寓和旅店,支起成千上万的帐篷,他们阻断了交通,挤爆了Tiergarten公园,聚集在防空壕、教堂、停机坪、湖畔这一类地方彻夜不眠地跳舞和呐喊。在48小时的狂欢中,无数人在心里或嘴上说着同一句话:“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使他们赶到柏林的东西,其实只有一个,就是40辆艳丽的流动彩车上所播放的那种音乐:Techno。
Techno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可以包括House、Euro-Reggae、Raggamafin、Jungle、Ambient、Trance等先后出现或并存的音乐种类,这种音乐由计算机和电子装置取代了传统乐器吉它、贝司、鼓之类,主要由deejay(DJ-discJockey唱片骑师)制作而非传统乐队演绎。Techno及与之相关的舞蹈、party等一系列状态被称为rave(香港译为“瑞舞”),其狂热者就是raver。
Techno最初出现在80年代中期德国、英国和美国中部城市的一些地下俱乐部和舞厅之中,经过10年的发展,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蔚为壮观。在德国和英国不用说了,Techno音乐已打到排行榜第1位,在美国Techno被唱片业老板称为下一个热点,希望能够取代市场份额正日渐衰退的另类音乐、说唱乐和乡村音乐。在莫斯科已经有50个Techno俱乐部,大街上充斥着色彩亮丽的Techno服装。波兰的一个青年企业家向柏林的LoveParade派出了30辆班车。亚洲的Techno中心是东京,但在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Techno也正日益风行。
对于传统流行音乐的爱好者来说,大多数Techno是不易把握的,它流动多变,喜欢重复令人昏昏然的单节奏乐句,装饰“哗哗”、“嘟嘟”等各种各样的电子噪音,关键是它常常缺少流行音乐所有的主唱、旋律和内在逻辑。但是ravers却从中得到了他们所渴求的东西:脚步在奇妙的混音中迈动,手臂伴随振奋的节奏开始摇摆,Techno是一种更直截了当的表现;更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更彻头彻尾的激情与沉迷。与Techno结合在一起的是年轻人整个的生活方式,从时尚到高科技到休闲到运动。德国Bielefeld大学的社会学教授KlausHurrelmann说:“Techno文化是一场青年解放运动,它是尖叫的,多彩的,自发的;使它区别于过去的作主流文化的是它的宽容和开放性,是对严格的意识形态的排斥;任何人都可以参加。”

U2也在做Techno,但似乎不如英国的乐队成功
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吗?
欧美流行乐坛落下的石头,涟漪总会泛到中国。无论重金属、硬摇滚、朋克、说唱还是爵士,在中国总会找到相应的乐队,至少自称是这样。但Techno呢?有待是北京音乐台的一位主持人,他在五六年前即开始播放这种音乐,尽管那时他自己还是一个摇滚音乐迷,但直到今天——他已经是一个Techno迷了——他说:“中国没有一个人谈得上是Techno的制作者,Techno的听众也非常之少。”有待在北京开有一个唱片店,近来TheProdigy和ChemicalBrothers这两个最出名的英国Techno乐队的唱片销售有增,但多数购买者是听了唱片店的推荐才买的,因为“这是最新的、最时尚的音乐”。
Techno首先是舞曲音乐,美国最初的Techno即由一些前卫deejay将迪斯科、灵歌和高科技合成声混音而成。尽管欧美许多raveparty在郊外进行,但各种风格迥异的Techno舞厅无疑显示了这种音乐的丰富多彩和花样翻新。而北京的迪厅似乎除了顾客变少以外,没有什么区别和变化。5年前放的是Euro-Techno,今年依旧Euro-Techno,昨天的舞曲招人多,今天继续放,哪怕一个晚上放3遍。事实上,恰恰是这种单调、粗糙的方式使多数迪厅受到了冷落。有人说到迪厅去就是“卖块儿”,“出大力,流大汗”。在不多的几个迪厅,像北京的Lightman、“热点”、昆仑饭店迪厅,因为比较专业的deejay控制了场面,较新的Techno音乐首先引来不少如饥似渴的外国人(迪厅把外国人作为点缀,因此多数对他们免费),然后是蜂拥而至的时尚中人。
HardRock是北京颇有名气的一家酒吧兼舞厅,它的deejay黄烽说:“我每天尽可能地放一点Techno,因为我太喜欢它了。但迪厅是从中国人身上挣钱的,他们不喜欢,你当然不能放。你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个成功人士,但很明显他不懂音乐,不会跳舞。倒是一些孩子很自然地接受了,身体的摆动也很好看。”
创作Techno需要你既是一位音乐工作者,还需是一个电脑狂人,从loop(采样)、mixing(混音/打碟)、programming(编排)这些专业用语就可以看出来。设备的购置和开发对中国的deejay来说是一个难题,更重要的是关于Techno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需不需要这种音乐?中国有没有西方的那种clubculture(俱乐部文化)?

迪厅饱合了还是发展不够?乐队现场演出调动起年轻人的热情(邹俊武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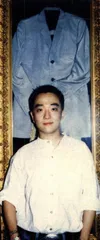
黄烽说:“我喜欢Techno,但我必须考虑中国人的趣味”(邹俊武摄)
俱乐部文化
英语中有一句口头禅叫做“toseeandtobeseen”,即除了要赶潮,还大有“表现自己,我即时尚”的意思。但我们的心态未必如此。一位小有名气的年轻广告人在Lightman迪厅说:“谈完工作就想玩,看看这么多人跳得这么欢,很痛快,生活丰富多彩。自己就无所谓了,你说‘要么赶上要么落下’,在干活儿上要这样,娱乐上就免了吧。”去年万圣节大西俱乐部搞了一个化装舞会,据老板介绍,除了两三个演艺圈的人以外都是外国人。
想表现自己的人当然不在少数,事实上每一个时尚和潮流都是被他们带动起来的。年轻人无论在着装、休闲、运动还是在艺术和观念上,都使他们的父辈和兄辈自叹弗如,当年对摇滚乐和迪厅的热衷只是一二例。但俱乐部文化除了俱乐部所含的参与意识外,还在于它包含着一种可称为文化的内蕴。
崔健在一年多前接受《今日先锋》的采访时说:“中国的音乐教育很差,差到了有听觉危机的地步。人们始终不把音乐当作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更不当作深层次交流的方式,而是始终作为消遣,就如卡拉OK,把音乐当作低级消遣方式。”以迪厅为例,舞曲音乐是流行音乐,但它现在无疑是国际上极具前卫性和探索性的音乐,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为之疯魔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而中国的迪厅无疑还只是商业和娱乐结合的产物,老板为赚钱,客人为玩玩儿,即便在它最火爆的1994年,有多少人是非去蹦迪不可的?“谁说迪厅饱和了?不过是我们的发展不够,不足以吸引人罢了。”deejay马钊这样说,他感觉自己所在的潜水艇迪厅(北京大学旁)对此无能为力。
因此时尚归时尚,文化归文化,迪厅的火爆一闪即逝,扭秧歌和交谊舞却能够长盛不衰。黄烽说:“尽管中国的迪厅和俱乐部很多,但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并没有一个俱乐部(club),有的只是夜总会(nightclub)。”
毫无疑问,值得骄傲的艺术和文化是那些具有原创性的艺术和文化,而绝非搬弄与效仿。但多元文化的共存才可能促成一个健康的、生机勃勃的、有创造力的社会,每个个人才可能从某种形式中获得与他生活相关的精神满足或创作灵感。回到Techno,有待说:“我觉得它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想听它,这就跟渴了要喝水一样。你可能会觉得这不是中国的音乐,不是你的音乐,但你应该感觉到这是地球上的音乐,或者说,这是明天的音乐的一种。”他还说,“如果我来开一个迪厅,那会大不一样。”好吧,让我们等着。 艺术音乐